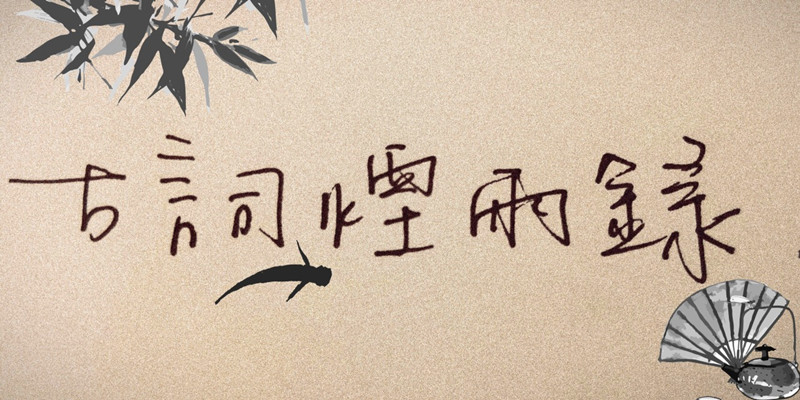不知韦庄在深夜花下初识的这位“谢娘”究竟是什么身份。杨湜《古今词话》说,“谢娘”本是韦庄寓居蜀地时一个才貌双全的宠妾,后被蜀主王建以“教词”为借口夺占。但这一解释已被指出“殊不可信”——其实不必确考韦庄生平,词中之言与杨湜之说便牛头不对马嘴。
在古代社会,曾经花下相逢的一男一女在数年之后“俱成异乡人”,并不是正常的状态。这需要女子拥有特殊身份——如官员的女眷或仆婢,可随官员宦游或因官员失势而云散天涯;也需要社会具有特殊形态——如天下大乱,人总是不得安居、被迫迁徙。
在古代社会的正常条件下,男子远行、归来,女子等待、重逢,二者一动一静,构成了许多闭合的人生轨迹。唐人杜牧相隔十四年重来湖州,尚能见到前番爱慕的女子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罗隐“钟陵醉別十余春”,还能够“重见云英掌上身”。像韦庄与谢娘这般各在他乡、寻访无凭、后会无因的分别,倒是一种特殊状态。世乱飘荡,各如飞蓬。世路之茫茫、命途之乖舛、人生之荒谬皆呼之欲出。
个体和家庭迁徙的概率、频次、距离、激烈程度,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指标,衡量社会的性质。当一个社会的成员没有任何迁徙的机会,儿时的亲友邻舍到老都在你的身边,这个社会必定毫无生气、静如死水。而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则无人能得安居,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在辗转迁徙中度日。
当今世界,迁徙因机遇多多、交通便利而成为了人生常态。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说:
“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来越少地生活在他们或者他们祖辈生长的共同体内。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要求生产以及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经常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社会联系越来越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来越难以在共同体内扎根或者与工作同伴或邻居建立长期关系。个人必须经常在新的城市从事新的职业。”①
在分别已成常态的世界上,“分别”一事本身也因互联网和交通工具的发达而悄然改变了内涵。大家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有因,相见却未必再可贵难能。古诗中求之不得的伤情,今天或许已变成求而得之、甚或无谓再求的无聊。
而人生荒茫乖舛的底色仍在。
荷叶杯
[唐-前蜀]韦庄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
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
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选自《唐宋名家词选》第17页)
怅诗
[唐]杜牧
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选自《中国历代爱情诗萃》第230页)
赠妓云英
[唐]罗隐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选自《中国历代爱情诗萃》第283页)
①《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第367页。
冯震翔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