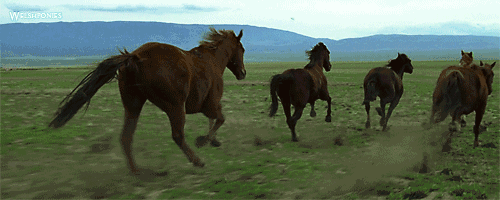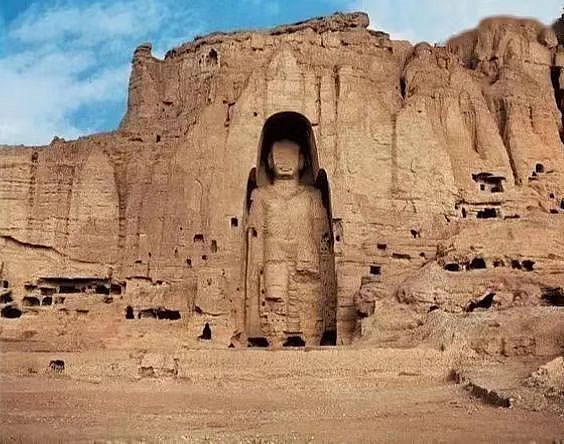我出生整两个月的那天,在马夫带着我们母子去B河洗澡的路上,母亲悄声告诉我:“我怀你两个月的光景,驮着旅长去北平,那天,赶到西直门,天已昏黑,城门下了关。旅长的传令兵叫了半天门,城楼女墙边好不容易露出个老兵的半截身子。传令兵说了一大堆需要马上进城的理由,他理也不理,又把半截身子退了回去。”
我打断母亲的叙述,说我早就知道有这回事。
“你那阵两眼烘黑,莫非在我肚子里听到传令兵叫关来?”
“不是。昨天我还听马夫和传令兵念叨这出事。看门老兵本想学学不给皇帝开门的古人,也图个升官发财。不过他官没升,财倒发了个血的;他赚了五百大头的奖励,同时又得到了枪毙的赏赐。他们说一时一事,恩威并施。”
“咳,是这么回事。旅长是很恼火。当时也只好随随从在西直门歇息。大约有嚼十口八扣炒豆的时间,城门吱吱啦啦地开了。马夫忙取下我头上挂的栲栳,准备……”
“栲栳?我知道,不是现在外出吃饭时挂上的那种帆布筒,是拉炮骡子现在用的那种,柳条编的。很密实,盛水不漏。”
“你真聪明过人。你快快长,总有一天会有好几个比这强的马夫侍候你!”
母亲侧过脸,瞟了瞟前面懒洋洋的马夫,马夫感到手中的缰绳有点紧,回头看了看。许是母亲觉得内疚,便赶忙摇摇头,好像她的眼睛上有尾死皮赖脸的绿头蝇,单凭合合眼皮是赶不走似的。马夫放慢脚步,哼了一块歌:
拨火投鹅毛,
骑马到临洮。
来回三千里,
鹅毛还没着。
这歌可能是歌颂母亲的,因为母亲不再忍心议论马夫了。一会,她又讲:“我头上的栲栳还没被收拾好,城门上传下医生吆喝:‘傻帽,白着什么急!快让开点!’让什么?回头一望,旅长和他的随从就都就地跳了起来,恭恭敬敬退到路旁,立正站好。只见一头灰色小毛驴,一头比狗大不了多少、老得不能办事的叫驴,一走三摇晃!给他让什么路?就因为他拉着辆一走三吱嘎的木轱辘水车,车上插了面小黄旗?但我看到他老不带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一对沾白沫的鼻孔煞乎煞乎直喷气,就恶心地向路旁躲去。真讨厌!这个马夫,许是猴孙给他的胆,照我的脊梁就是一拳,骂咧咧地小声唠叨:‘你不看看,人家是给皇帝拉水的。这水是玉泉山的玉泉水,拉的车还是乾隆爷时的……’过一会,他又怕我报复那一拳之仇,又嘟嘟囔囔地解释:‘别说你,就是李鸿章爷,张勋爷,见它都得让路三舍,都巴不得给他怀个驹子!’我义愤填膺,即刻想超越到他前面,压压他的威风,谁知城门楼上又传来那老兵的一声高喊:‘滚你妈的!全老住地呆在原地!你们是外国洋大人怎的?不是就老实地给我呆在原地!’”
“那么……”
“啊,也是我太感情用事了。虽说那已是民国十三年,皇帝管的地盘远不如往昔,不过皇帝到底还是皇帝呀。论大小,天底下除了皇帝就数洋大人了。旅长就不如他们……”
“驾!驾!”马夫嫌母亲越来越慢,就很骄傲地叫了几声。大概,他后悔自己吆喝的声音有些僭越,便扭回身来,像在自言自语,其实是用谁都能够接受的方式讨好她:“老姐,你白白长着四条没有出息的飞毛金腿!你该到紫禁城里去啃草!我来世造化,天天念佛,托生个您,就嘎吱一口咬断缰绳,一溜烟跑到里头,叫万岁爷天天屁股亲我的脊梁杆子!”
我虽然出生不久,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前不久,他喝了四两高粱烧,和三个团长的马夫赌钱输了,偷了母亲的料豆变卖,事发后遭到鞭打,屁股出了血。这件事,他倒不埋怨我母亲,她绝对不会告发他。当时旅长拍拍她的脸,说:“马夫拿脸当腚,叫你掉膘啦!”母亲假装耳背,木呆呆的,一动不动。如果她表示会意,动动蹄子,嘶鸣一声,马夫就可能倒大霉。她还是马夫的恩家——马夫在死受旅长鞭打时,她越过横在门前的马槽,到了旅长的身后,用项鬃拂着他的靴子代为求情。所以马夫身上除了有些血写的洋文外,并没更大的损害。
母亲紧走几步,又悄声说:“紫禁城,紫禁城,伤心!我本来就该到皇家去的。”
“我们就是皇家的马!”我连忙接上去。这事母亲和我说过多次,每次总要伴以泪水。我怕她追昔忆往,又是郁郁不欢,酸楚的泪水把以后几日浸透了抑抑,就干脆接上,使她不必再讲。“你就是御马!我就是御马的种!”
母亲本是蒙古王公活佛向皇帝年贡宝马名驹中的一匹。清朝历代皇帝都是“马上天子”,且不说在我们身上建立满洲的努尔哈赤,也不说在我们身上入关当上大清皇帝的皇太极就连多病早殁的咸丰皇帝,也自诩是善驭我们的能君。母亲曾说:“清朝的皇帝,谁不喜欢我们就不得好。”这倒未必。但是光绪皇帝也的确不喜欢驭马。总而言之,清家皇帝和我们也真有不解之缘,否则他们就不会把上上下下的官衣礼服做上马蹄袖了。我最不同意母亲这个观点:“清朝的灭亡,原因是去掉了袖口上象征权力和高贵的蹄形锦片。”但是为不引起争论,就顺着她的心意,造了个可以结束她抱怨的句:“清朝皇帝不骑马,纯属不孝列祖列宗的行为!”
哪知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皇帝不爱马了,本该代替牛肉红烧的劣匹骞蹄,反倒成了宝马良骥!”
就像食槽里的料豆,吃空不见了,在肚子里还要保留一段时间那样,清朝最后的皇帝,固然不能再紫禁城以外发号施令了,然而,蒙古王公活佛,却年年照例进贡许多马驹。那阵上驷院有一百四五十匹马,全是些磨光牙、不痾粪、瘸短腿、瞎尽眼的东西。这都是因为光绪皇帝以来,皇帝不再过问上驷院,所以每次进贡的马匹,还没牵进皇宫,就让上驷院的官员高价卖掉,然后,再用低价买进劣马顶替。到头来,小皇帝溥仪要骑马以示光复帝业的决心时,那些靠倒卖御马长肥变阔的官员,不得不去北平马店买了一匹小黑马以充骥材。
“那是匹什么东西!”母亲这是在议论那匹小黑马。这时她突然抬起头,细长的脖子弯成弧形,高高眶骨下的眼珠凸了出来,黑眼珠小,白眼珠大,眼珠表面虹彩一般变化多端的光彩,变成单一色的血丝,鼻孔大大地张开,很有节奏地向外喷着热气。“那是匹什么玩意!她娘是果下马,她爷是川马子。怀歹心的车把式,存心不良的艄公,开黑店的笑面虎,嘴唇涂香油,舌头裹蜜的牙客,南来长大疮的娼妇,北去摘了肾子的太监,什么人也好骑他们。就是在处处碧草的季节,他们的主人公害怕他们吃饱后脾气发燥,伤了乘主,也只让吃个半饱,然后给戴上笼嘴……”母亲每说到这里,声音都降得很低很小,而且会慢慢低下头去。但略停片刻,她又猛地抬起头,斜削竹筒般的耳朵好像捕捉四方声息,前后左右迅速转动着说:“哼哼,他们的孩子,就在油油青草不能尽吃的季节里下了种,本来先天下不足,结果碰上上驷院的鬼头,杂种翻成了御骑。驽马恋栈豆,日月逊灯盏。上驷院的混蛋,他们让我肚子里一会着火,一会结冰!”
中国最后一个正牌皇帝骑这匹马时,不仅有教授骑马的人,还有从王公大臣中选出的八个“压马大使”陪他。她辔头上紫磨金用了三四斤,豆粒大的钻石少说镶了一百颗。至於鞍子,虽然都嫌朴素了些,但上面细饰用的瓜子金和东珠,也几乎把这匹短腿鼓肚的杂种压折脊梁骨。她吃上三五粒料豆就饱了,皮毛闪亮如缎,屁股肥得像泥老虎的屁股,往马厩里一牵,就打着响鼻,摇头摆尾,很有些猎人钻出老林回家,水手离开漏船上岸的轻松心情。她有好几个马夫照料,他们的官职都比我的主人大得多。她走到哪里,那里便是一片喝彩。甚至有位文臣还说,一千多年前有个诗人便已料知她必然出世,写下了“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的五绝为譛。“这马不瘦呀!”当时有位官员看到这杂种肉乎乎的短腿,就这么说。不料为此他受到举朝上下的责骂,连那些太监也跟着瞎起哄,说他学问不到家,太欠“夫功”——这些没肾子的家伙故意模仿乾隆皇帝的口气。据说这个风流天子曾经贬一位把“翁仲”错当成“仲翁”的翰林太欠“夫功”。至於他欠什么“夫功”,他个人,乃至闹事的太监,竟然到死不知。
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马的好坏。这使母亲甚为不满。其实,维护这种局势的人,才是真正的可恨。
母亲由蒙古进贡到上驷院之后的经历,她向来讳莫如深。这证明她不满足眼下的位置。就今天我接触的各种情形来看,凡对自己的位置得意的,总喜欢提到自己过去的种种艰辛不易,而且,这些艰辛和不易,总要被夸张到非是一般忍受力能忍受的程度,使听者闻之肃然起敬。譬如,军长的铁青马常常炫耀说,他一岁的时候,他原先主人家的兒汉要给他打鬃,他见那人生相丑恶,又加上满嘴脏话,就一蹄子送过去,把头给他蹬去了半拉子。既然出了人命,人家当然不能饶他,而且声称非打杀他不可。可是,任皮鞭竹杆,锨镢二齿子,怎么打他都没事,最后那些打他的人反倒吓软了手!其实,那时他才学驾套,听不懂进退拐转的吆喝,羞恼之下,趵开了蹄子,带起的泥块打中了看光景的小孩,让主人用甩得挺响的鞭子吓唬了他几下罢了。
母亲的一些经历,还是被我知道了。
我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第五旅旅长的马为了一小撮盐发怒,冲起了鬃毛的尾巴,样子非常可怕,致使她那位很忠厚的马夫遭受了两个耳光的惩罚。母亲对我说:“马夫给她的烧饼里盐分并不少。难怪她,口外长大的,没见过世面。要是她到盐田里去驮一趟私盐,看看满地铺的都是什么,就不会吹沫呲牙了。”
“盐田?私盐?”这新鲜的词汇使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场面:几十里一片的平原,上边没有一棵树,全是绿色的卤蓬,平原的前边是一片银灰色的水,水天相连;靠近水边是一块一块的大畦子,畦子的边沿有青泥筑成的坝埂,坝埂上落着很多驼背缩脖的白鸟;那些畦子里有的有水,有的铺了一层盐,很白。
我把这番景致一说,母亲很惊奇。“你没去过呀!我怀你的时候也没去过那里呀!我去的时候,还是被上驷院混蛋倒卖不久的事情呀!”母亲诧异的神情,使我的脑海里又浮出一个场景:我不是马,然而一切感觉和马一样。奇怪的是自己被一团血影包裹着,仿佛被盛在厚薄不匀的紫玻璃瓶里,也能看着天,天很亮;也能看着地,地很暗。我的后边有一群兵士,形状变化不定,如同凸凹镜里的活动投影,时长时短,时宽时窄。他们握刀持枪,有的骑马,有的跨骡,高声怪叫着追我。我的前头时常冒出一伙堵截的兵士,可是都被我一跃而过。我身上压了很多盐,还坐着两个人。现在分析,我当时还是一枚细胞,这些还是一枚还没离开母体的细胞的感觉。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母亲必是贩私盐人的坐骑。
“在‘盐田’和‘私盐’里,也打仗杀人、也冲锋撤退?”
“待你大大的时候再告诉你。不过将来你不去贩私盐了。贩私盐,最后很少全鬃全尾活着的,能侥幸活着,也免不了充公,三钱不值两钱也地卖了。”
她说到“三钱不值两钱地卖了”时,声音变得很凄凉,绝不像人们吓唬小孩管用的“别哭了,麻虎来了”那样不关痛痒。人们说,买母亲的价钱特别便宜,好比用鱼目换了颗祖母绿宝珠。这就是“三钱不值两钱”的意思。可是母亲会拉车,会耕地,不像一般的军马,只能充当坐骑。驾辕拖犁,自然不是她与生俱来的。可是她帮人贩私盐以后,被旅长发现以前,曾辗转于庄稼人的手中。
“十几年前,”有一次,我主人来看我,与马夫聊起来。我多次看到,这个身着戎装的人,一提起他的老家和家人,一种有些悲哀的怀念便出现在他的脸上,这自然使我也怀念起我的母亲来。而他这次讲的,也恰巧是一匹与我母亲有着相似形象的马的故事。
听主人讲,十多年前,他的祖父买过一匹马。“就和这匹马一样,白色的,不过是匹母马。”他抚摸着我的脊梁说。
那天,主人的祖父进城赶大集,直到掌灯的时候才回来。一进门,老爷子就喊:“快饿死啦,快饿死啦!”他老伴一听,忙抓了一把鸡蛋放进锅里。
“唉呀,不是那回事。快铡谷草,快刷槽子——我买大牲口了!”
“买了个什么?”老妈妈这才明白过来。
“马子。”
“多少钱?”
“你猜猜。狠往低里说。”
“十块?”
“没个数!你当这是口猪?”
我主人的父亲是远近有名的孝子。那时他感了风寒,正在里间蒙被发汗。二老的谈话他全听见了。听见父亲启动了高声,他慌忙掀被下炕,问道:
“爷,买了个马子?”
“那是。你知道了?”
“好!咱家再有匹马子就全套了。”
“那,你猜多少钱?”
“少说也得百十块大洋。”
“哈哈,才三十块!”
儿子听说,忙穿好衣服跑了出去。天井里已看不清东西,他又回来点起了灯笼。等他看到了那匹马,心里顿时凉了大半。你想吧,那么一匹瘦骨龙,在灯影里,全身都是一道道的骨头影子!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听到天井里踢踢跶跶的,起来一看,那匹马挣断了缰绳,走出了牲口棚,把竖在杏树旁的一捆高粱秸吃得净光,还喝了半缸水。再看看夜间第三次添得冒尖一槽子食,早叫她吃得连点草渣也不剩。她缺多少食!
白天明亮里,那马就更难看了。从我主人的描述里,我惊奇地发现,那匹马竟与我母亲这般相似!我母亲就是这个样子的——略显驼背的身子又高又短,屁股向下耷拉着,一根细又长的脖子被一个瘦头坠得直往下弯。宛如一根挂住勾的钓竿;脸只一捺宽,鼻孔却大得能够塞得进大个的鹅蛋。至于蹄子,也一点不错地像我母亲,薄薄的,形状如半个倒扣的卷沿碟子,走起路来从膝盖那里向外撇,前后扭错,就好比两个重不齐的八字。端详久了,她这丑模样连主人的祖父也觉得扫兴,不光彩。活该!谁叫只图便宜,看也不看仔细就抢着交钱买她呢?於是像遛马这一类的差事就硬落在我的主人的身上。其实这本是理所当然:别看那时他已经长得不矮了,但在家里,可是个孙子哪。
有一天,他牵着马走到村外,遇上了他的叔伯兄弟。他那叔伯兄弟是根独苗,平日除了吃就是玩。这天他是一早去给选好的树枝涂胶粘鸟的——那是鸟们特别乐意栖息的树枝。他见到那匹马,远远地取笑道:“呦,从哪里弄来了这条刀鱼片?”不过,待他走近来,端详过那匹马后,口气可就不那么随便了。“可怪呢。眼光倒挺活泛……”说罢,他又接连把我那同类打量了好几遍。
我主人的父亲要面子,怕人家笑话家里的牲口瘦,所以对那马倍加小心,一连几个月,料也足,草也细,喂得又勤,她也无病无灾,可就是不上膘,走起路来还是搭啦搭啦的,老垂着头。后来让她学驾辕,怎么打她也不进辕,只好让她拉前套,叫她耕地拖耙,和拉车一样,学了好长时间才会。唯独她干活很卖力,从不用鞭打喝骂。家里人对她很失望,不再把她当一个整状牲口使用了。
一天,我的主人又去遛马,又遇上那个叔伯兄弟。这次他劈头就说:“我寻思了这些天,总想对你说:你看,它瘦归瘦,可不是长病的瘦法——它是不是匹跑马子?”
我的主人说,至今他还忘不了那匹马听到这话时的情景。那匹马听到人家这样说她,便突然停住了脚。她横侧着的头低停在空中老半晌,像在寻思着什么。我的主人说,现在他已明白,那马想必是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一个伯乐、在屏息等待着实事求是的評論呢。据主人说,他的那个叔伯兄弟的确是个能家:虽说他的个头不大,可是像斗鸡的挑选呀,叫翅儿的调养呀,狼狗的好坏什么的,却是样样精通。他甚至还会种“油葫芦”,那方法极巧:待“油葫芦”抱出来,他就在它的翅膀上点一点石料颜色,让它的叫声合仄押韵。他见马停住不走,就把手举到它的背上拍了拍。这时候怪事发生了,只见那马突然昂起头,两只耳朵向下,鼻孔朝天,大瞪着的两眼刹时闪起奇妙的光彩。最叫人吃惊的是,她全身像打过气,筋肉全绷了起来,匀合结实丝毫不见瘦相。“这马八成是匹跑马子。好的跑马子一跨上人,都是这个样,都是这个样。走,快去和咱爷爷说说去!”没想到那老人家听完他的推举反而骂了起来:“你们懂个屁!跑马子哪有这个架势的?哪有牝子?哪有补瘸不瞎,三十块钱就卖了的?你们还想骑骑?要骑,先砸断你们的腿!就算是跑马子,好好的被卖了,必有杀主之心!母鸡中打鸣还要公鸡咋?”在老爷子呵斥的空当,猛然间我的主人看见那马哭了,眼泪顺脸吧嗒吧嗒直往下淌。他想把这个发现告诉祖父,又怕引起他更多的火气,举出她更多的罪状。他的叔伯兄弟是根独苗,命相与属马的相尅,他母亲从来就不让他靠近马,对这样一匹马,当然就更应该小心了。从此,他只能老远地看看这匹马。说也蹊跷,这马一见他就低低地叫一声,声音几乎听不见,可是能震得人身上不知哪块地方的肉痒痒。我主人就是这么说的。
光听主人讲,我竟忘记了吃料。我问主人:“您叔伯兄弟的小名叫什么?”遗憾。主人误解了我的意思,竟以为我嫌麦粒拌得太干了呢!
主人讲的那匹马是谁?听我母亲讲,她曾遇到一个伯乐,是个七八岁的庄户孩子。她永远怀念他。他的名字叫“狗子”。
“有一年,我牵着那匹马,和祖父及我的弟弟一块赶大集,准备籴些黍子。将到集市北口,忽然……”我的主人不知他讲的故事对我产生的影响,他见我听得全神贯注,不再嚼草,就问马夫:“它今天怎么吃草料这般少?”
听故事的马夫猛被一问,打了个愣怔,随着马上立正站好,很小心地试探着回答:“许是嫌食……”
马夫真冤枉我。主人不知道他曾多次借我嫌食为名捞些外快。我的主人待我极好。听别的马夫议论,他每月要为我花好几匹军马的钱。实际上我平日不过是白水料豆而已。其实马夫的可憎,不在于他尅扣我的食料,而是他把我阉了。
上年驻军团级以上的军官,不知为什么要去同登S山。这山很高很陡;通到山顶是一条十一里长,勉强能容一匹马通过的山道。军官坐骑当中,有匹毛色如回回红毛缎子一样的小母马,美极了,我对她印象很好。一踏上山道,二师师长的马便向前冲去,欲想向她显示自己的才美。另外还有几个团长的马也冲了出去,竞相炫耀自己的骁勇。他们这样爱出风头,未免太不含蓄了。我有意落在后边。那匹小红马也落在后边,大概她有心在我一前一后地走着。待她和我并头时,我向她说:
“他们傻子似的乱跑!这并不是非跑不可的。还是我们这样好。”
小红马瞅了我一眼,像在自言自语:“跑在前头的是二师师长的马,出生在阿拉伯!”
在我们当中,出生在阿拉伯,就好比中国学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不管出生在哪里,首先得会跑。您瞧,他跑的步伐不对,前腿老是同时抬起。”大概是认为我在吹牛皮,小红马不以为然地掉过头去。我有必要让她知道我是什么材料。我一阵风冲了出去。
这时,领先的几匹公马都按材力排成单行。走入山道特别陡峭的一段,我很轻易地超过母马和阉马,进入了他们的行列。我知道小红马必然注视着我。我时常回顾身后,却故意把视线偏离开她。我全身雪白,在一片春绿的山道上,自然十分醒目,非同凡俗。我跳进没有路的丛草灌木里,踏着碎石块向前猛冲。我超过三匹从日本人手里弄到的大洋马,又越过一匹四蹄雪白的铁骢马,头已和二师师长的马尾相连了。我的主人也是师长,我岂能给他丢脸?前面那个弟兄发觉有人追了上来,就左右摇着屁股,摆撒开大大的尾巴,加快了步伐,企图阻止我超越。我听见他的主人大声喊:“道兄,你疯了?小心折了马腿!”话音未落,我已冲出没有道的地方,远远地绕到他的马前。不一会,他已被我落下很长一段路,在我身后变得有一截铡好的谷草那样大小了。一半路过去,我回望身后,除二师师长还骑在马上,其余军官下了马,牵着马爬山。主人多次劝我停脚让他下马,我都拒绝了,直到山顶的平坦地带,我才站住。这时我的主人翻身下马,一把搂住我抖个不停的腿,竟然哭出声来。
不多时,二师师长也骑马上来了,随后,其他的马也都让自己的主人陆续牵了上来。小红马也被牵了上来。
我见小红马上来,便全力抑制住双腿的抖动,不想腿不争气,仍然颤个不停,我真惭愧。然而,她不但没像我预料想的那样,见我不停颤抖的腿而刻薄地挖苦我,或者干脆不注意我的存在,一身傲气,而是讨好地凑过来,试探着用月牙齿轻轻梳我的脊背,又把脖子不停地在我腿上摩擦。我极为恶心,便不自觉地摇摇头,向后退了一步。乱子发生了:她没了依靠,猛地歪倒在路沿下面。要不是这下面有段坡地,它就会永远离开黄土之上,蓝天之下。
人们的上司误解了我的行为。他下令:凡他统领下的马,只要是公马,一律去势。这可得意了我的马夫。他用绳子系住了我的一条前腿,趁我不在意的时候绕到我身后,把我的后腿也缠住,猛地一拉;把我绊倒,动了刀子。我的爱沾便宜的马夫当然极愿做这种歹事:他会把摘来的睾丸切碎,和辣椒炒在一起,吃得有滋有味!
我的主人和二师师长,在我们去势的那天,都告了假,去酒家借酒消愁。他们喝醉了,不但无缘无故打了人家,还向人家的水缸里撒了尿。我知道,他们是为良马绝后而心中难受。
主人非常疼爱我,有此演习,要渡一条很宽的河。别人都骑在马上,让马夫他们泅水过河,唯有他例外。那天他穿着一身新军装,特漂亮。当我的前蹄踏进水里的时候,就请求主人给我松一下肚带。他误解了我的意思,连忙翻身离鞍,拽着我的尾巴跟我泅水。我深知主人的诚意,只得运足气鼓断肚带,快游向前,拖他早到对岸。他的同事事后都笑他,他却说出一席让我感激涕零的话:“有什么可笑的?这马跟着唐太宗,少不了名垂青史,影照丹青;跟着一个庄户人家,只有拉耙拖犁;它跟着我,虽说比跟庄户人强些,可怜还是大材小用了,太委屈它,我得对得住它!”
眼下从他和马夫的闲谈里,才进一步了解他疼爱我的原因。他祖父买的那匹马,让他认识到马显示才能的大小,得随主人的位置来定。
“主人,你可有个名叫‘狗子’的叔伯兄弟?”
主人没听清,他走过来围我走了一圈,又把我的蹄子挨个抬起来看看,似乎在否定心中先前的一个推测那样,摇摇头,然后对马夫说:“去抓一只马蛇子,用草包好喂它!”
马夫回答“是”,但迟迟不向外走。他显然和我一样,迫切需要听完主人讲的故事。他装出就要往外走的架势,却有意提起主人刚才没讲完的话头:“您老人家那一带,给牲口泄火,不用远志汤吗?”
主人看穿了他的心思,笑了笑,又讲了下去。
“我不是讲到赶集籴粮来:哦!我们到了粮集的北口,才发现前边过队伍。这么多的兵士排队走过,我们不太容易看得见,当然要停脚看热闹。这时一辆汽车开到我们跟前,吱呀一声刹住车,紧接着从里边钻车一个军官,直朝我们走来。”
“他并不看我祖父,只是打量着我们的马。我祖父不知所措,好一会,才醒悟过来,急急忙忙地回答:‘老总,你不嫌这马不中用,你就牵去吧,花什么钱!’‘这怎么行。不用讲虚套,该多少钱,你要吧。’我祖父犹豫了一刻,才鼓足勇气,狠狠劲说:‘三十块,行不行?’‘行!来,数三十块大洋来。传令兵,你骑骑看!’‘是!’随着,传令兵就跳上了马背。和那回我叔伯兄弟扶它脊梁时的情形重演了。只见它的头忽然地抬起来,四肢蹄子在交替踏个不停,鼻子哼哧哼哧地响着,传令兵一个‘跑’字还没说完,它就‘嗤’地一声窜了出去,转眼就跑到了队伍的前头。等它蹄下的黄尘消散净尽,大路尽头,已看不清它的身影了。‘哈哈!大爷你不知道吧,别看它是个母,可它是匹千里马。千里马都是公,还有方九皋的餉!’军官急急钻进汽车,追那白马去了。
“买马的人当时是个旅长。后来知道,这匹马驮着他出生入死,立了大功,还给他生过驹。可是我祖父却觉得赚了大便宜。当时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揣到我怀里,一份揣到我弟弟怀里,这还不放心,又反复在我们揣钱的地方摁着,说:‘这个老总一会就后悔啦,准会追着退马。快点,你们一个从南门出去,一个从东门出去,不准停下,赶忙往家里跑!’我的弟弟一听事情性质严重,一边呜呜地哭,一边双手捂住装钱的地方,撒腿就跑。我倒没哭,只是没命地向南跑。跑出三两步,我听见祖父自言自语地说:‘我行了什么好。要是像俺老兄,只一个孙子,不就麻烦啦!’”
他老兄的独根孙子是谁?如果是那个叫“狗子”的小伯乐,那么我的主人爱我,定是对自己过去不识良骥的追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