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想想自己的小学,严格说起来真算不上受过什么教育,五年时间学回来的就是识了些字,学了拼音。课程是“万岁”“阶级斗争”之类的内容,好在当时老师也不明就里,没有灌输太多“思想”,所以,小时候学认字没有受到内容的污染,时至今日,我从内心感谢老师的“无知”。
可能是受父亲太渴望认字读书的影响,从小,我就对文字有一种迷恋,不拘什么书报杂志,但凡有字我就爱看,小时候家里没有书,大队(就是现在的村)有一份报纸,每年都会把旧报纸打捆放在一个不怎么严实的库房里,我曾从窗户钻进去偷报纸看,那时报纸的版面最醒目的是“最高指示”,最大篇幅的文章是周总理欢迎外宾的祝酒词和外宾的答谢词,当年这种文章的一头一尾我都能背过。父亲不是党员,家里连最常见的“毛选”都没有,带字的一本线装书全是繁体字一句也看不懂,因为这种纸很薄容易过油,都被家里卷成灯芯做了照明的材料,剩下几页被母亲当成了夹“鞋样”的夹子,直到我上大学后,回到家里偶尔翻看,才知道那是一本《诗经》,最晚也是民初版的。残破的《诗经》曾经引着煤油伴我夜读学习,也算是是给过我知识的光亮。后来想,如果当时家里有人知道这是一本珍贵的经典,教我几句“关关雎鸠”,我的命运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敌后武工队》,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水浒传》,前一本传到我手里时几乎没有书样了,后一本感谢大批判的年代让它作了批投降派的反面教材才会被我看到。第一次接触唐诗宋词是到了高中以后,班上有同学有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我借来后,就像阿里巴巴走进藏宝的洞穴一样兴奋,整整抄了一遍,之前,从没有见到如此多的诗词。中学的语文老师看我对读书有兴趣,就额外给我加大阅读量,借我一些书看,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古文功底深厚,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就是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培养的。上到中学有了一点读书的能力,书也渐渐多起来了,我开始到处找书看,春节走亲戚,亲戚家有一套《纲鉴易知录》和《佩文韵府》,我费了好大的心思将书借到手,限期归还时,我根本就没怎么看,因为借这些书纯粹是叶公好龙,当时,没有阅读这些书的能力。但,爱书、嗜书的癖好已经开始养成。
熬过十年寒窗,终于考上大学了,还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尤其是文史专业在国内曾一度很有影响力,很多专业在国内领先,我报的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到大学后,才知道自己竟是如此的浅陋,听同学聊天,人家嘴里一秃噜一秃噜的名词压根就没接触过,所说的书籍根本就没见识过,不免心生出些许自卑来。当我来到图书馆,看到望不到尽头的书架,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书籍,顿时兴起望洋兴叹的感慨。对我来说,图书馆的书籍可谓应有尽有,我暗下决心刻苦读书,来弥补少小无书可读的缺憾。
开始读书有点饥不择食的样子,因为自己看书少,凡是带字的都想翻看一下,听人聊天提到的书名就想借来阅读,渐渐,自己开始有了选择,对那些高深艰涩的书籍暂时放弃了,因为读不懂,对那些热门的文章读过之后因为没有太多收获慢慢也就淡了。
因为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影响,我们那一代读书人大都迷恋过美学和哲学,记得当年有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要求学生们分组给教授家里“送卫生”,我们小组有几个美学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抢到了周来祥先生,当时周先生风头正劲,他的“美是和谐”论与李泽厚等人形成对峙,很受我们这些似懂非懂的学子的崇拜。选择去周先生家,有点学术朝圣的感觉。去到周先生家里,看到的几个房间地上桌上触手可及尽是书籍,很乱,很有书香气,作为一个美学家,经过那么多的运动,周先生自然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和自己需要怎样配合,他让我们什么也别动,家里不需要我们帮忙整理,说是自己习惯了这份乱,整理了反而不好找东西,但是会向系里反馈我们的“文明礼貌”行动。接下来,就和我们聊起了学习,当几个“半吊子”美学爱好者问到如何学好美学的时候,周先生语重心长说道:“学习美学,首先要学习哲学,美学的基础是哲学,不懂哲学很难把握美学。”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话,周先生也是有问必答,可时隔三十年,只记得这几句了。也正是这几句话,让我硬着头皮读了几本哲学方面的书,而我们好几个家境算是不错的同学还买过一些哲学书籍,估计直到今天,他们的书架上会有几本商务印书馆八十年出版的哲学译丛。也就从那时,我知道了康德、黑格尔、萨特等哲学大师的名字,也零零散散看过他们的一点文字。
在大学真正有兴趣的课程依旧延续了高中培养的一点兴趣的古代文学,一段时间,对话本小说尤其着迷。中文系的学生除了能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自己系里有一个规模小一些但针对性更强的资料室,更方便我们借阅,后来这里就成了我留恋不舍的地方,几乎把能看见的所有话本小说都看了一遍,今天想起来,自己当时正是青春期,那些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就像白日梦一样满足了一些意念。后来准备写学年论文(大二作业),我自己选的题目就是关于话本小说的,当时正值比较文学兴盛,我设想,通过比较三言二拍与《十日谈》,从文学的角度探求东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与西方文艺复兴阶段的异同。后来,材料看得越多,越难以下笔,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写作能力都不可能把握这样一个大题目。临时抱佛脚,把题目换成了《阮籍“咏怀诗”的出世与入世》,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萧华荣先生,萧老师给我的成绩是优。这鼓励我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尤其是建安到正始期间的文学和哲学演变发生兴趣。后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这一时期的,题目还是萧先生准备自己写的《从雕虫到雕龙——汉魏六朝文学观念的演进》,他把题目和找材料的路径给了我,由着我去折腾。对魏晋的兴趣持续到很久,直到如今,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章书籍我还会特别的关注,书架上有多种这一时期的专著,其中就有两本萧先生的大作《华丽家族》与《簪缨世家》,都是老师送给我的。收到《华丽家族》时,我和同学一起写了书评,《青岛日报》《文汇读书》都给予刊发,成就了一段关于师生读书的姻缘佳话。
喜欢读书的人一般都会渴望拥有很多书籍,买书藏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为什么说是奢侈的梦想呢?因为缺钱。大学四年,我是享受二等助学金的贫困生,当时一等助学金发放目标是老少边穷,而我的家乡地处半岛中部的昌潍平原,历史上不富裕但也能吃饱肚皮,相比当时的临沂老区要好一些,比陕西老区就更好了,但我们家收入低,属于相对富裕地区的困难户,所以学校给了我二等助学金(现在想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还是有点的)。记得助学金是19.5元,家里穷,给的钱少,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有点紧张,买书几无可能。饶是如此,我还是省吃俭用买过一些喜欢的书,好在当时的书实在便宜,我买书的范围,就是自己的喜好,这个范围里超过一块钱的几乎没有,直到如今,这些装帧简单,朴素雅致,不事张扬的薄薄小书还是我经常阅读的对象。后来我去过很多人的家里,差不多读过书的人家里都会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摆放着精美的书籍,很新很好看,但是在角落里,会有一些我说的八十年代的旧书,我看到这一情景都会向主人说道,这些好看的精装本就是装点门面的,我们的知识恐怕十有八九是拜角落里的小书所赐,大家四目以对,相视而笑。从书籍的装帧和买书的态度上,大致也能看出一些社会风气的变化,这也算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仔细琢磨,面子多的时候,里子一般就被忽视了,一个读书人,当你在指责社会上的面子工程盛行的时候,回家看看自己的书架吧!
扯得有点远了,赶紧回到买书看书上来。真正能舍得花钱买书还是这几年的事,我买书有两个原则,一是买来一定要看,不跟风,不贪全;二是有平装本绝不买精装的,我一向认为,平装是用来读的,精装是摆着看的。第一条坚持得不是很好,有两个原因,随着年龄增长,读书越来越吃力,读得时间一长眼花头晕效果很差,不能坚持了。另外,买书的数量多了,远远超过阅读的速度,一本书往往在书架上呆好几年才轮上阅读,这时候可能又买了新书。而有些书却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重读,这样的书就像老朋友,隔三差五的见上一面,每次见面都会增加新感情,获得新收益。而这些书往往就是那些平时在角落里不显山不落水的旧书,像那本刘熙载的《艺概》如今就在床头,这本小书已经陪伴我三十年了。再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百读不厌,可以当小说看,可以当散文读,可以参悟,可以体味。张岱的《陶庵梦忆》也是如此。读的遍数多了,不免技痒,还狗尾续貂点评过《阅微草堂笔记》和《陶庵梦忆》,正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我很羡慕民国时期在琉璃厂淘书的文人们,他们总能在那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书,1993年,工作中一度失意,被赶回家反省悔过,我也试着去地摊上淘书,可惜青岛没有琉璃厂,根本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好书,到时在胶州路上见过买“黄”书的爷俩,不知从何渠道弄了些粗制乱造、淫秽不堪的小册子摆摊贩卖,老的有六十多岁,儿子也得三十好几了,整个两个不着调,看人的眼神也充满着邪性,走到摊前,他们会猛不丁压着嗓子说一句:买书吧,草逼的。搞得你就倒像做了贼一般赶紧逃离。不过地摊淘书也不是一无所获,2008年12月17日,就曾在山东头一个地摊上淘得一本品相上佳的《十日谈》,人民文出版社的版本,花了不到五元钱,一本《杨万里诗选》,品相稍差,也才二元钱,最值得炫耀的是淘得一本《日本的战争责任》,若貴泰雄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位若贵泰雄先生1924年出生于青岛,十七岁以前在青岛上小学和中学,1944年入伍,战争结束后复员。买这本书主要是看到他出生于青岛的背景,当时有一个想法,能有机会访问他,做成一部纪录片,这一想法恐怕只能是一个想法了,看来机会渺茫了,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此事也在此列。还有一套书《先知三部曲》也是在一家很不起眼的书肆淘得,时间大约是在2003年夏天,当时去淄博出差,晚上东道主设宴款待,酒酣耳热之际我逃席来到酒店旁一家小书肆,见里面书籍摆放横七竖八,我便随便翻捡,在一堆书中找了它,拂去上面的浮灰,完全是一套新书,品相很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波兰人伊萨克·多伊彻,传主是著名的托洛茨基,三卷的书名分别是《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限制——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译者前言中说道:“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这套书在书架上放了好多年了,一直没静下心阅读,2015年,我将用心去读一遍,或许会给我许多新的见识,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对制度。就像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读完几年前买的约翰·托兰所著《希特勒》和路德维希所著《德国人》一样,不一定非得急着逼自己阅读此刻读不下去的东西,阅读也需要积累,需要缘分,需要心境。
到目前,最幸福的读书时光是在美国OSU的汤普森图书馆(William Oxley ThompasonMemorial Library)度过的,1804年成立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是以这所大学第四位校长也是贡献最大的校长的名字命名的,为全球知名图书馆之一,它知名的原因在于它的馆藏丰富,有200万册的藏书、11,000种定期刊物、160万份缩影片,并且与美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网络联机,建立良好馆际合作,图书馆各部门均采用全面自动化操作系统,每年约有33万册的借书量记录,各种类的藏书,总计有约有200万册,十分惊人。2013到2014学年,有幸作为这所大学东亚语系汉语旗舰工程的访问学者在这所大学生活了十个月,工作之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图书馆,除了藏书丰富,这里也是大学最舒适的地方之一,是这所全美最大的大学引为自豪的所在。图书馆的3M整个一层是东亚语言文学类藏书所在,见到最多的是汉语、日语和韩语类图书,图书可以随意取阅,对我这个英语不好的阅读者真是方便至极。美国社会对于言论自由崇尚备至,在这里不存在禁书之说,可以说我想看的书籍这里应有尽有,正是在这里,因为工作需要,我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历史专著,余英时先生的一些学术著作,读了在大陆难得一见的很多所谓禁书,可是最值得一说的是,这里让我沉下心来阅读《苏轼全集校注》。煌煌二十卷《苏轼全集校注》是第一部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集、词集、文集进行全面校勘注释编年辑佚的大型古籍整理著作,代表了当代苏轼诗词文集整理的最高水平,为苏轼研究提供了一个校勘精良、注释完善、编年准确、评论充分的上佳版本,为宋代文化研究呈献出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本书由四川大学的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先生担任主编。耗时二十余年,其规模800余万字,大32开,繁体竖排,精装,全20册,126卷,包括苏轼诗集校注50卷,词集校注3卷,文集校注73卷,另附苏轼文集辑佚6卷。我一向喜欢苏东坡,零散阅读过他的诗、词、文等各种文体,但都不是系统阅读,以来没有那么多完整的时间,二来版本太多无从选择,这套全集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架起了一座桥梁,二十卷全集在美国我读了差不多一半,另外一半将是我今后阅读的重点。为更加了解这位千古第一达人,我阅读了林语堂撰写的《苏东坡传》,王水照、朱刚撰写的《苏轼评传》,眼下正读李一冰的《苏东坡传》。这些阅读,使我深刻认识到知人论世的重要,阅读的乐趣就在于通过作家的作品走进他的内心,和他交流,获得教益。
进入网络时代,最大的方便是可以足不出户可以遍游天下书店,自从学会在网上购书,从网上已经买了不少书籍,既便宜又方便,人越来越老,对于老年生活有很多的担心,如今再也不用担心买书的事情了,只要脑子没糊涂到不明事理的程度,就不用担心买不到书了。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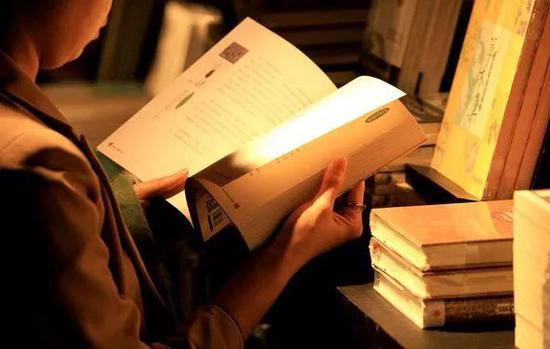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