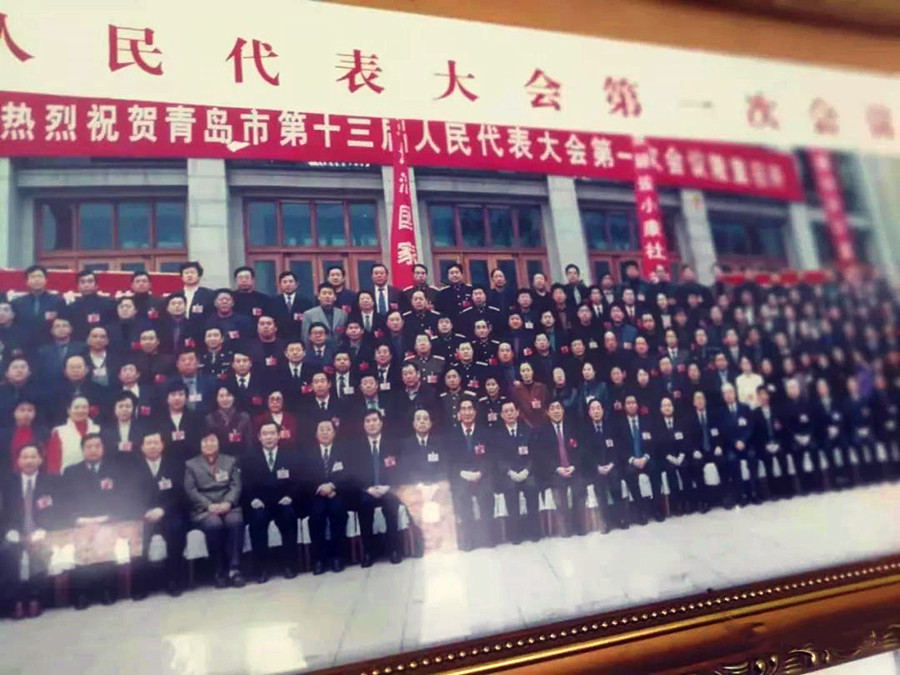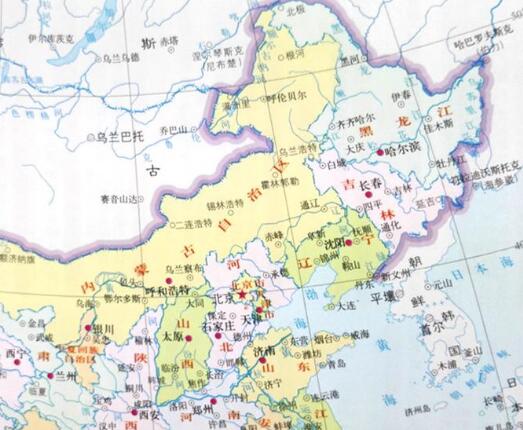上图是父母在高中时与剧团同学的合影。第一排左三坐着手托腮者是父亲,他右边第三位穿黑衣者是我母亲,前排站立最右边穿白衣者是国民党灵甫号③起义的士官赵松阳。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父母通信集《自从有了你——宁青两地书》中多次提到他。
星期天,吃过早饭,父亲就找他的老同学去了。弟弟在看电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拿过几张白纸。
我总是想写,想写。其实谁也没要求过我,可我就是想写。现在写点什么呢?
我抬起头,望着窗外,透过薄雾一样的细雨,是灰蒙蒙的天空,拥抱着城市灰蒙蒙的水泥建筑物。
我一下想起今天是清明节。
手里的笔立刻流出这样的句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一遍又一遍默写着这首老幼皆知的古诗,越来越惊诧:这一个个再简单,再朴素不过的字,一经诗人之手组合起来,竟有千古销魂的魅力!我也不由得感叹自然规律真是神契,大概多少万年前多少万年后都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吧!有人敲门。
我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弟弟已经把门打开了。
“请问,这是禹轩同志家吗?”
是一个男人很客气有些沙哑的声音。哦,是找父亲的。
“是呀,他出去了。”
“啊——!”
一声怅惘地叹息,紧接着急迫地追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中午能回来么?”
大约看他不愿离去的样子,弟弟把他让进父亲那间客厅兼卧室的房间。
我仍坐到桌前,涂抹纸张。真的,当我冥想时,当我和别人清谈时,总感到“惶惶然”,而一拿起笔来,不管写出的东西多么不像样,也觉得踏实。
弟轻轻地走到我面前,有些神秘地说:“姐姐,这人是从即墨来的。”他将“即墨”二字说得很重。
“呦,挺远的,我过去陪一会?”
弟弟想说什么,但只是点了点头。那人端坐在沙发上,看样子有五十多岁。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五六十年代的蓝布干部服,帽子也是那个时代的。脸和手很粗糙,黑。神情有些拘谨但很斯文,我知道他是一位农民型的知识分子。自从父亲落实政策从农村回到青岛后,我家常来这种人。中国之大,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人从土里钻了出来。
我坐到他对面。他很亲切,很温和地望着我,这目光很陌生。因为来找父亲的人,对于我和弟弟一向很少留意,可又觉得这目光很熟悉,在哪儿……
“我是从即墨来的,我姓赵——你不认识我了。”
我突然想起——是他!“不,我认识你,你在即墨×中,你是我爸爸妈妈的中学同学。”他连连点头,十分快慰,我的心却沉重了。那些仿佛从没存在过的事情,从记忆的最深处浮现出来。
“我这次是来青岛治病的,鼻咽癌。就住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治疗。”说着,他转过脸,面颊上隐隐有几道红药水画的杠杠。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心平气和地讲自己患癌症。也许,我显得震惊,他竟然宽慰起我来:“这个病,在癌里算轻的,只要治疗及时,活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都有。我这是初期。”我虽然极力克制自己,但仍忍不住细察他的面部:皮肤被炙烤过似的发乌,毛孔粗大,他身上,也散出一股消毒水的气味。
他的目光温柔而执着地停留在我的脸上,仿佛在寻找,在印证……“你长得不像你妈妈,像你爸爸。你弟弟像你妈妈,真像!”我一惊,只有母亲说过我不像她,神情不像。我受不了他的注视,站起来,踱到他旁边的沙发前,坐下。我很为难,怎么告诉他母亲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她是怎么死的,用什么方式暗示给他呢!我知道,他对母亲很有感情。他并不看我,低声地,缓缓地说:“你妈妈的事,当时我就知道啦。”“那年,我‘解放’了,有一次,跟车到青岛市来拉水泥,我偷着跑到邮局,给农科所打了个电话,想找找她。知道了她死的事。咳——!”泪水迷蒙了我的眼睛,我把脸扭向一边。我真想毫无顾忌地放声恸哭一场,把五脏六腑吐个干净,为惨死的母亲,为艰难地活到今天的父亲,和这位同样艰难地活到今天却又得了绝症的叔叔,为所有那些过去了的苦难的日子。但我还是按老习惯,把这一切一切,闷在胸腔里。我悄悄伸出手指,把溢出眼角的那滴泪珠,拨了下去。
他的身体猛地俯下,双手捂住脸,然后,一只手摸摸索索地伸进裤兜里,拽了好几拽,才拉出一方幼儿园孩子擦手用的小方毛巾,另一只手掀开帽子,连头带脸地抹了一把。我看见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好一会儿,我才一字一顿地挤出这么一句话:“您、这、个、病,要、保、持、心、情、舒、畅、吧?”
“是啊,我现在的情绪很安定。确诊后,反而坦然了。”他平静,详细地向我叙述发病经过。
我盯着他,听到他的声音,脑子里却翻江倒海,眼前快速闪回着一个又一个画面,这些画面又叠印在一起,飞旋起来……
“朱文蕙!”“赵松阳!”1948年底,一个身着海军装的大眼睛黑黑眸子的英俊水兵,和一位短发齐耳的女大学生站在南京繁华的新街口大街上,惊呼对方的姓名:“你不是参加远征军去了吗?你怎么又当海军了?”
“抗战胜利后我就被保送到海军了,现在刚从英国培训回来,想不到,咱们在这里见面了,你呢……”
槐香飘溢的傍晚,金陵女子大学校门前。他们在散步。
“你说,咱俩是什么关系?”
“同学呗。”
“……”
……黑漆漆的夜,一艘起义了的国民党军舰出没在小山样的波涛里。蓦的,前方海面上升起一座灯火的大陆!甲板上,欢呼跳跃的水兵中间,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热泪,在他面颊上流淌。突然,那泪痕变作一道道红药水的印迹……
一位悲伤的农村妇女,紧抿着双唇,身边依偎着四个孩子,由远而近,由远而近……
信封。淡黄色的。落款“即墨×中赵缄”。我就是靠这个回忆,“猜”出他的,我绝不会“认”出他来。
我想大声对他说:“叔叔,讲讲吧,讲讲你,讲讲我妈妈,讲讲你们的少年、青年……你们经历的一切……”
我想对他说:“我一定要去看望您的妻子,帮助未成年的弟弟妹妹……”
但我说不出。
弟弟拿着雨伞走过来,说是要去找父亲。
他挺直身子,仰脸望着弟弟,喃喃地说:“不要去找了吧,还是不要去找吧。”那神情却分明是很想见到父亲的。
弟弟走了,我们便想到哪说到哪。
“你们家在农科所时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62年,我摘了帽子,很兴奋,去看你妈妈。你爸爸那时还在王村劳动教养。”
“你还带给我们一包面条鱼干。”
“是吗?你的记性真好。”
我怎能忘记,我和弟弟瞪大眼睛,看着他和母亲把那包用报纸包着的面条鱼,在我俩鼻子前推来推去。那淡淡的鱼香引得我们直咽口水。母亲一个劲说,你家在农村,比我们困难……可到底没拗过他。那包鱼,我们吃了好长时间,跟吃海米似的,一次只放一点点。
“第二次,是你爸爸解除教养回来。那次,我在你家住了一宿。住在里屋,里屋有个小炕……”他一一回想着我们共同记忆的那点情景,连一点一滴都不放过。唉!苦难中毕竟有些许使人留恋的事情。我们的谈话就沉浸在这让人心酸的温馨里……
楼梯上响起叽叽嘎嘎的说笑声。宣容和芳芳来了。我不愿让别人窥视到只属于我们所有的那个感情世界,便迎上前去,大声嚷着:“对不起,家里来客人了,今天我就不去书店了,你们去吧!”不由分说,便送她们到楼下。
细密的雨,迈着轻捷匀齐的脚步,向我包抄而来。柏油路像是铺了一层薄冰。反射着幽幽的,灰色的光。我很难过。虽然,我知道,这就是生活。但我仍然很难过。
我想起他给母亲的那封信。有一回,我注意到母亲看完一封信后,哭了。等她挂上“白专分子”的黑牌到大田去劳动后,我便掀褥子拉抽屉地搜,终于找到一个淡黄色的信封,落款“即墨×中赵缄”。
“……看了你的信,得知你说为了孩子想和禹轩离婚,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他第一次向母亲讲到他在农村的妻子,他的家庭。
“我出事后,简直绝望了,想一死了之……她来到学校,生怕我想不开……现在,我们有了四个孩子。没有她,没有孩子们,我怎能坚持到今天……”他写了很多,但没有一句直接责备母亲的话。我一边看,一边流泪。我想把这封信永远保存起来,但母亲却把它烧掉了……
雨,仍在斯斯文文地下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温暖湿润的气息。就像这无声无息地渗入土地的雨水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浸润了我的心灵。我慢慢走回家去。父亲已经回来了。我听到他们在低声谈话。
吃完饭,他便告辞。
“不要去看我,也不要买水果、罐头什么的。我这不是挺好吗?你们这六楼,一口气就上来了。”说着,他还做了几下高抬腿动作。依稀辨得出,当年是个水手。
父亲找出雨伞,执意送他回医院。
我站在阳台上,俯视着两个黑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地间。我想起一首长诗的开头: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从死的土地上孕育出丁香掺揉着回忆和欲望……
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日
汐注:三年后赵松阳叔叔去世,又过了两年,他的小女儿从上海某大学毕业,到青岛来找工作时来到我家,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很快,她就在青岛的大学找到了教职。2017年当我整理这些资料时,才知道她父亲是“灵甫”号驱逐舰起义的官兵,是从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又从天津到达解放区的。“灵甫号”驱逐舰共有77位起义人员,后转赴东北,进入安东海军学校,参加了海军建设。我家原有好几张赵松阳叔叔着中华民国海军军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装照,沿帽上黑底烫金字显示出两个时代,大大的眼睛萌萌地望着这个世界。我小时候还问过母亲:为什么这个人又是国民党又是解放军?母亲说,“他是起义的”。“文革”时,这些照片全都烧掉了。
【注】
①“难童保育生”: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我11岁的母亲故乡安徽蚌埠沦陷了。姥爷姥姥带着6个孩子随逃难人流扒火车、步行到达当时尚未沦陷的汉口,住进难民营,3岁的小姨得了麻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就在全家陷于绝境时,由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董事长,邓颖超等各界人士任理事的“战时难童保育会”成立,在汉口街头分发传单,收养无家可归的难童,一船船地运往大后方。姥爷姥姥就把四个女孩,大的13岁小的5岁全送去了。难童们被送到四川乐山的保育院。保育院条件很艰苦,吃的是糟米饭、咸菜。经常吃不饱。但在保育院可以上学。保育院毕业后,母亲和其他三名保育生考取了私立女中(初中),由保育院出面交涉,学校免除了她们的学费。每月回保育院背口粮交给女中。寒暑假就回到保育院。
②国立六中:同样在1938年,刚上初一,才12岁的父亲刘禹轩跟随从山东大后方撤退的三千多名师生,步行七千余里,跨越五省,于1939年初分别抵达四川的绵阳等地。所谓国立中学就是流亡师生组成的中学。由于由民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资助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学校利用空地种菜,建手工作坊,自制文具、纸张等书费全免,课本一级一级相传),住得条件很艰苦,大多是借用废弃庙宇、老屋。流亡学生牢记国仇家恨,学习特别努力,高考升学率非常高,1944年抗战最后时刻,大批流亡学生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远赴印度、缅甸。
③灵甫号:“灵甫”号驱逐舰是世界上第一种专用护航驱逐舰,1948年5月,英国政府租借给中国海军,租期五年,为纪念国军名将张灵甫,以其名字命名该舰。1949年5月“灵甫”舰共77位起义人员在香港起义,后乘船后转赴东北,进入安东海军学校,参加新海军建设。
潮汐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