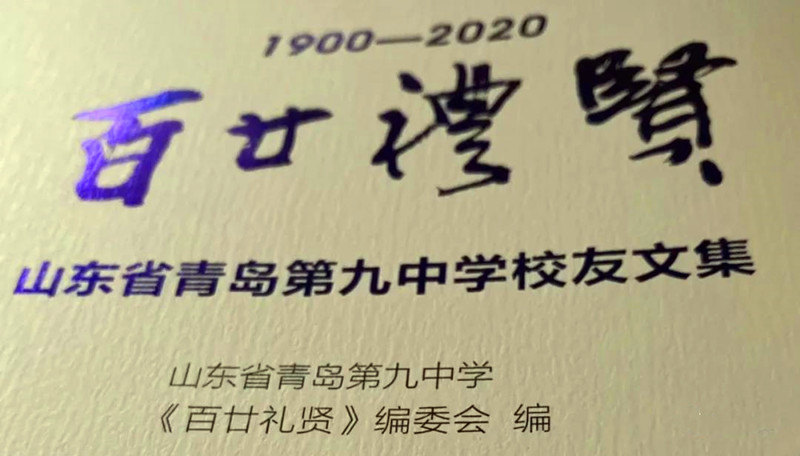译者对“濒危的文学”这个提法很感兴趣。不过译者有所不知,这个“提法”不过是作者用偏激的语言指出法国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苏联东欧时期,那里的文学与人一样,都是命运多蹇。
用偏激的语言突出要表达的意思,是西方人的语言习惯。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不可误以为文学真的“濒危”了。
1.文学不管怎样“濒危”,是不可能消亡的!
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自从有文字开始了人类文明的进化,文学就与人类休戚与共到今天。文学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现象。只是这种现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罢了。
众所周知,所有的文学都是审美意义上的。人人都有审美意识,都有审美需要,这是人类的天性。所以能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文学,与人类地久天长。
2.托多罗夫推崇的“为美而生活”,不是译者所理解的那点意思,并非那么简单、那么浅薄,并非在唯美主义层面上的生活方式。
“为美而生活”类似于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息”,都是指人生要活出点审美意义来。不仅仅是审美的需要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坚持审美的追求、审美的创作,作出审美的贡献。这都是所有的诗人、作家、及其他文学艺术工作者,共同的生活需要。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只是审美不是局限在译者谈到的意思,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对称和谐与生活中的赏心悦目,在文学作品中的重放光彩;审美与“审丑“是相辅相成的。“审丑”是对审美更深刻的补充,是在相反的方面,用凛然的笔法对美入木三分的剖析。
朱自清用生动的语言勾勒出“荷塘月色”的美妙意境;鲁迅用犀利的文字彰显人间的丑恶底色,难道不都是体现了作者对于审美的向往与追求?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对那些龌蹉人、卑鄙做法,丑恶现象的“审丑”,又何尝不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审美?
这其中的道理连农夫村姑也都明白,他们有时会说某人长得很丑——这不是暗含着他们质朴的审美评价?
所以译者不吝笔墨地批评托多罗夫的“为美而生活”是不足、是缺陷、是多么的偏颇云云,除了显露译者审美的陋识拙见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3.译者很同情、很理解托多罗夫对苏联东欧时期文学遭受摧残的憎恶。不过译者话锋一转用“但是”,罗列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与舒拉的故事》《毁灭》《铁流》等作品是那个时期的文学成果。试问译者:这些“文学成果”,在俄罗斯、乌克兰、东欧各国,还有人看吗?
4.译者把《阿Q正传》归入革命文学的行列,这是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不能苟同的。大家都知道:革命文学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即首先是以讴歌革命,讴歌革命人与革命家,讴歌革命事业与革命理想为主要内容的。译者怎样从《阿Q正传》里读出了这种“讴歌”?
5.译者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有风花雪月的文学,有卿卿我我的文学,有美轮美奂的文学;还有革命文学、救亡文学、为了正义事业抒写的文学,还有大我的文学……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译者在一万多字的译序中,始终没有说明白:文学是什么?译者罗列的上述各种文学,是在什么意义上都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这是个必须搞明白、译者却没有搞明白的问题。难怪译序中的谈文学,越说越糊涂了。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有其不可或缺的:
(1)文学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不是文学。
人道主义精神有着这样的要义:以人为中心,人是根本,人是出发点,人是目的。除了上帝,人世间没有凌驾于人之上的神圣与伟大。雨果在其《九三年》中有个著名的说法:在崇高的革命之上,还有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推崇自由、平等、博爱。凡是背离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都是文学的堕落。
(2)文学是审美意义上的思想情感表达。文学欣赏首先是领略审美意义上的思想情感。缺少这种审美欣赏价值的作品不是文学。当然这里所说的审美,涵有不可或缺的“审丑”方面。实际上缺少“审丑”的审美文学,例如小说若远离了“审丑”,都是片面的、或不真实的。
(3)“文学是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体现:
灵魂的复杂与深邃;
个性的生动与独特;
性情的执着与神秘;
人性的善恶与不定;
情感的无序与多变;
缺少“人学”的文学,不是文学。
这里概括的三点,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不可或缺。
所以,没有搞明白文学是什么的译者,提出“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就让读者不知所云了。所以译者关于“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说了半天,让人懵懂中不能不质问:你连文学是什么都搞不明白,所谓“文学非文学”,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命题,是目前学界见多了的、连作者自己也不明白的“故弄玄虚”!
试问译者:文学如果了缺少上述三点“不可或缺”,没有了审美价值,没有了审美情趣,没有了审美思想——读者欣赏什么?这样的作品,还会有读者看吗?
6.译者说文学是用那些非文学领域里的东西加工出来的。这个被译者自己视为重大“发现”的说法,让读者不能不奇怪:作为教授的译者,难道连中国人谈文学创作、谈写诗时,常说的“功夫在诗外”这句常识性的话都不知道?你还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发现”吗?
7.译者把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中批判法国的语文教学是“封闭性教学实践”“框定其理论的官方指令”——认定为“恰恰是托多罗夫与热奈特等文学前卫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殚精竭虑所要达到的效果”。
译者进一步认定,托多罗夫其实是法国文学“濒危”的始作俑者!译者的这个断言,说明他没有读懂《濒危的文学》:托多罗夫所谓的法国文学“濒危”并非现实中法国文学的“濒危”,而是指向法国在语文教学上关于文学课的指导思想与授课方法,背离了文学的原旨要义,避开了审美意义上的欣赏视角。
如果说法国有什么文学“濒危”,《濒危的文学》看重的,是法国文学教育可能对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
托多罗夫并没有指责目前法国文学是怎样的糟糕,哪来的译者所理解的“文学的濒危”?
再说半个世纪前的托多罗夫与热奈特文学前卫派,如何像译者认定的,造成了目前法国文学的“濒危”?译者在译序的长篇大论中并未涉及这个问题。译者不谈这个自己十分看重的问题,岂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实际上,批判法国的文学教育是《濒危的文学》中的主要思想之一。所谓文学“濒危”,在托多罗夫眼中,不过是法国错误的文学教育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罢了。
译者在译序中谈《濒危的文学》,东扯葫芦西扯瓢,末了留给读者一地鸡毛,成了佛头着粪的译序,不如不写。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