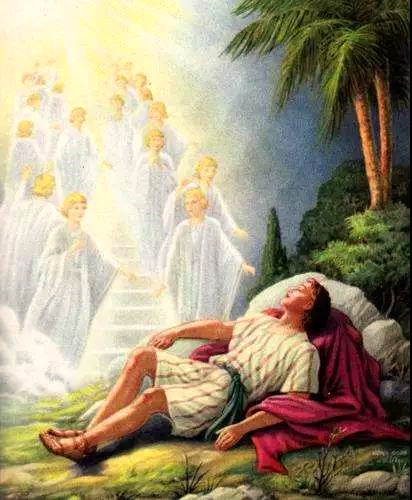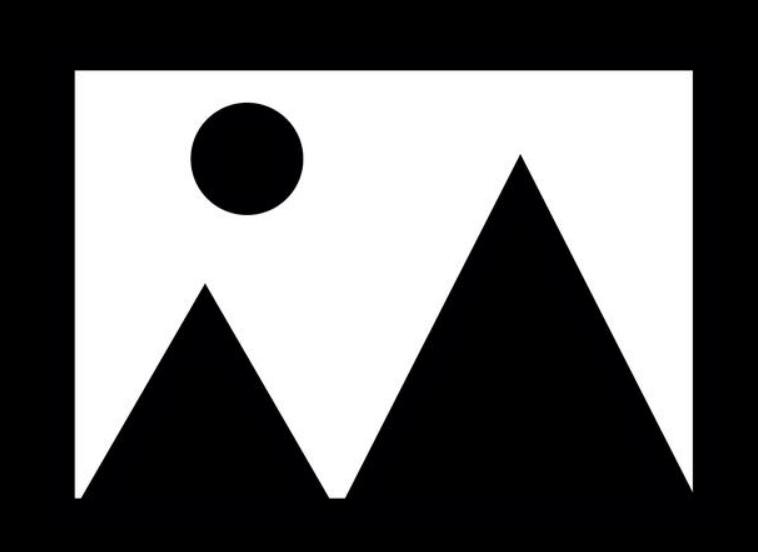我的答案是:依然有意义,并且这意义还十分重要。
原因之一:口头语言是人凭借自身的生物能力,在漫长的演化中习得的技能。它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便可通过人自身而实现。
后来,语言落成文字,人们通过熔铸铜器或是刻刀笔墨进行书写,对工具也仅仅只有“弱依赖”。像传说中的岳飞之母,一支竹棍、一把沙子,一样可以完成书写和教授书写的过程。书写时,笔可以视为手臂或手指的延长线。
而若是通过电脑、手机,使用表情或照片进行表意,则工具完全独立于人,甚至可能将人降到从属地位。同时,人对工具是拥有“强依赖”的,没有电子产品,信息便无法编辑、无法送达。
原因之二:语言史,即是一部人类文明史。语言文字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人类通过语言——即在对语言的创造、习得、运用、修改甚至是误读的过程中——定义着客观世界,也生成着自身观念,最终成其所是。
抛弃语言,即是抛弃人类自身的来历。
在人类历史上,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发生过很多次。但革命、演化未必就是正向的“进化”,而应当被视为中性的“演化”。技术是否更发达、使用是否更便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让人是其所是、成为其更应该成为的样子;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人”、实现了“人”,而不是异化了“人”、压迫了“人”。
所以,技术更先进,未必等于世界更合理,也未必等于人类更幸福。不少媒体已经有如此意识,所以才时常呼吁人们: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放下网络。
这样的呼吁,对大众而言总是显得廉价而无效。更何况,如果我真的放下这些,又如何读到你对我的这些呼吁?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可能放下一个个诱人的APP,重新退回到技术简陋的古典时代。就算是在那个时代,又有几个人真正拥有审美意趣、过着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不无讽刺地说,人们总是“有着非常健全的意见”,比如“宁愿选择消遣与狩猎而不选择诗”,而那些对此发出讥嘲的人则是一些“半通的学者”,他们通过这种讥嘲“得意洋洋地显出高于世上的愚人”①。
所以,无论在什么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相应的技术条件之下,按照最舒适、最便捷的原则过活。同时,也总是有人凭借丰富的精神、丰满的人性、活泼发达的智识度过人生。大家的世界观或许彼此难以通译,一旦相遇,不是你嫌我矫情,就是我嫌你头脑简单。在更多的时候,大家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各循其路,各自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
注①:语出《帕斯卡尔思想录》。
本文发表于《青岛财经日报·红礁石》2021.4.23 A8版
冯震翔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