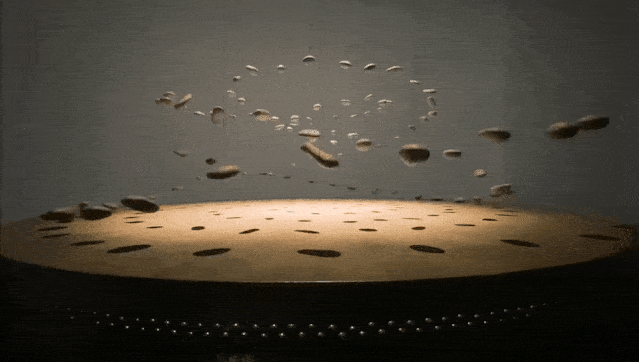前一部书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另一部书是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
我并没有因此而获救,反而在不断遭遇和面对“现代”这一词语时,陷入更深的迷途之中,没有归路。
我承认,始终以来,我并没有真正进入过“现代”。在以往所有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阅读体验与经验中,我所获取、理解和接受的美学信息,以及在潜意识里形成的审美取向,依旧是早期阶段的:所谓古典、所谓浪漫、所谓现实、所谓崇高、所谓神圣、所谓宏大、所谓真实、所谓忠诚……等等,我以为我在不断走入历史隧道,而实际上,抛却了身之所在的“现代”语境,“历史”不再真实。当它孤立的时候,当它零碎而混乱的时候,当它丧失了最根本的参照系的时候……它的意义何在?没有历史感的历史,无异于一只孤零零地钉在墙上的标本,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日落时分的满天彩霞”和旭日东升时的彩霞满天,有着怎样的不同?一个敏而深知的人,一眼就能从一幅油画的色彩中认出来,而我们凡俗的眼睛和心灵,只能被同样的瑰丽与绚烂所感染所震撼。因此,我们感叹不止、激动不已的情形,在缄默的前者眼里,是怎样的浅薄与可笑。那喋喋不休的赞美诗和伤春悲秋的情怀,在巨大的噪音和巨大的沉默中,变得无力而滑稽,就好像站在轰鸣的即将起飞的班机玄梯上,慢慢吟着“……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来跟恋人话别一样。
在不断遭遇的过程中,“现代”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对我而言,它成为一种检验心理承受力的测量仪,尤其是对一个自觉不自觉地已然接受并将自己交给了“传统的”、“古典的”美学原则的人来说,站在“现代”的门槛前,是一场灾难。
现在回想起来,温斯顿给我的打击与伤害已经不是最残酷的了,但当时,我不能接受。那织网结篱一般的文字,密不透风地将阅读的人封锁在一种绝望之中。他告诉并让你坚信一个事实:“人”的无望。尘世之上,除了强权,永不再有“人”和“人的一切”——人的品格、人的尊严、人的情感、人的理智、人的目的地……所有、所有,人将无所退守,就连头皮屑那么丁点的据点都不可能有。死亡乃至肉体上的苦难与折磨都是一种幸福,但你不能选择和拥有。屈服,彻底的屈服,是唯一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不是出路的出路。
温斯顿唤醒我的记忆,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但当时并未理解的电影《弗兰西斯卡》。影片的最后,弗兰西斯卡安详宁静地从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走过,面含微笑,像每一位幸福的公民一样。那美丽容颜上的微笑跟温斯顿最后坐在栗树咖啡馆里喝着杜松子酒的宁静与自由一样。
当你看完全部影片和整本书,到了这里时,你知道作者在说什么,但你已经什么都不能说。那是就连绝望都是一种奢侈的感觉。“微笑”里面已经没有弗兰西斯卡,但弗兰西斯卡的微笑是真诚和幸福的;“自由”里面已经没有温斯顿,但温斯顿在满怀感激地享有着。
这种时候,就连沉默都是无力和没有意义的,“表达”和“试图表达”,除了滑稽和可笑,没有别的。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做出来的每一个姿态,就在脱离你的一瞬间,便已彻底背叛,变成了一只会笑的鞭子,朝你抽打过来。
然而,人却不能不表达,就好像绳索中的猴子不能不挣扎一样。人想通过思考与表述而获救,猴子想通过挣扎而获救。但,那是不可能的。
对于猴子来说,人是看客;对于人来说,上帝是看客。置身于一种强大而冷酷的控制力中,任何挣扎都是徒劳无益的,挣扎的程度,只代表着可笑的程度。
因此,当我穿过奥威尔,再次进入《被背叛的遗嘱》时,曾经的不理解与不接受以及对昆德拉的所有排斥与对抗,瞬息之间土崩瓦解。读着他的文字,感觉没有比昆德拉更像上帝的人了。
第一个告诉我说奥威尔并不那么残酷的人是罗罗。她在一个回帖中说:如果跟《古拉格群岛》对比阅读,你会觉得奥威尔实际上要仁慈的多。
于是,我开始认真寻找这套老早就在留意却没遇到过的书。终于因一位朋友的指路,在一家非常小而偏僻的书店里找到了它。那是临近春节的时候。
《古拉格群岛》跟我已往间接知道而臆测想象的情形完全不同,对它的阅读障碍重重,然而,它所告诉你的事实,让你无法计较任何文字上的障碍和不习惯,哪怕缓慢,也只能不断地走向书的深处。至今,我尚未到达第二卷。
但是,就目前,索尔仁尼琴所提供给我的启示,并没有真正超越奥威尔,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讲着同一件事情,只是,索尔仁尼琴更加直接,他甚至抛弃了修辞与形式,不屑于讲述过程中的任何美感追求。
对他们的阅读,依旧没能逃脱对意义的寻求。跟随文字的过程,是一个残酷地面对“人”的彻底无望的处境的过程,它带给你的震荡是一种没有出路的绝望与灰心。
然而,昆德拉将这种巨大的、不无黑色悲剧色彩的绝望轻描淡写地带入日常中。“意义”早已消失,“人”又何需苦苦追寻并为了追寻不到而绝望?“人”在人的无所谓意义、也无所谓终极关怀的、一切都在相对与模棱两可中变成为谜的尴尬处境中,唯一能做的就是:笑一笑。
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将奥塔维欧·帕兹对现代精神的定义放在了唯一的最高的位置。
“但是幽默,请记住奥塔维欧·帕兹的话,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
以此为本,他追溯现代小说的历史,直达拉伯雷那里。小说的历史是对历史的报复。具有现代精神的小说,是引人发笑的艺术。“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不会懂得任何小说的艺术。”
但是幽默,“它不是笑、嘲讽、讥讽,而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可笑。”是“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其乐。”
但是幽默,它“不是人远古以来的实践,它是一个发明……”因此,“……它不是从来就在那里,也不会永远在那里。”
那么,之后呢?幽默不再,人将怎样?
“我的心抽紧,想着巴努什不再让人发笑的日子。”
因为,“没有比让人理解幽默更难的了。”
因为,面对拉伯雷,即便上帝会告诉我们,“请猜一猜!每一个答案都是一个给傻瓜的陷阱。”我们却依旧满脸庄重、前仆后继、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扑通”、“扑通”跳进陷阱里面去。
因此,他在追溯中是那么怀念“幸运的拉伯雷时代”,那时的人们是那么单纯而出自内心地为巴努什发笑,而不问意义。然而,在欧洲艺术之外,在“现代精神的发明”之外,人类不断地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以及存在寻找和树立着种种“意义”,并在这些“意义”的支撑与鼓舞中,走到了今天。那么,人又怎么能承认并接受“意义”的不存在呢?对于没有“意义”便不能活的人来说,面对“意义”的丧失,你让他怎么能笑得出?
因此,当他说,现代艺术的“旅行是短暂的”时,他指给我们看他称之为“第三时”的现代艺术“日落时分的满天彩霞”,这又何尝不是人类“日落时分的满天彩霞”呢?
他说,“一个意象追逐我:按照老百姓的信仰,要死的人在弥留之际,看见的是往日的全部生活在眼底浮现。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欧洲的音乐回忆起它的千年生命,这是它向着永恒无梦的长眠出发之前的最后一梦。”
“现代”,当我认识它的时候,已然是在“日落时分的满天彩霞”里,更何况,我真的认识了吗?我真的理解米兰·昆德拉的“让人发笑”的“幽默精神”了吗?我不知道。因为,在罗罗之后,又有第二个人跟我说奥威尔其实要温和的多,他的话更加直接:“如果奥威尔都让你反应激烈、难以接受的话,我恐怕你不一定真的能读懂《被背叛的遗嘱》,也不一定真的能理解昆德拉。因为,你如果没有真正走入现代艺术和哲学的内部,其中,许多符号所代表的含义,你是没法理解的。”
我想,是的。
胡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