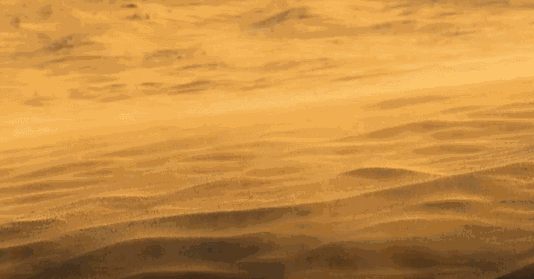不能飞行达之,则应跛行至之;
圣书早已言明:跛行并非罪孽。
——哈里里《马卡梅韵文故事》
1
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
隔着玻璃和细钢筋的防盗网,窗户外面的一组月季正开得争奇斗艳地红。很可惜,是胭脂红。而车莲自认为她最喜欢的是曙红,也许还是朱砂红。
父亲说窗外那组月季是不同的品种,香型的。
难道月季原本是不香的吗?她有些后悔自己以前从没留意过这样的事情。
车莲?这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谁,什么人,叫过这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名字,而实际上跟她并不是同一个人?有吗?一定有的,只是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从来就叫这个名字。父母和哥嫂只叫她,莲。妹妹妹夫和弟弟弟媳叫她,莲姐。如今,她很少听到,几乎听不到被人叫车莲了。
入春以来,她每天安静地呆在自己的病里。安静地坐在,或站在玻璃窗前,看着外面的花园,花园里的月季、塔松,花园边上一溜密实的矮柏,还有从花园边伸展出来,爬满小径两边,有些也攀缘到塔松和矮柏上的藤蔓。那些藤蔓各各相似却又各不相同,有像常春藤、女萝、爬墙虎的,也有像打碗碗花和野豌豆花的,还有更多散碎的花花草草、枝枝蔓蔓,她叫不出名字,也打不了比方。
她每天都看着窗外的花园,长时间安静地看着,一直从窗前很近的矮柏、月季、塔松,看到对面花园尽头的红砖墙。她不知道红砖墙另一边是什么样子,只是每天早晚都能听到那边传来的狗叫声。她看着花园和红砖墙,好像就是为了要叫出那些花花草草、枝枝蔓蔓的名字,认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好像就是为了要猜出红砖墙那边是什么样子?住着什么人?那每天都要叫唤的狗长什么样子?它有名字吗?那名字叫什么呢?黑子?大黄?帅克?巴特?或者还有更好听更漂亮的名字。她猜不出来,就像考试答不上题一样,很沮丧自己的猜不出来。
她就这样看着花、树、红砖墙,有多久了呢?入春以来?可现在是夏天。夏天也已经过去了,是初秋。她忘记了时间、日期,有时也忘记了窗户,也有时忘记了坐在或站在窗前的自己。
这个女人——她有时将坐在窗前,手里拿着绣花绷子或者一本书的自己,叫这个女人,或这个名叫车莲的女人——此刻就在窗前,她手里拿着一本书,书打开着,和手一起放在膝上,但她并不看书,眼睛——是那种很中国的杏核眼——一直看着窗玻璃,长时间一动不动。她在发呆吗?或者她看着窗玻璃睡着了?她想叫醒她,提醒她该做早饭了,该吃药了。她从一起床就坐在这里已经快三个小时了。她从窗玻璃的一片灰黑,一直看到花草树木和红砖墙一一显形,又看到太阳光带着花园和晨光的气息照进窗内,一缕光落在她身上。
她看见她动了一下,动了一下手指,将书合起来,放在身边的书桌上,但眼睛没动。直到她站起身,眼睛都没动。直到她转过身去厨房,眼睛才仿佛醒了一样眨了一下。很缓慢地眨了一下。转身时眼帘盖下来,转过身以后,眼帘才抬起来,就像搭起门帘或者拉开窗帘一样,她的脸面和身体都因此变得明亮活泛了一些。
她穿一身宽松休闲、深色碎花的棉布衣裤,脚上是双绣花畔带的“老北京”牌黑布鞋,浅肉色丝袜。
车莲看着这个名叫车莲的女人在房间里走动,去厨房打开电饭锅,倒水,馏馒头,淘米,洗菜,切菜,水开了,下米,打开煤气灶,炒菜。
很简单的饭菜:一碗小米稀饭,一只馒头,一碟玫瑰大头菜,一碟清炒西葫芦。她一个人坐在木沙发椅上,面对着木茶几上简单的饭菜,安静、寂寞、缓慢、机械地吃。不开电视,也不开音响。她喜欢这种全无声息的静,也喜欢这种无所搅扰的寂寞。
吃完早饭,她突然满面腾起羞愧的表情,像偷别人东西一样,伸手到茶几下面摸取烟盒和打火机。她取出一根白沙点燃,看着手里的烟,又看一眼白沙烟盒,满面的愧色有增无减。因这羞愧,使她抽烟的姿势有种紧张和躲闪,没有办法从容和优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头脑中灌输进来一种观念:抽烟的女人,就像不洁的女人一样,是要被人嫌弃和厌恶的。如今,她身边除了自己再无别人,但她被自己嫌弃和厌恶着,一样有众目睽睽的感觉。
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她又看了一眼茶几上的白沙烟盒。也许并非是喜欢这种烟,而是喜欢烟盒上两只丹顶鹤中间“白沙古井”的四个小红字,才买这种烟的。就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只爱一种纤巧精致的白盒茶花,烟盒上小而灵透的两朵红花瓣和一行娟秀的行楷“如见故人来”,让她爱不释手。如果不是这种烟后来就象突然失踪了一样再也买不到,她不会改抽别的任何烟。即便是现在抽着别的烟,并且因为抽烟而羞惭,她仍然只钟情于遥远记忆里的白盒茶花。
那时,她并不躲着藏着像做贼犯罪一样遮遮掩掩地抽,没有这么深重的羞愧与自责。许多时候,她与三俩女友围坐在咖啡屋或书吧,一起聊天,一起抽同一种白盒茶花。她没有女友们那么舒展优雅,但至少也是从容自在的。没有责备和厌嫌的目光。那精巧素净的烟和烟盒不包含任何不洁与龌龊的信息。它干净。
有一次,她采访一位年轻的女作家。那女作家穿一袭白连衣裙,只抽520,只喝鲜磨现煮的咖啡,浑身里透着一种热烈自信的生机,手指间一支细长的、烟蒂上隽刻着一枚晶莹鲜亮的水红心印的520,极尽优雅之点缀。那烟里虽无褒扬,但也并不包含任何贬抑的成份。
如今,她想那些舒展从容的时刻,就像是另一世界的事情。
这个女人,她难道在编造一种记忆,来安慰或者开脱自己吗?
车莲用不信任的、极其克制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名叫车莲的女人。
然而,她并不是在怀念烟。烟总是有毒的(但哪一种食物、哪一朵花,没有毒呢)。她只是在怀念一种舒展从容的姿态和内心里干净辽阔的天空。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只留下一支如同万恶的烟。
2
烟,只有烟,
到处都是烟,
谁在这些柔嫩的草原上,
点起火苗?
——《血染天堂》主题歌
“该吃药了!”车莲看着这个一下一下磕着烟灰,脸上的愧色慢慢消散的无耻女人,极其厌恶和忍无可忍地说出了声。
她听见了,木然地摁灭烟蒂,站起来,收拾碗筷。涮洗。水龙头开到最大。水花溅到衣袖和前襟上。然后取水杯,倒水,取药,一片一片数,又一片一片数,眼睛木然地看着水杯上的热气,目光在一缕浅雾一样的热气里潮湿和朦胧着。仍在手里数药片。她一句话不说。从睁开眼睛到现在,她始终沉默着。
车莲看着她将药片倒进嘴里,喝了水,咽下去;看着她木讷地坐到木沙发椅的边角上,机械地拿起织了一半的毛线活,这才比较放心地移开眼睛,用一只手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
电视里频繁换台的声音,让屋子一下充满嘈杂和支离破碎的聒噪声。她抬起眼睛不耐地看了一眼车莲。她不喜欢这种声音。但她不说话,只是央求一般看着仍在那里不断换台的车莲。她希望她找不到要看的节目。她希望她因为找不到要看的节目关掉电视。但车莲很有耐心地换频道,换频道,再换频道。一圈换完了,又从头摁一遍,嘴里还念念叨叨“什么破电视,怎么就没有一个好看点的呢?”
其实不是电视不好看,是她自己厌烦着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毛线活却不织的、只盯着自己看的、名叫车莲的女人。她心里厌烦着,就不停地摁遥控器。
这个女人等的不耐烦了,很突兀捷速地从车莲手里夺过遥控器,朝电视机扔了过去。
“砰——嘭——”的声音让车莲和这个女人一起惊愣起来。她们同时转过身,彼此瞪视着对方,都认为如此暴力的事情一定是对方干的,不可能是自己。
这个女人除了一些突兀而莫名其妙的举动很迅捷以外,一切都是迟缓的,行动迟缓,思维迟缓,言语更不用说。她几乎始终都因为迟缓而废黜了语言表达。有一些时候她也偶尔被迫发出声音,但那声音无限恐怖和森冷,不是话语,不是歌唱,也不是哭泣,而是一种本能的尖利的嚎叫,像兽。她自己都害怕那声音,所以,她一直都尽量克制,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响。她只希望安静。她只要安静。
但与人面面相对,尤其是被人咄咄诘难时,无声无息的沉默就等同于默认。她因此背了无数黑锅,那也没有办法。
车莲就从眼前的“暴力事件”开始数落和批评这个瞪视着自己不说话的女人。前三年后四年。车莲的数落就像摁遥控器一样,漫无边际,没完没了。
这个女人一边听着,一边就大瞪着两眼睡着了,不知道车莲都数落了些什么。
这时,另一个车莲从她们中间的缝隙里极轻盈地站起来,对这睡着的和数落的;对这织了一半的毛线活和独自在那里说唱哭笑的电视机;对这木沙发椅和木茶几,一概熟视无睹地越过去。她跟前两个车莲大不相同。她轻盈。她穿一袭长袖齐腕大摆及踝的真丝白连衣裙和一双细高跟的白皮鞋。她缥缈。行动间,水一样披在身后的乌黑长发和雪白的裙裾如同舞蹈一般。
她从她们中间起身,在她们面前走动,车莲竟一点都没有发现和觉察到她的存在;这个名叫车莲的女人似乎看见了,但她只是不动声色地坐着,假装就像车莲一样什么都没有看见。
3
“卡拉的儿子?还是白人的孩子?”
“都是?每一个都不相信另一个,怀疑和害怕占据着你。
你看上去是泰山,但实际上却不是了。”
你看上去是泰山,但实际上却不是了。”
“丛林不再是你的家,动物也不是你的朋友。
你在哪儿都不会感到安全,除非你找到方法让自己完整。”
你在哪儿都不会感到安全,除非你找到方法让自己完整。”
“泰山,生命就像河水,
有时你需要找到它的源头,才能知道目的地。”
有时你需要找到它的源头,才能知道目的地。”
——《泰山传奇·羽蛇神》
那么现在有三个车莲(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该怎么称呼她们,怎样分配她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名字,才不会让人倒混,不会让她们彼此认错对方,也认错自己呢?
最简洁的办法是编号。车莲就叫车莲一。这个名叫车莲的女人就叫车莲二。那个身轻如燕的车莲就叫车莲三。
现在,车莲一二三都在这里了。我仍然好奇她们为什么都喜欢“莲”这个名字。事实上她们生长的北方大地,因为干旱,极其少有天然的莲。为了菜市场的莲菜而进行人工培育的,大约各地都有一些吧。她们名字里的莲,应该不是这一种吧,谁愿意自己取了名字,是为了让人家当菜吃呢。
那么应该还有一种能在高原旱地里自然生长的莲花吧?的确是有的。它叫旱莲。有一种烟就取名叫旱莲。我见过的旱莲是盆栽的观赏花,只有曙红色一种。我没见过别种颜色的旱莲。
旱莲自然是生长在旱地里的,像所有北方大地上的耐寒耐旱植物一样。它属于木兰科,花季在三月,花期有一个多月。如果任凭一株旱莲在荒野里无所搅扰地自然生长,它会长成一棵花树,就像玉兰、合欢们一样。
她们名字里的莲,应该是属于旱莲之莲吧。只开花,不产莲蓬与莲藕。
车莲三轻盈地飘离车莲一和车莲二,出了客厅,进到车莲二每天在那里发呆的书房里。她的身体慢慢缩小,展开双臂。当她小到比彼得·潘的丁卡还要小的时候,它就从窗户上面飞了出去。
她飞到花园里,混迹在蝴蝶和蜜蜂中间,逗留在一朵又一朵的花蕊上面。她一边跟遇到的老朋友们打着招呼,一边采集花的香味。
她每天都将采到的花香传递一些给车莲二,但她没有办法传给车莲一。整整隔着一重世界,车莲一难以接收到花的香味,也不知道隔着一个经常发呆的车莲二,还有一个车莲三的存在。这使得她的体内积满浊污腐败的气息,也使得她越来越脾气暴躁,言辞滔滔,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怨愤与不平,并不断地将自己的怨愤之气发泄到车莲二的身上;车莲二无言地承受着这发泄,借着车莲三的传递,她无尽的忍耐中,渐渐充盈着一种混合植物的苦香味。她沉默的容颜上也慢慢绽放出一种花草般的安详气息,只有极少的时候,会猝不及防地爆发出一点不耐与反抗。
车莲三则要幸福得多,她不被车莲一看见和知道,她在车莲一以外真实而欢悦地存在着。她只被车莲二看见和知道,却又丝毫不被车莲二所左右。她是自在的,欢悦的,歌唱的。她每天最热爱的工作,就是从窗户里飞出去,一边唱歌一边采集花香。
车莲二经常满怀爱怜地打量着车莲三,觉得她既像天使,又像撒旦,有时候更像白痴。幸亏中间有个车莲二,否则,她若在车莲一那里,恐怕一分钟都难以存活下去。
车莲二侧身面对着车莲一,很认真地听她没完没了的数落,但她并没有听见她都在说什么,她只听见车莲三又在胡乱唱歌:“……蔚蓝的天空上漂满康定司基和达利/夏加尔的夜空夏加尔的夜空/一对新人举行盛大的婚礼/凡·高的麦田蒙克的原野/尖锐的颜色无声的叫喊/莫奈炉火纯青的安详/盛开在满池塘的莲花和莲叶上……”
车莲二听着,在心里忍不住笑起来。车莲三经常会乱唱一气,一边唱着一边自己就忘记了唱的什么。
“你没听我说话?!”车莲一瞪大惊讶和愤怒的眼睛,咄咄地逼问车莲二。
“我在听。”车莲二一边满含微笑与沉浸地回车莲一的话,一边伸手又拿起毛线活来织。这时她的内心里一片宁静,任何嘈杂的声音都不能侵入。她安静地微低着头,织了一多半的红毛衣搁在膝上,长长的毛线针横在臂弯间,一针一针从容地织。
车莲一唇干舌燥地看着车莲二,觉得自己纯粹是在对牛弹琴:这个听不懂人话的白痴!
她不再数落,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去地上捡起遥控器,将摔出来的电池重新装好,很不情愿地和车莲二坐在一起,又去摁遥控器来选节目。她很奇怪刚才她给车莲二发脾气和牢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听到电视声?它一直是开着的,此刻正声音很大地播送广告。她怕车莲二又来夺遥控器,选频道时手指抓得紧紧的,想尽快找到一个比白痴车莲二还要白痴的泡沫剧来看。那种剧看起来轻松,可以完全不经过脑子,直接左眼进右眼出。
但是这次车莲二没有去夺遥控器,她已经听不到电视声,就像刚才听不到车莲一的数落一样。只要车莲三能在花园里唱歌和采集花香,她就对眼前的所有事物都熟视无睹了。
她爱车莲三,爱她浑身散发着隽永的花香和婴孩一样的乳香;爱她欢悦轻盈如稚子的纯净气息;爱她永远都只会歌唱和采摘花香这两件事情,除此之外再不会做别的任何事情,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她深知车莲三在车莲一那里难以存活,一旦被发现,一定会被捂死的。所以她一直都格外小心地藏匿着她,不让她的行藏露出可疑的影迹。
但是很难。车莲一似乎已经有所察觉和狐疑,她在前些天陆续将所有的玻璃窗都贴上了玻璃纸,只有书房这一个窗户没有贴。此刻她多想去那里,去早晨坐着的地方,隔着玻璃窗看看车莲三,看她落在哪一朵花瓣上,看她是在小声唱歌还是在跟遇到的某一位老朋友聊天。但是她不敢去,只能陪着看电视的车莲一坐在沙发椅上织毛衣。她怕去那窗前太频繁或呆得太久,引起车莲一的注意,连这惟一的窗户也要被贴得严严实实了。
其实她不是很爱织毛衣,所以总是织不好,不是这里不平整,就是那里不均匀。嫂子、妹妹、弟媳妇她们个个都是令人羡慕的织毛衣能手,手底下出活又快又平整细密,不管给谁织,也都非常地可身。而她织出来的不管给谁穿,都总是不合身,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不是宽了就是窄了,不是长了就是短了。
但她希望自己能织好,总认为下一件会比这一件要好一些,只要她一直就这样织下去,总有一天会织出一件既恰切可体又平整细密的毛线织品,不管是一件毛衣、毛背心,还是一条毛披肩、毛裤,或者是一顶毛线风雪帽、一双毛手套、毛袜子……不管是什么,总会有一件能令自己满意的。她抱着这样的信心,一针一针地织着眼下这件已经让自己很不满意的毛衣。对这一件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只是在完成它。她不希望半途而废。她的柜子里已经塞满了半途而废的织品,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她不知道该拿那些半截织品怎么办,穿不能穿,扔不好扔,看见它们就会心烦。所以就算再不满意,她也要将手里这件毛衣织到最后一针。
必须有耐心。有足够的耐心。她不能心烦。她知道她不能心烦,丝毫的心烦气躁都逃不过车莲一的眼睛。她比任何秘密警察都灵敏细致,都恪守职责。她每天无数遍地翻腾检查车莲二的衣柜、书柜、手机和容色眼神,巴不得在她的心脏和头脑中也装置许多窃听器和摄像头。车莲二对此只能听之任之,她没有办法阻止她这么做。但她如此狂热,会拿任何一点可疑的蛛丝马迹来咄咄逼人地审讯车莲二。她总怀疑车莲二背着她在跟什么人通奸。她给她乱定罪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抽打她。
车莲二在那样的时候格外沉默。她把自己变成一块花岗岩一样的石头。在石头里面深深地含着晶莹如钻的车莲三。仿佛轻轻摆动摇篮一样,轻柔地摇动内心一片黑暗之中的一粒晶莹,哄车莲三睡着。她不愿意车莲三感受到鞭子的残酷、刀子的锋利、坚冰的彻寒、烈火的炙烤……
如果车莲三那时恰巧像现在一样轻盈地跑出去,在花园里流连忘返,她就会格外地担惊受怕。她害怕她突然在这时回来,从外面看见这一切,因惊吓而转身跑掉,再也不肯回来。
如果那样,花园里将多了一个蝴蝶样的游魂。她漂泊无依,洁白的衣裳会染上泥污,会被酸枣刺和荆棘挂破;她小小婴孩样明亮晶莹的双眸,会蒙上雾水一样的哀伤;她清澈欢悦的嗓子会变哑,不再唱歌……但她不会死。她会在某一个寒冷的冬夜去叩问每一扇亮灯的窗户,直至被一扇开着的窗户里坐在窗前台灯下面读书的、满心温暖如梦的女子收留,以此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新家。她会为那女子唱歌,采集花香,一如她曾经找到车莲二并为她所作的一切一样。
如果那样,车莲三无论是被捂死在车莲二的石头心房里面,还是被驱离身畔,车莲一都将再无能挽救车莲二的性命,就如同她再也无能挽救自己的黑暗与孤独一样。
4
是的!只要他没有浸染在人的变色龙般的颜色里,
孩子就是一个神性的生灵。
孩子就是一个神性的生灵。
他完全是他所是,因此才这样美。
法则和命运的强制碰不到他;自由惟独在孩子身上。
在他身上是和平;他还没有自相崩离。
——荷尔德林《许佩里翁或希腊隐士》
“该做中午饭了”“该午休了”“该起床了”“该做晚饭了”“该吃药了”“该上床休息了”……车莲一依旧毫无察觉地命令着车莲二。
车莲二无言地做着车莲一要她做的每一件事,却总是做不好。她满眼忧伤地看了一眼专断的车莲一,看着她和车莲三永不相识、相见、相知的样子,满心忧伤。
她无声无息地做着所做的和必须要做的机械重复的事情,就如同水和光从手指间流淌过去一样。
她从早到晚听任车莲一的数落、谴责、误解、诬陷、欺凌、咒骂等等无边无际地铺展在自己四周,又到处蔓延,她只能克制着、忍耐着,不让心里住进去嗔恨与愤怒,以及过度的悲痛。她知道那些东西都没有用,只能让她和车莲一之间更加分崩离析,更加对抗,更加冲突迭起,更加你死我活,无所调解。她用一道迷雾一般的忧伤沙丽隔开这些激烈而无用的情绪,在心里默默地唤车莲三回来。
傍晚的花园,光线暗淡下来。车莲三带着花香、鸟鸣和自己的歌声,要从窗户上面回到车莲二那里去。
车莲二想去书房。她极其顺从地做完车莲一要她做的每一样事情,只是不想这么早就上床睡觉,因为车莲三还没有回来,因为坐在窗前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大约是因为她的顺从吧,车莲一的容色竟然变得很温和,她猜出了她的心思,看着她换好白丝绣花睡袍却不上床的落落寡欢的样子,便用一缕无奈而柔和的目光允许了她。这目光竟让车莲二感觉到一种暖融融的气息,她满脸透出感激和欢悦的神情轻快地跑向书房去,像她还是十岁小女孩时的样子。在她身后,她听到车莲一叮嘱的声音“不要超过11点。”
她知道“不要超过11点”的意思是,零点必须进入深度睡眠,否则一切秩序又将紊乱。
她如同久违一般再次坐到书桌前,看着窗外深邃邈远的夜空,夜空上闪烁的星星,满心满眼都氤氲着一股清悦馨香的气息。那是车莲三的气息。她正在回来。
其实,她并不全都喜欢和满意车莲三的所有歌唱与花香,那里面也有许多杂芜和琐碎的东西,是她不喜欢的。她只是深爱她如同孩子一般永远都只是歌唱和采集花香的专注与浑然一体的气息。
她曾经长久地观察四周的大人与孩子,满怀哀伤地看到大人们怎样向自己的孩子强行灌输世俗的观念,使得孩子浸染人的变色龙颜色的年龄越来越小。三四岁的孩子就被教育着学习察言观色,分别好恶,趋势向利,讨人欢喜,飞扬跋扈……以此远离孩子的天性,远离自然与自由,远离神性。
人类正在失去自己的童年,却浑然不知。
车莲三像真正的孩子一样,欣悦、天真而不知疲倦地飞回来,将满身的花香传递给车莲二,又用她童真的乐音讲故事给她听。像她每天回来所做的一样。
车莲二总在这时内心肃静,眼里渐渐潮润,淌下晶莹而欢悦的泪滴,如同晚露。她每天都在担心车莲三不再回来。就像母亲担心女儿飞走不再回来一样。又像女儿担心母亲出门弃她不回一样。这归来与迎候,这欢悦与泪水,如同别后重逢一样,日渐成为车莲二每晚睡前的仪式。她越来越担心这仪式会在某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被一把锋利的剪刀剪断。也同时剪断了她和车莲三之间的联系。
她一定会好好掩护车莲三,并誓死捍卫这仪式和联系的。
她带着车莲三回到卧室,身体里散发着新鲜植物安详清越的气息。
5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海子
她甚至满心满眼都是无奈与悲伤地看着这个病入膏肓的无可救药的女人,看着她回来,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几乎是无忧无虑地回来,并且很快就睡着了。
但车莲一无法入睡。
到这时,屋子里就只有车莲一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否可以将车莲们的编号去掉,只叫她车莲?
是的车莲无法入睡。因为这个刚刚回到自己身体里,现在正在酣睡的,名叫车莲的女人,因为她的存在,车莲已经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这个女人象一个把柄一样让车莲日夜不安与焦虑。
无数次,她想杀死这个女人,但她发现她根本做不到。每一次当她动手,她所能戕害和损伤的都只是她自己,这个女人却安然无恙地深藏在她的身体以内,她碰不到她。即便她瞅准了她在外面的时候,仍是一样。
她渐渐放弃刺杀这个女人的念头,她想教育她。但是显然教育也是失败的。从一开始她满腔热情地批评教育她时,她就是默然恭顺的样子,一句话不说地听她说东道西、说长道短,到现在仍是这种样子,前后没有丝毫改变。她终于知道在那默然恭顺的外表下面,包裹着一块石头。那些从石壁上碰回来的所有批评教育的话语,所有的苦口婆心,全都争先恐后地纷纷如霜雪一般从自己四周降落下来,使得她的所有热情日渐变冷。
她躺在更漏深深的黑暗中,眼里淌下两行冰冷的清泪,所有白天里的凌厉之气,化作枕巾上一片凄冷迷茫的湿气。她不知道该拿这个油盐不进的、铁石心肠的女人怎么办。她像恨铁不成钢一样地恨她。她在批评她的时候,自以为她对这个女人是了如指掌的。然而现在,她必须承认自己对她一无所知。
这个女人就像厄运一样降落并永驻在车莲的命中,让她历尽尘世上万万千千冰与火的凌迟,处处行与愿违,日渐丧失了一个社会人的行为能力,成为一个病人。如今跟她一起囚禁在一间病室之中,仍不得安宁。而她,对这个木讷寡言却如此掌控了自己一生命运的女人,竟然是一无所知?!
但她知道,这个在白天几乎一言不发的女人,在寂静无声的深夜和深沉的睡眠中会说梦话。以前,她每当失眠之夜,都能听到她既清晰又含混的梦话,她只嫌那梦话聒噪,搅扰了她想问题。此刻她却突然希望听到她说梦话。也许,那梦话中会透露些什么信息,让她有办法破译和了解这个女人。
是的,一定得有一种办法了解她。
车莲突然好像心中冷却了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一样,并且慢慢炙热起来,以致潮湿的枕巾也渐渐温热并且干爽了许多。
是的明天,从明天起,她要用全部的耐心与爱心,来探寻一条通往这个女人石头心房的路径,了解她,爱她,并且赢取她的信任与爱。无论她带给自己怎样的厄运,都要像接受晨露与花香一样接受它,不包含恨与怨地欣然接受。
她不知道这样的愿望是否又是她过于热情迫切的一厢情愿,但她确定,只有当她和她彼此牵手,彼此默契,相视一笑时,她们就可以从这间病室中走出去。除此,无论是杀死她还是用一只手拎着她,都不可能从这里出去。
明天,明天就像一个希望一样,遥远飘缈地悬挂在夜的另一边。车莲望着它,眼睛渐渐朦胧起来。这时她似乎闻到一缕浅淡而馨香的新鲜植物的气息。
胡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