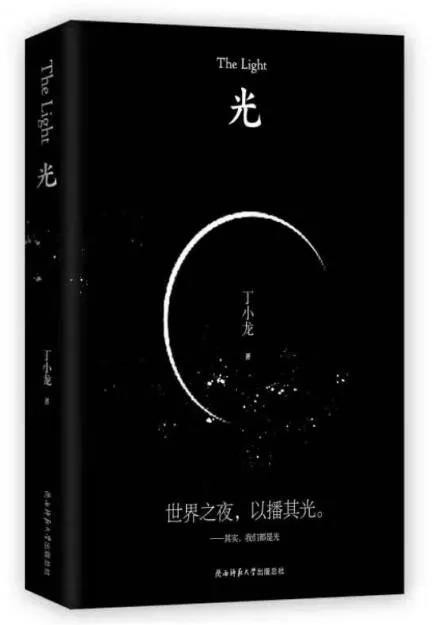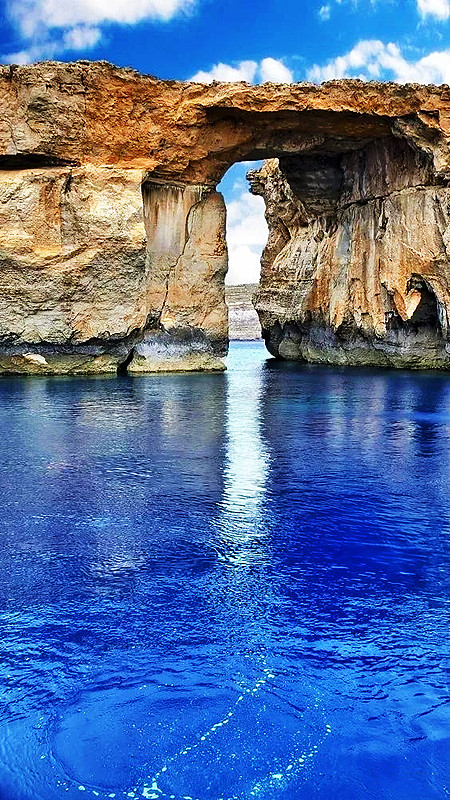在陕西,年轻一代的80后、90后作家,大致有这样一些醒目的标签:学历高、起点高、富有才华、阅读广泛而深入。他们的写作,已不满足于传统写实主义对生活资源的过分依赖,对人的社会性阐释;而是更多地观照精神现实,寻找人物命运的内在根由,探索叙事艺术的诸多可能性。他们表现出对上世纪80年代业已落潮的先锋小说的积极回应,或者说,是在新的时代境遇下的重新启航。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当代小说克服重重阻碍,重回现代性的起点。
这些青年作家当中,丁小龙写小说,写随笔,写诗,还搞翻译。他的个人才华,在不同文体之间自由穿梭,均有突出的表现。当然,他的写作重心还是放在小说上,这种虚构性的叙事文本,也更多地承载了他对生命和世界的整体性思考。他从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神学的领域广泛汲取,带着新的理念和方法,打探并化解自己的梦想、欲望以及生存经验,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也许会有人觉得,包括丁小龙在内的很多作家、诗人,都难以摆脱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响,甚至处于他们的阴影之下。毋庸讳言,这种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已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学的真实状况。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便清楚地知道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催生作用以及巨大影响。当然,“影响的焦虑”及其克服,对构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是有益的,尽管这一过程会相当漫长。
《世界之夜》《幻想与幻想曲》《万象》这三部中篇小说,是丁小龙探寻现代人存在困境与精神难题的艺术家三部曲,主人公分别为诗人、钢琴演奏家和画家。当作家将笔触对准艺术创作的小众群体,呈现他们内心的波澜、情感纠结及命运走向之时,无意之中也展现了诗歌、电影、绘画、古典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的魅力。不同的艺术形式丰富了小说的材料构成,铺陈出斑斓的色调和情感氛围,而且主人公对艺术的深刻见解,也赋予作品相应的思想深度。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作家对创作本身和创作者生存状态的观照,也是对自身的审视与剖析。现代小说多以“我”的视角进行叙述。这种角度呈现的视域并不宽广,不适合用以描绘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但第一人称特有的主观性,能够深入人物内心,展露意识深处的暗涌,呈现多层次的心理结构。而且,“我”的称谓也是对读者的亲切呼唤,这呼唤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进入文本现实,主动分担人物的命运和悲欢。
《世界之夜》(原载《延河》2015年第8期)从始至终是第一人称叙述。这也是三部小说中“意识流”特征最为显著的一部,但已不同于早期“意识流”小说的晦暗和费解,明晰度、可解性大大增强。小说随着主人公思想意绪的流转,自由地转换叙事场景,并在回忆和梦境中植入更多的情节单元。《幻想与幻想曲》,用的也是第一人称视角,但这个“我”分属男女主人公,是以他们的口吻交叉叙述的。直到第九章的“幻想曲”,才改换成第三人称。这样的视角以及灵活转换,不仅拓展了叙述的场域,也使得两人的叙述有了相互印证的真实感和层次感,以及结构上严丝合缝的效果。相对于前两部,《万象》应用了罕见的第二人称视角。文本中,称呼“你”的只能是隐身的“我”,即叙述者本人(作者)。第二人称叙述,会形成一个亲切的对话性结构,或者说话语场,哪怕这样的结构(话语场)仅仅表现为一种语气、语调或氛围。这样,在呈现的视域、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等方面,都大不相同。选择这样的视角进行写作,对于作家来说也会是奇妙的体验。
三部小说在结构上都非常讲究,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说到结构,它既有外在的形式感,又具备内在规定性,凸显文本的空间感以及时间的纵深感,从而形成一个深度空间。《世界之夜》分为“冬部”“春部”“夏部”和“秋部”四个章节,而2047、2015、2001、1988,这四个时间节点,生命年轮的四个剖面,用来展示主人公的一生。四季对应不同的生命时段,其循环往复,也赋予作品生命轮回的寓意。小说以2047年的“现在”为起点,以整体倒叙的模式展开,生命的终结成为小说叙事的起点,而生命的开启则成为结局。这种物理时空的错位与颠倒,给人造成时光倒流的幻觉。这样的结构模型犹如一个平行置放的漏斗,末端最小,但也是开启生命历程的顶点。
《幻想与幻想曲》(原载《清明》2017年第5期)分为九节,前八节是“白色”“黑色”的交替,第九节以“幻想曲”收束。何以如此标明题目?小说中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说明:“这一次,他们两个人成为了一个人,一黑一白,像是一个人灵魂的正反两面,与钢琴黑白键交换着对世界的理解。”“白色”是女主人公潘以梦的视角,“黑色”是男主人公荀生的视角,当他们再次相遇长安城,两个人的视角往往叙述同一件事情。第九节是结局,也是他们合体演奏的高潮部分,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了客观呈现。小说似有两条线索,两个声部,但仍是以交叉耦合的方式结为一体的。如果有兴趣,只读取其中白色或黑色部分,对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减损。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可以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小说,或可比喻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双面人格”。
而《万象》(原载《广州文艺》2019年第6期)这部小说,则以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结构文本。“水象”“土象”“金象”“火象”“木象”,是主人公为自己即将举办的画展创作的五幅作品,画展名为“万象”,也被用作小说的题目。事实上,这“五象”分别暗合了女画家在不同阶段的精神状态和自我追寻的历程,与叙述内容紧密呼应。“五象”构成“万象”,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便得到整体展示。
这三部小说,除了叙述视角和结构上的关联及差异性之外,在内容呈现和主题的表达上也是互补的,同构的。《世界之夜》中,一个失败的诗人,唯一成功的诗作竟是献给母亲的“安魂曲”,或许只有经过死亡之光烛照,有关生命的书写才能抵达诗歌的本质。主人公曾说,回忆是“时间的葬礼”,而小说正是在宿命般的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展开叙述的。母亲已死(表姐成为唯一的牵挂),“我”凝视死亡,抵临存在的深渊,依次回顾自己底层生活的艰窘、婚姻的失败、对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兄弟之谊、母子之情等。透过小说诗性叙事的审美构成(对于时代、诗歌艺术、生命、时间、死亡等事物的形而上思考),我们发现其中最基本的叙述构架和脉络:一种建立在(或侧重)家庭关系模式上的表达。兄弟之间存在母爱分配不均导致的嫉妒,但更多是亲情的关爱;“我”对表姐极为依恋,而这种依恋也没有突破伦理的禁忌;而母子之情,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在小说最后一章有着非常精妙而动人的抒写。亲情叙事的魅力,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冲突、隔阂、和解,一种感情的扭结及其缓释过程。而小说中的这一对母子的关系却十分融洽,有着深切的理解和亲密的精神联接。当然,舅舅、父亲、哥哥的先后离世,也是促成这种关系的客观因素。
《幻想与幻想曲》讲述了一对学生时代的恋人,时隔十余年,因舒伯特的《幻想曲》重新聚首,但又不可抗拒地再次分离的故事。小说以情爱关系为线索和主体,在情节的推进、感情的发展过程中,又穿插、交织着各自的家庭生活矛盾。情爱关系中特有的微妙和细腻、韵律和色彩,亲情关系中的爱恨交织与无法释怀,在其中都有集中而鲜明的呈现。在潘以梦和荀生看似弥合的感情发展过程中,却横亘着潘以梦的婚姻和对家庭的依赖,荀生的独身理念(一场灾难的后遗症)。童年时期的荀生因被钢琴教师猥亵,致使父子关系恶化、父母的冲突以至家庭破裂,罹患抑郁症的母亲最终选择自杀,而外婆也因此猝然亡故。这是荀生的心病,也导致他对婚姻生活的恐惧或者说厌恶。事实上,潘以梦面对婚姻裂痕的消极态度,也有着来自原生家庭的心理根源:父母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小说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通过与亲人和解的方式,打开了心锁。他们合体演奏的《幻想曲》的高潮,也成为这段感情的升华,新生活的开始。
同样的,《万象》也是以情感生活导入并进一步展开的。女画家苏葵感情丰富,富有创造才华,但她的内心封闭而孤独,对他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父亲是她绘画上的启蒙老师,幼小心灵的庇护者,然而父亲的过早离世(在和母亲的纷争中跳河自尽),成为她的心结,也成为母女关系间的一道屏障。父爱的缺失,让她从自己的大学导师身上寻求补偿;母爱的缺失,让她对母亲心生芥蒂和怨恨;一场婚姻的失败,更是让她无法从心底真正地接受一位热情似火的年轻恋人。但和女儿的相处,以及对母女关系的重新思考中,她逐渐理解了母亲,修复了母女之间的裂痕。同时,她也从外公外婆历经风雨、始终不渝的婚姻生活中得到启悟。于是,她重拾信心,从残缺的家庭关系和破裂的婚姻关系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新人”。
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父母关系不合导致的家庭动荡,是子女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在人际关系中缺乏信任感的根本原因。而父亲或母亲的过早离世,也会成为子女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痕。在普通的家庭结构中,父女或母子、父子或母女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不一定令人满意,但基于某种深切的心理动因而呈现的错综复杂却是事实。原生家庭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子女的人格,并进一步影响他们此后的生活和情感抉择。而对艺术家来说,还会暗中支配他们的创作主题与风格。关于这一点,文学和艺术史中不乏例证:
波德莱尔幼年丧父,母亲带着年仅六岁的他改嫁,其乐融融的童年生活发生剧变。父爱缺失,母爱也被人分享,于是他与母亲的关系日渐疏远,与继父之间充满对抗和厌憎。实际上,波德莱尔对母亲抱有强烈的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这也深刻影响到他对女人的态度以及自己的情感生活。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可以从小说《判决》中一窥端倪。他一生都活在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对父亲的反抗或者说“精神弑父”,只能以失败告终。这失败也导致他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对婚姻的恐惧。“形而上画派”创始人基里科,十六岁时父亲病故,这让他无法释怀,以至数十年间反复梦见父亲。他的很多作品中,地平线上都毫无缘由地出现一列冒着浓烟的火车,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深情和怀念(他父亲是铁路工程师)。
艺术家早年的家庭关系,是艺术家性格、命运乃至艺术创作的深刻根源。但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童年的不幸促使艺术家以其超凡的创作进行疗治和补偿。小说在展示父子、母女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母子、父女之间的深挚情感上,都有着非常生动的表达和令人信服的现实依据。这也是主人公历经婚姻或情感生活的波折,为求解脱而追根溯源,最终从童年的精神创伤(家庭关系)中觅得解药。小说呈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将这一过程演绎得曲折而生动,不能不说其中有着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应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有着来自艺术创作和现实生存的双重困境。“这是一个敌视艺术的庸众时代”,“婚姻就是艺术的天敌”,“其实,你心里特别清楚,艺术改变了你的生活,常常将你推向深渊,然而,在你最困顿的时候,艺术又拯救了你。”
这些来自艺术家心底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他们过的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双重生活”。这“双重生活”有谐和的一面,但更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异常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导致艺术家的命运悲剧。小说聚焦这类人群的生存状态,也就展示了更为多姿多彩、深刻盈透的生命主题。对艺术家而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那种“古老的敌意”,也不能阻止精神探险的脚步——艺术哺育的心灵有特别的韧性,能在任何境况下实施突围。
注:丁小龙,1988年生,现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理事,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入选陕西省“百优计划”。出版与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万余字,作品见国内多家文学杂志,被收录于各种文学选刊与选集。另有译作三十万字,翻译并发表了包括托妮·莫里森、科尔姆·托宾、萨曼·拉什迪与珍妮特·温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出版小说集《世界之夜》。曾获第三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参加第八次全国青创会。
作者简介:
王可田,1972年生,陕西铜川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铜川市作协副主席,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陕西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出版诗集《麦芒上的舞者》《存在者》,访谈录《诗访谈》。曾获鲁藜诗歌奖、延安文学奖、陕西作协年度文学奖、陕西青年文学奖等。
王可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