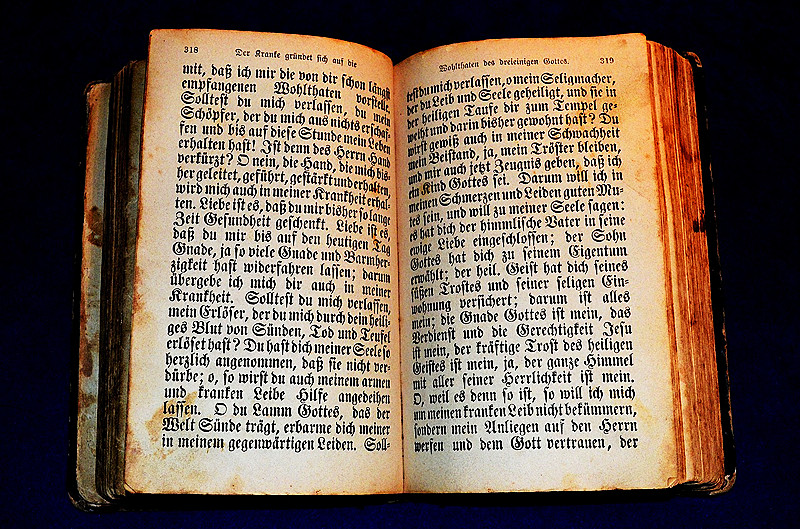反复读这篇文章,并且不断有泪朦胧自己的眼睛。不为别的,只因为每一次在夜深人静里自问自省时,都非常明白和清楚,此生此世,自己的内心以及精神都已绝无可能抵达纯粹、靠近神性,因此,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信者。
在我们的前面,在信仰的路上,有特蕾莎修女,有西蒙娜·薇伊。在她们的身上,在她们的爱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信的虔敬、爱的纯粹、以及人所能够抵达的神性的极端。
是的,不可能拿“神”来要求人,不可能拿特蕾莎、薇伊和圣徒来做我们的参照系。即便我们天生善类;即便我们不乏同情、怜悯与爱心;即便我们一生都在追寻一种精神上的皈依;即便我们始终都怀着罪感而努力寻求一条能够让自己内心得到安宁的途径……然而,当“她”终于来到眼前时,当我们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所求时……我们知道自己走不过去。
因为,“她”不在高处,而在低处;因为,“她”不在于获得,而在于放弃。换言之,神,不在天堂,而在地狱。如果那种降低与放弃,可以拿尺寸计算,或许对一个内心有所求的人来说,并非难事,然而,没有任何单位可以计算,那是一条决绝的一降到底的不归路;那是一种除了"爱"一无所有的对一切欲望和俗念的彻底弃绝与忘却……
薇伊的阐述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的最底层,比乞讨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实际上才有可能说真话。其他人都在说谎。”谁有可能去实践“狂人”那样深刻的真实?
特蕾莎的表达是另一种,“我想这正是我们打算做的……变得卑微、无助,”“当我们生命完结时,神审判我们将不以这些作为衡量:我们曾考获多少文凭/我们曾赚取多少金钱/我们曾做过哪些伟大的事//神审判我们,是以/‘我饥饿时,你给我吃/我赤身时,你给我穿/我无家可归时,你接待我。'”因此,她说,神就在最丑陋的麻疯病人身上,神就在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身上,神就在所有贫困中最穷苦者身上,神就在所有受苦受难中最无助者身上……“如果我们不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起生活,就无法明白和有效地帮助他们。”“当我们一无所有时,我们会将一切付出——因着贫困的自由。”“与受苦共存共生的,乃是喜乐。”……
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不仅这样说了,而且,毕生都这样做了,直到生命的终结,直到接受审判的时刻……因此,在她们的生命里,所包含的、所闪烁的,正是我们所欲所求却不能够有的“神性”。
有什么是比看到自己的所求却知道永不可得而更加绝望和羞愧的事情呢?
一直以来,我们自豪并自慰于自己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那是因为,我们惧怕着自己内心的空虚、生命的荒芜、价值与意义的缺失、无所归属的孤独以及无所依赖的无助,等等。其实都还只是为了给生命增加而不是减掉或者丢弃。所谓"追求",无非是像诗人要折桂、竞技者要摘金、鼓励孩子考试要考第一、生为女人梦想最美、生为男人梦想最富……而所谓对“神性”的追求,也如此一般,不过是要一个最高的精神奖赏而已。然而,一切都可以求而得之,唯独“神性”,实在是南辕北辙了。
是的,我们无法彻底摒绝人欲,因此我们无法彻底抵达神性。
正如李家同写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心里筑了一道高墙,我们要在高墙内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而将地狱推到高墙之外。这样,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装人间没有悲惨,尽管有人饿死,我们仍可以大吃大喝。”即便我们并非熟视无睹而是承认人间有悲惨,即便我们并不那么心安理得地大吃大喝(何况我们实际上是的)而是很节约,即便如此,我们真的就能彻底拆掉心中的这道高墙,永远而无所保留地走到“悲惨”的中间去吗?
李家同本身就是一位基督徒,在他的内心以及修为中,原本就有我们大家所不具备的许多克己的品质,而且他是去过印度,并在特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里做过义工的。他却也毫不隐瞒和避讳自己的不彻底性。
他是1994年9月经过一再电话约定后去印度面见特蕾莎的,为的是将自己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授予她——其实,对特蕾莎而言,所有的荣誉以及奖赏都是多此一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她给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答词是这样的:“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
特蕾莎一生获得的荣誉与奖金何其多,全世界至少有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和国际大机构向她颁发过崇高的荣誉和奖金,然而她转手就将所有的东西包括奖牌、勋章之类全都换成了钱,撒到最穷、最卑贱、最无助者那里,只为了让他们被弃的生命有一个栖身之所;只为了让饥寒者可以得温饱;只为了让孤独而濒死的生命获得一点最后的安慰与关爱,安宁地死去……
她也懂尘世间的经营,比如,她拿罗马教皇赠给她的白色林肯轿车作为抽彩奖品,换来的是一座麻疯病人医院,那里便成了所有被弃的麻疯病人惟一的家,还有艾滋病人的家、流浪孤儿的家、濒临死亡而面临曝尸街头者的家,等等,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上千个类似的机构,或由她亲手创建,或由她的追随者创建,这些归于她的“仁爱传教会”之下的所有机构,拥有四亿多资产,而特蕾莎和教会的七千多名正式成员却全都是身无分文的赤贫者,而且她绝对反对募捐筹款,尤其不许以“特蕾莎修女”和“仁爱传教会”的名义,这里不仅包含了她对自己纯洁性的维护,更重要和深一层的是也包含了“神性”对“人性”的尊重。
至于荣誉,随后就被她忘记了,那是跟她无关的东西,她不会因为有而多做什么,也不会因为没有而少做什么。
因此,当李家同站在她面前时,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答应过接受荣誉博士这件事情便是自然的而非造作的了。
李家同和特蕾莎的见面只有五分钟。之后,他在加尔各答呆了3天,有两天的时间在仁爱传教会的"垂死之家"里做义工,世界各地利用假期来这里做义工的人很多,除了最多的是大学生以外,各个阶层的都有,有的三两天,有的每年都来一两个月,但他们总有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的时候,而特蕾莎和追随她的七千多名仁爱传教会的修女和修士是永远没有那样的为自己活着的时候的。
李家同在这里还留心到了另一个现象:来做义工的最多的是欧洲人,他没有见到一个美国人,也只见到一位印度人,还是刚刚从欧洲回来的。我不管他想说什么和现象本身说明什么。我只有一点自己的感觉: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不仅印度,许多地方都一样),既对身边的不幸和悲惨熟视无睹,同样也对身边的感召无动于衷,那种麻木与漠然深入骨髓。至于美国,我大致认为这个年轻的国家更可贵的在于充满赫斯嘉一样顽强的生命活力与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西部牛仔一样的开拓与创造精神,而一直都在张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却包含了许多做秀的成分,给世界做秀看,因此,失去了“教义”本身的朴素性和纯洁性。
李家同做义工的“垂死之家”是特蕾莎自己创立的,起因是,一次她在火车窗口上看到一个流浪汉靠在一棵树下,濒临死亡,而火车正在行驶中,等她坐下一班车返回来时,那个人已经死了;另一次是她在街上见到一个老妇人,满身都被老鼠和虫子咬坏了,她带着她去了好几家医院,都被拒绝接收。她一直看着她死去。因此,她创立了“垂死之家”,捡回并收留这样的人,让他们能够在被照顾、被安慰中不那么孤独和恐惧和凄凉地死去,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感到人类的关怀与爱,让他们不在被弃的遗憾与怨恨中死去……
虽然,在这里仅只做了两天的义工,还不是修士,李家同已经在生命里烙下了终生的记忆,他说:
“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
“我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用杯子在阴沟里盛水喝。
“我忘不了两个小孩每晚都睡在我住的旅馆门口,只有他俩,大的顶多四岁。
“我忘不了垂死之家里骨瘦如柴的病人。
“我忘不了那位年轻的病人,一有机会就希望我能握住他的手。
“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野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湿他们。他们的眼睛望着天。”
是的,他们的眼睛望着天。
最让这位做了四十年基督徒、已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几乎心灵无法承受的情景,正是那眼睛……在他两天里抬过的遗体中,有一个年轻的死者,因为被扑下来啄食的乌鸦拉开了盖布而露出了死后的表情:“眼睛没有闭上,对着天上望着……”——他记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已经四次踏进“垂死之家”的流浪者,每次病到奄奄一息时进来,病好些时就出去继续流浪。第四次,他已完全丧失信心和勇气,拒绝吃饭,拒绝喝水,拒绝吃药,只求人家握住他的手。——他说,“虽然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那孩子无语问苍天的凄苦表情,以及大乌鸦来啄食的情景,已经使我受不了。”
两天里,他那么逼真贴近地见到了“Poorest of the poor”,见到了从未留心过身边只在报纸和电视新闻中看到过的人间悲惨……因此,他“心头沉重无比”;因此他终于理解了特雷莎的一句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与,自由地爱,直到它受到创伤。”;因此,他真正理解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时更深的含义;因此,他反省自己,“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在监狱里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在孤儿院里为那些被修女们惯坏了的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服务,那些事情都不会让人感到心痛,反而会有欢乐,而他绝不敢去安慰死刑犯,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人类真正的贫穷和不幸;因此,他自问:“可是,我敢自称是基督徒吗?当基督说‘我渴'的时候,我大概在研究室里做研究,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
其实,坐在研究室里做研究;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或者,心安理得地过自己小康的日子甚至富人的日子,原本都无可厚非……我们许多的“乌托邦”理想与追求,不就是想要建立让人人都过富人日子的社会吗?我们也经常大呼小叫“消灭贫困”“消灭歧视”“消灭三大差别”等等,然而,什么才是有效的?
“他们的眼睛望着天”……而我们既可以“看不见”,也忍心别他们而去……李家同在临行之前,再次看见一位垂死的刚刚被家人抛弃在街头的老人被一位修士和义工扶起……他说自己真的不想走,很想永远留下来,为“他们”服务,但他还是走回计程车,去了机场。
“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我们无法抵达。在混乱的时代里,在复杂的人性里,能够像李家同一样,保留着人性中极其柔软、善良和敏感的部分,不断被“神性”感召,不断朝“彻底”与“纯粹”靠近,这是我们常人惟一能够要求自己的。
我们无法效仿特蕾莎和薇伊,还有许多带有圣徒精神的人,抛开我们不能“丢弃所有”这一点,还因为我们内心里存着太多的怀疑与恐惧,我们甚至怀疑这样做真的是有效的吗?这种苦行和殉道难道不是一种病态吗?这种几乎自残的方式真的是爱的极至吗?尽管“他们的眼睛望着天”,但能够拯救人类和消灭贫困与悲惨的真的只有这样一条途径吗?……苏珊·桑塔格说,“我想到西蒙娜·薇伊一生那种狂热的苦行主义,她对快乐和幸福的鄙视,她那高贵而又怪诞的政治姿态,她那精心实行的克己,她对痛苦的不倦追求……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然而,只要我们热爱严肃,以及热爱生命,我们就会受其感动,受其润泽。当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重,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神秘……”神说:“小信的人哪,你们为什么要害怕?”……我们害怕,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勘不破这一层神秘。(2001)
胡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