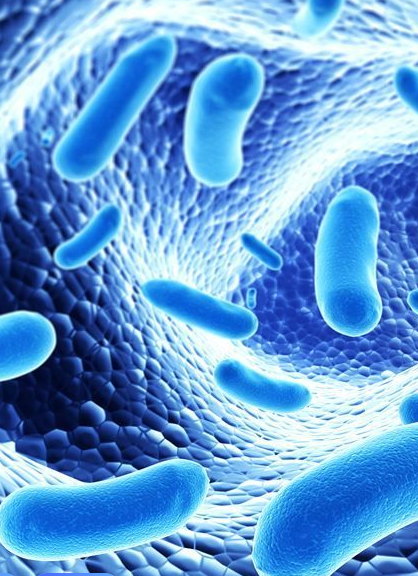交响乐《嘎达梅林》是上海人辛沪光1956年在音乐学院毕业时的作品。这部毕业作品使她一举成名。《嘎达梅林》不仅奠定了辛沪光中国作曲家的地位,《嘎达梅林》还成为中国人创作的最优秀的交响乐之一。与陈刚、何占豪的《梁祝》一起,被国际音乐界誉为中国音乐的“双珍”。
听《嘎达梅林》,时而如暴风骤雨,天昏地暗;时而又是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时而如狂风巨浪,汹涌澎湃;时而又是风平浪静,万里银波;时而如广阔的大草原上万马奔腾;时而又是蓝天白云下牛羊成群……
《嘎达梅林》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有着“气吞万里如虎”的力量。在音乐厅里欣赏《嘎达梅林》,会发现听众无不为之心血澎湃,热泪盈眶。
我听了几十年《嘎达梅林》。晚年仍然喜欢听,仍然会在《嘎达梅林》的旋律中老泪纵横。
再说赵本山的小品,多年来一直是春晚的重头戏。赵本山那特有的东北腔调中土里土气的表演,会让亿万观众兴趣盎然,在情不自禁中,笑得前仰后合……
但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生前却这样说:赵本山的小品是出洋相。那不叫艺术。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赵本山的“出洋相”却能给亿万观众带来精神愉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愉悦?出洋相,上了春晚这样的艺术舞台,应该算是什么艺术?或者说编导与观众的艺术欣赏属于什么样的审美?
上述两个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的不同显例,很值得玩味:《嘎达梅林》的审美与赵本山小品的审美是有高低水平差异的,体现了雅俗不同的审美层次,体现了欣赏者不同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情趣,体现了不同的审美思想。虽然雅俗不同的审美没有好坏优劣的分别,但一个民族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普遍地停留在俗文化的层次上,却是个值得反省的现象。
这大概不是用一句“萝卜韭菜,各有所爱”就能解释通的。“出洋相”能有亿万观众热忱的收视率,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与相去不远的“文化沙漠”直接相关。
就像那位读者认为的,老干体诗也是一种“审美存在”。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审美存在”确实存在过。但是,它还能存在下去吗?讴歌“假大空”也曾经是一种“审美存在”,这种“审美存在”还存在吗?
按照那位读者的审美逻辑说下去:乾隆皇帝一生写了数万首诗,也属于“审美存在”。但是乾隆的诗,没有人喜欢看;更没有人愿意保留。乾隆的诗早已灰飞烟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所以乾隆诗的“审美存在”,其实是毫无审美价值的文字垃圾。
与乾隆诗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老干体诗,都是作者花钱出书中的“自得其乐”。这种乐在文字垃圾上的审美,属于什么样的审美?
就像南京的博导钟某的旧体诗,除了让读者嘲笑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外,究竟有多少审美价值可言?
其实,议论文学艺术雅俗不同的审美问题,属于讨论常识,讨论常识本来属于废话,这里不得不说了半天的“废话”,主要是那位读者对这个常识的模糊,是很有代表性的。既然这样,讨论常识就不是废话了。
(三)张爱玲小说的审美价值
首先应该指出,那位读者说的张爱玲小说一度风靡大陆读书界,这个现象不足以作为评价小说的主要根据。例如张恨水的小说民国年间不是也风靡读书界?能说张恨水的小说有多少审美价值?张爱玲小说一度风靡大陆读书界,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个问题不说大家都知道。
文学是人学,小说是表现人物的。而小说创作的最大难度也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所以评价一部小说,看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怎样,是首先重要的文学评论。
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有人称赞张爱玲小说描述了平凡人的生活。但是小说中人物可以是平凡的人;却不可以是平面的人。平面的人没有个性。例如《阿Q正传》中的人物是立体的,阿Q有个性。《雷雨》中的人物是立体的,例如繁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
阿Q的一句“我祖上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体现了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生动的典型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因为这句话再形象不过地体现了:国人动辄拿祖上说事的陋习,其实,你祖上就是当过皇帝又怎样?你现在不是穷得叮当响?
所谓立体的人物就是“有棱有角”的人物,就是有独特个性的人物。阿Q因其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文学形象。看看百年后今天的中国,阿Q仍然随处可见。可以肯定的是,在可见的将来,阿Q仍然是国民个性的突出代表。阿Q是不朽的。有个性的文学人物不一定是不朽的;但没有个性的平面人物,肯定是“匆匆过客”,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有生活气息,却没有个性化的特点。读张爱玲小说,其中的人物难以给读者留下阿Q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印象。可以说,张爱玲在塑造文学人物上是不成功的。让人怀疑,小说家的张爱玲是否明白:小说创作中最重要、最难的是人物塑造。
若说张爱玲的小说有什么成功之处,那就是她很会讲故事。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与集市上说大鼓书中的讲故事没有多少水平上的差异。因为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含量、知识含量、历史风貌与社会状况的含量太低。这种“太低”决定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涵有的审美意义,不过是没落贵族犹如夕阳将尽时的那点惨淡的余晖,绝无审美意义上的精神震撼。
1940年代末期中国贵族无可奈何的落日景象,其实是很有历史意味的,这类体裁即便写不成文学巨著,也很容易成为张爱玲小说丰富深刻的内容。只是停留在会讲故事层面上的张爱玲,没有能力驾驭这种题材罢了。张爱玲1940年代的“孤岛”走红,与其又在新世纪的大陆走红,其深层原因都是一脉相承的,这里不多谈了,仅指出一点:张爱玲在大陆的两次走红,都是人们文学欣赏中审美情趣低俗的表现,这种“表现”其实是时代人荒芜的精神世界的缩影。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层次的审美呢?
(四)是什么决定了审美水平?
如上所述,围绕着文学艺术,人们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趣味有着雅俗不同的层次,是个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这种雅俗不同的审美层次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层次、截然相反的审美思想?
一般地讲,决定一个国家里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文化修养必定有着不同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思想。喜欢看赵本山的小品、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喜欢看世界文学名著,看上是无可厚非的“萝卜韭菜,各有所爱”。但这种体现了雅俗有别的欣赏水平,却隐含着读者的文化修养水准问题。数亿人争着看“出洋相”的小品;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也喜欢看“出洋相”,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有待提高的。
在人类经过了数百年全球化的今天,看问题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否则固有的结论往往可能是落后的,甚至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例如,相去不远的女人缠足,是中国文化中审美思想的使然:“三寸小金莲’被千百年中的国人视为美的象征。其实这种审美的本质是残忍的女性歧视。直到西风东渐后若干年,这种野蛮、粗鄙的审美陋习才被彻底根除!如果没有西风东渐,这种审美陋习还会存在多少年?所以审美应是开放的,应有世界的眼光。
再如,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认识,没有人类文化交流中审美观的变化与提升,不可能有刘再复《批判双典》这部巨著。刘再复在这部书里表达的思想,刷新了国民的审美观。
《批判双典》认为,“双典”把关云长、张飞、刘备、武松、李逵、鲁智深等这类杀人不眨眼的人讴歌为英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观?“双典”宣扬杀人解决问题是“替天行道”,是仗义执言,是坚持正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双典”里的女人都是祸水,这是一种让现代文明人震惊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思想。人类没有了女人是不可思议的;审美的世界若没有了伟大的女性,必定堕落为“双典”宣扬的愚昧、野蛮、有悖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陋识。事实上,一个把女人视为祸水的民族,其民族精神必定是落后的、愚昧的。刘再复的《批判双典》这部具有颠覆中国文化审美观的巨著,对中国人有着重大的启蒙意义。
但是这样一部巨著所以出现,不都是在人类文化交流中成为可能的?“双典”问世六百年中,生活在中国文化里的中国人从未怀疑过“双典”的审美思想。直到人类文化出现频繁交流的今天,才有了刘再复《批判双典》的问世。
不过问题远没有结束:由于“双典”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长期流行中国民间,刘再复《批判双典》中闪烁的审美思想,不太容易为国人普遍接受。就是文学艺术界对《双典批判》也持冷漠的态度,这不是很发人深省的吗?不仅老百姓仍然看好“双典”中的审美思想;就是今天的教科书不是仍然把“双典”正面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如此教育,岂不咄咄怪事?
于是看来,通过提高人的文化水平,来提高人的审美水平很有必要也很难;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变得像一个鸡犬相闻的村落,人们通过文化交流中改变落后的审美观,怎么会这样难呢?
结束语
审美是人的天性,婴儿都有审美意识。这是科学家早已作出的论断。事实上,婴儿见了容貌好看的人会笑;见了面貌丑陋的人会哭。这是平常人都知道的现象。所以说,审美与善一样,都是造物主赋予人的天性。既然善应该在后天得到养护与培养才能发扬光大;那么,人的审美思想又何尝不是在后天的文化修养中丰富提升起来的?
蔡元培当年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其实是个很有思想洞见的说法,其中暗含的“审美必定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自不待言。与西方谚语“喜欢音乐的孩子不会犯罪”内涵的道理一样:喜欢音乐是一种审美现象,这种审美对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上所述,既然善是美的基本特征;那么审美则是一种向善行为。道德水平在向善中得到提高,不是必然的结果吗?
都知道,人的审美水平是在读书中攀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说法与传统中的“知书达理”是一个意思:读书人懂道理,懂道理的人既明白道德操守的重要性;也明白审美水平是在读书中提高的。
总而言之,审美与道德、与善密不可分,审美在读书中提高了水平,也必定弘扬了人性善,培养了人的道德。所以,几十年来的道德在走下坡路,人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进行道德说教,做着“西西弗滚石头”的无用功。却不知:长时间的道德下坡,都是过去长期的“读书无用论”的逻辑结果!何况在道德下坡路上,不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几亿人都争着看“出洋相”,就不仅仅是个审美水平的问题了;这个审美低俗现象掩盖的道德危机、人性善的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的说法——不过这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