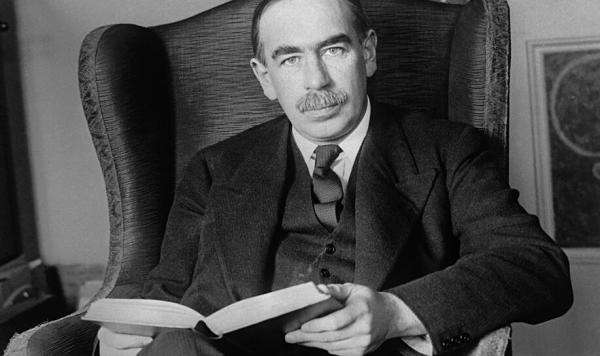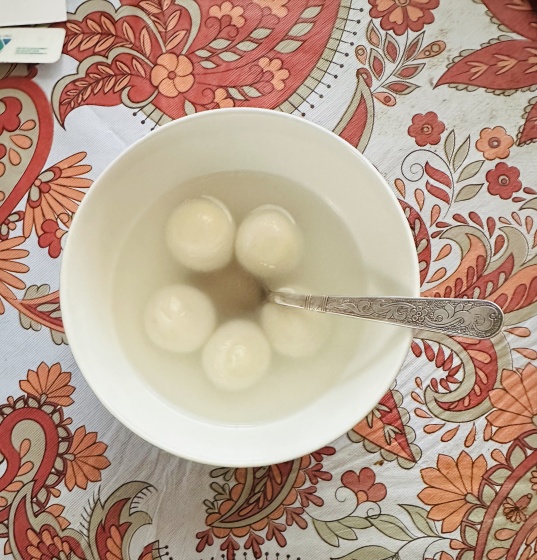在李泽厚看来,“强烈的历史意识”就是儒家哲学——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了,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是什么?李泽厚没有多讲,不过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呢?李泽厚借《战国策》给出的答案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于是看来,所谓的“强烈的历史意识”这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过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以史为鉴”。然而,凡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以史为鉴”虽为历代统治者及文人所推崇,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是中看不中用的教条,实践中屡屡重犯历史的错误,这个现象代不乏出,可谓“屡鉴屡犯,屡犯屡鉴”,成为历史上一道久远的“怪圈”风景,为什么会这样呢?李泽厚从未谈过这个问题。下面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
众所周知,中国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资治”、为一般人提供道德示范——严格说,这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意义。然而,这种为统治者服务、为后人“蓄德”的“史学”,是大可怀疑的,数千年的史实证实,不管在统治者的政权那里,还是在民间、学界,上下一致推崇的“以史为鉴”,其实从来都是一句空话。例如:
(1)一边是“以史为鉴”的危言耸听,一边是数千年不断重复大同小异的历史错误——什么“周期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城头变幻大王旗”,其实中国历史都是在重犯错误中的“周而复始”。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避免这种病态的“周而复始”呢?这是一个数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2)一边是王道仁政的号令天下,一边是阴谋诡计中的机关算尽;满嘴的仁义道德与满肚的男盗女娼,是中国古代上流社会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声虽震古烁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戒却也人人践行不辍;朱熹的一句“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间”,括尽儒家的道德文化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的空谈本质。
(3)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不绝于耳,人人概莫能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是世人都践行不辍的圭臬。所以才有了当代学者王学泰揭示的“另一个中国”社会:“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王”“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杀富济贫,替天行道”②。即便是大讲“君子之学”的上流社会,“伪君子”竟代不乏出,多如牛毛,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场芸芸众生。
于是看来,“以史为鉴”虽然被长期奉为编史的原则、读史的目的——也就是李泽厚所谓的“历史意识”,实际上人们一直都在重犯历史的错误。这个事实说明,所谓“史学”在“以史为鉴”中,成了一堆没有多少用处的“废话”。中国“史学”的这一事与愿违的现象,至今也没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探讨这个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讨“以史为鉴”为什么会形同空话——从而使李泽厚看重的是“历史意识”蕴含的“根本精神”,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科学的立场上实现真正的“以史为鉴”——这也是本文抛砖引玉的初衷。
二
数千年“史学”的宗旨其实是为维护君权统治,向统治阶级提供“资治”。所以内容大都是“帝王将相”史。那些口头上“民以食为天”的人们在编写史书时,却少有关于生产力方面的史实记载与看法,中国“史学”不关注生产力,不关注经济发展,不关注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所以这门“史学”不提供解决吃饭问题的史实借鉴与思想启发。“史学”除了记下零星点滴的技艺,并没有科学的一席之地。当然中国古代也没有科学,不存在“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生产力变革,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这样的社会现象——这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式与方法,长时间不能为中国人接受,直到西方已经完成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满清后期,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到中国,还被清廷斥为“奇技淫巧”。不关注老百姓吃饭问题,是官办“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毋宁说也是其致命的弱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所以中国数千年徘徊在农业文明社会,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儒家在政治上宣扬王道仁政,“史学”里的那些“资治”都在王道仁政的冠冕堂皇中,变为统治者的以身作则、体恤万民的招牌,所谓“资治”不过是统治者用来粉饰个人道德操守的“资源”——在政治上讲道德,可能吗?儒家天真地认为“人皆为尧舜”,不仅帝王可以成为尧舜,黎民百姓也可以走向尧舜。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治国安邦,除了帝王的“仁政”,就是官民一致推崇的“尚贤”。“仁政”与“尚贤”的根本意义汇通为同一个道德问题,代表了儒家“以德治国”的中心内容。所以“史学”除了提供“资治”外,还为官民“尚贤”提供借鉴。这一切看上去面面俱到、顺理成章,然而在实践上却从来就没有行得通过:既没有帝王效法尧舜施仁政,也没有上下官民“尚贤”近尧舜。有的只是统治者穷奢极欲在挥霍中对黎民百姓的无尽盘剥,以及上流社会代不乏出的伪君子当道与华夏神州“另一个中国”的我行我素。动听的“仁政”与美丽的“尚贤”永远停留在口头上与书本上,无人见诸于行动,也不可能见诸于行动,这种泛道德文化的国家永远是个乌托邦。
这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现象说明,“史学”维护君权统治的宗旨就是错误的。其中以史为鉴中的泛道德化思想理念并不切合实际。由于“史学”的宗旨与思想内容千百年不变,“周期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便成了长期存在的现象,并长期困惑着中国人——“统治者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前朝垮台的教训,最终都是重蹈覆辙?”——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周期律”便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持久的不解之谜。
其实,这个“不解之谜”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所谓奥秘与“贪官屡禁不绝”一样,都是人的天性使然,都是中国文化不承认自私贪婪懒惰是人的天性,特别是不承认“肉食者鄙”!这里的“鄙”不是教科书上说的目光短浅,而是“肉食者”在官场上的道德品质是很成问题的,是不可信的。所以中国“史学”奉行泛道德主义的理念,是造成中国“史学”以史为鉴永远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
关于腐败——没有不腐败的王朝,也没有不反腐败的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无法解决的悖论。在“封建社会”里,反腐败可能收一时之效,但最终仍然屡禁不绝。朱元璋用活剥贪官人皮以儆效尤,这样让人毛骨悚然的反腐败,结果还是有贪官以身试法。也就是说,活剥贪官人皮这种极端残忍的血腥做法都不足以震慑贪官的出现,说明对贪官的任何惩治都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反腐败是没有实际效用的,腐败只能靠制度建设予以杜绝。为什么“活剥皮”不足以震慑贪官的出现?对这个现象的唯一解释是:自私与贪婪是人的天性,天性是难以杜绝的——人的天性有着魔鬼般的力量,理性无法控制。所以在腐败问题上讲道德,无异于对牛弹琴。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腐败后终于发现,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腐败,腐败的“专利”属于权力者,没有权力的人想腐败也枉然。所以根治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制度上针对权力做足文章,避免集权、越权、超权与不受监督的权力出现,避免统治者“权大无边”,避免有权的人滥用权力,舍此别无他途。于是便有了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都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政治常识了,这里不赘。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将贪官的屡禁不绝与朝廷不接受前朝垮台的教训进行类比,可以明白无误地对上述“周期律”互为例证,显示其“庐山真面目”:
最高统治者皇帝与所有的官员一样,是人不是神,而皇帝因为自身的优越地位与有利条件可能更加自私与贪婪,由于其行为不受约束,其贪婪不像官员“犹抱琵琶半遮面”,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我行我素,可谓贪得无厌。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枯井”;然而。用来“填枯井”的“货源”总有枯竭的时候,此时便离“揭竿而起”不远了;当政权腐败到国家机器烂透了无法正常运转时,王朝的末日便来临了。所以“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与贪官都是葬送在自我腐败中,这是“封建社会”里历代王朝的“宿命”,也是数千年“周期律”的全部奥秘所在。而中国的史学远离这个“奥秘”,无视“政治上讲道德是没有用的”这个历史教训,仍然在泛道德主义文化中“以史为鉴”,不断地“重复历史的错误”。
有人举例“明末崇祯皇帝如何励精图治、俭朴敬业,怎么也垮台了”?一个政权的垮台不仅仅是统治者个人的腐败,更重要的是政权的集体腐败,国家机器烂透了怎样运转?岂有不垮台之理?何况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后宫皇家地窖库里搜出了几十吨银子,说明崇祯也是个大贪,而且是置国运于不顾的大贪。大明王朝的结局虽很悲惨,却是个绝妙的讽刺:就在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京畿之际,崇祯皇帝还哭穷国库空虚无钱解决兵马粮草问题,要求满朝文武大臣捐款自主军队开支御敌;崇祯皇帝平日里“以史为鉴”中,废寝忘食地披读经书的那些苦功夫,竟换来了自己吊死在煤山上。
五
所以李泽厚津津乐道的“历史意识”不过是无视历史真实的一厢情愿——“中国人活着的背景、依靠根据”,这话虽然没有说错,却成了愿望与事实相悖中的自我反讽——只是这种反讽李泽厚本人未能意识到。毋宁说,这是有损李泽厚的大学者形象的。于是看来,李泽厚推崇的“历史意识”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由于上述原因,在“封建社会”里既没有精神意义,也没有实用价值。不知李泽厚是否清楚:中国“史学”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就被人批评过——供帝王在“周期律”中“循规蹈矩”的;供政治家“百忙之余”休闲的;供“条陈奏折”中“旁征博引”的;供坊间市井百姓饭后茶余笑谈的;就是不能提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因为中国“史学”既不关心社会的进步,更不关心人类的生存——百年前读书人对中国“史学”的这种“嬉笑怒骂”,看上去是在调侃无用的“史学”,却直戳中国“史学”失败的要害。
那么,中国“史学”的出路在哪里?换言之,“史学”怎样才能摆脱“御用”的陈腐观念、抛弃官学的重负,真正实现为人的精神提升、为社会进步与发展提供“鉴戒”?这个问题是篇大文章,有待于观念的转变,有待于消除“史学”中的官本位意识——这些谈何容易!它意味着一场变革——中国“史学”从“官学”回归科学研究,不啻为一场重大的学术革命。这似乎是个有待时日的问题,然而如果“史学”不能回归科学的立场,不能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仍囿于传统的“为帝王师”中,只能自寻绝路。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看到,国际学术界毕竟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经验可资借鉴,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中,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不会走太多的弯路。
注:
①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4日。
②王学泰著《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版。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