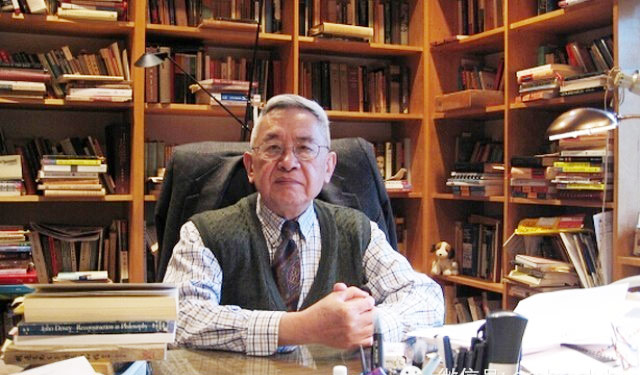这句颁奖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传统学者研究历史的宗旨;另一个意思是,余英时用其毕生所学所作对这个宗旨作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先看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言辞并不晦涩难懂,比较直白,不难理解,意思很明显: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搞明白古往今来历史变迁的规律。
实际上这个被“唐奖”颁奖词称为传统学者治史的宗旨,岂止是学者治史的宗旨?四书五经里的那些文字,又何尝不都贯穿着这个宗旨的思想?
例如,被誉为中国文化最高哲学理念的“天人合一”,难道不是“究天人之际”的翻版?也就是说,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治史的宗旨,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问题的严重意义在于:中国人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历时两千多年,至今也没有探究出天道与人事到底是种什么关系!
这种探究的结果,除了一句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天人合一”的空话外,就是为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君权神授。
于是皇帝的圣旨便有了经久不衰的神圣力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实际上,无神论的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君权神授”。连当代著名学者王学泰在《流民文化》中“发现的另一个中国”里的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江湖人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
所以历代硕学大儒践行“究天人之际”中的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几乎毫无思想学术成果,不过是为维护君权统治搞了个自欺欺人的理由罢了。
实际上天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天道,那也是天体间的运行规律,宇宙中的规律——与尘世人事有何相干?
所以说,不仅“天人合一”是一句没有用的空话,就是“究天人之际”也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一代又一代传统学者的治史是在一个伪命题上皓首穷经;就是人类进化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是仍有人,例如“唐奖”颁奖词,将“究天人之际”奉为治学之神圣的圭臬?
拿一个伪命题当神圣,“唐奖”颁奖词是很成问题了!
下面我们再看看另一句“通古今之变”,是否就成立呢?
我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了:历史没有规律。
不仅人类历史没有普遍的规律,就是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没有历史规律。
规律是指可以在相同时间(条件)反复出现相同现象者为规律。
例如,春夏秋冬是在相同时间反复出现的相同现象。这叫自然规律。
例如,“加在密闭液体上的压强,能够不变它的大小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是帕斯卡尔定律。反映了压强加在流体中,只要条件相同,就有向各个方向传递的规律。
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
欧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教会与国王共同管理国家的中世纪“双套马车”的历史。中国没有这种历史过程。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皇权中央集权体制社会。欧洲从未有过这种社会。所以教科书上说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实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
有人以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的“周期律”举例说中国历史有规律。
“周期律”之说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况:
秦朝存在了十五年。汉朝存在了四百年。隋朝存在了三十七年。清朝存在了二百九十五年。王朝存在时间差异如此之大,哪来的“周期律”?
至于王朝更替,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种作用千差万别,不一而足。而皇权中央集权体制却不变!这样的中国历史事实,何谈“周期律”?
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所谓“通古今之变”隐含的搞明白历史变迁的规律也就无规律可言了。所以“通古今之变”其实也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
本文并非说余英时先生搞了一辈子伪命题的研究。而是想说:“唐奖”汉学奖的颁奖词拿伪命题说事,称赞余英时先生对伪命题作了最佳的现代诠释。这个存在明显错误的说法,是“唐奖”颁奖词作者对中国传统学者的史学宗旨的理解有误,还是对余英时史学思想、史学贡献的认识有误?
众所周知,“唐奖”的奖金数额远远高于诺贝尔奖!如此不堪的颁奖词,是“唐奖”本身的思想学术含金量有问题,还是余英时的思想学术有问题?
余英时的思想学术成果,有其等身著作摆在那里,不必赘言。剩下的,就是台湾“唐奖”汉学奖颁奖词有问题了。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