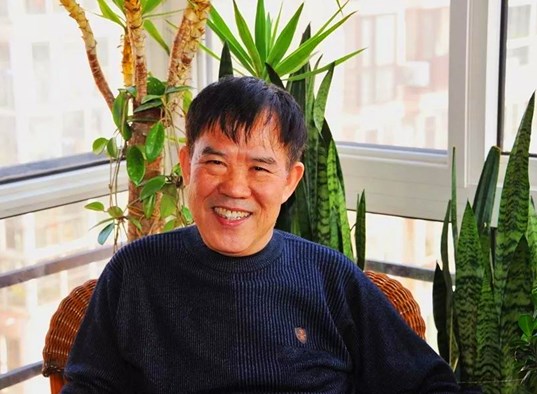我和李工认识很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青岛市图书馆等单位发起评选“十大藏书家”活动,经过层层考察推选,十大藏书家终于出炉,颁发证书仪式在青岛图书馆举行,我作为记者去现场采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工。
在那些温文尔雅的藏书家群里,李工显得有些“土”。我一问,果然,李工来自市郊崂山,是一家企业的厂长,我又有些吃惊,在农村,还是企业的厂长,他怎么会有那么多书,而且藏书家的评选不仅仅是比书籍的数量,还要考察读书的质量,也就是说硬件和软件都得行。我问了李工几个问题,记得有“为什么买那么多书?”“当厂长很忙怎么挤时间读书?”“你读书的目的”等。
记得他说从小就喜欢读书,即便是当厂长,那些管理学的书也很实用。由于他没有更多业余爱好,空闲时间基本上就是读书,他还尝试着写点东西。
过了几年,听说李工辞掉厂长职务专心回家读书写作了,我又吃了一惊,放着好好的厂长不当,读什么书啊,当下社会人心浮躁,谁不急吼吼想着挖钱,李工却看着钱不捞,真是稀罕啊。
我在电视台的同事王辉湘是从《前卫报》转业来青岛的,他也喜欢读书,颇有知识分子儒雅睿智之风,王辉湘数次提到李工,说目前像李工这样的人太少了,他提出我们几个所谓作家,应该去拜访一下李工。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和刘涛、栾新建、王辉湘等人就到了李工家里,中午在李工家里吃的饭。记得那天我们谈的话题,全是哲学、历史和文学,刘涛当时在青岛晚报编副刊,栾新建在青岛电视台为专题节目撰稿,王辉湘是青岛电视台《新闻广场》节目负责人,我在广播电台跑专题,我们年轻气盛,恃才傲物,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与李工争论得面红耳赤。
李工那天很健谈,我们临走时还得到了李工的赠书。
许多年过去了,李工一直没有放下读书和思考,当然还有思考的结晶——写作,前不久我在李工家里做客,看到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学者或作家,尤凤伟、刘海军、徐培范、柳士同……真如古人所说“门前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些老朋友纵横捭阖、议论风生,有时愤世嫉俗,大骂肮脏丑恶,有时则心平气和讨论某个作家学者的新作,长短得失,甘苦寸心,明亮的客厅里起伏着学术观点,流淌着真诚交流的声音。我突然有些感动,觉得有这样一个探讨和研究学问的地方真好,空气纯净,思想温暖。这些人有着过去“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特征,一群暂时没被世故和铜臭击倒的文化人,李工的家是难得的一方净土啊。
李工现在被一些媒体称为文史学者、人文学者,其实他原本是从企业熬出来的。
他19岁进运输队,最初是每天拖着载有一两千斤重的货物的平板车,“爬”行数十里路,后来进工厂当工人。在那些无奈的日子里,因有实践经验,他很快地进入了技术角色,能独立完成设计任务,成了机械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设计过的图纸达一米半厚。为了做好设计工作,他白天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晚上就自修大学课程,自学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机械原理、金属材料热处理、电工学等大学机械专业的教材,其中的艰苦自不待言。他用两年时间自学完了别人四年大学才能完成的机械专业课程。多少个夜晚,他在昏暗的灯下苦读,做各种计算题。有时困得睁不开眼了就用冷水洗头。
在80年代恢复职称制时,从事技术工作的同事以一纸大学文凭便被授予相应的技术职称。而他这个没进过大学门的人,虽已独立从事设计工作多年,却与技术职称无缘,于是将自己厚厚的图纸送到县技术职称评定办公室,问“哪个工程师设计过这么多的图纸?”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向市人事局打报告,终以“有特殊贡献的拔尖人才”的名义,给他颁发了一个烫金字墨绿色的工程师证书。为此,家人为他设宴庆贺,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如此来之不易的工程师称号,虽然凝结了他太多的艰辛、痛苦、挣扎与无奈……但在一个不管怎样努力都难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里,绝大部分人其实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个人喜欢的工作。因为李工并不喜欢技术工作,自幼酷爱文史——这一爱好终生不废。为了摆脱苦不堪言的重体力劳动,他才不得不把视线转向技术。
退休之后,李工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写作、讲课。他在青岛市图书馆等地举办的讲座广受欢迎。他在学术上的观点总能独树一帜,观点新颖,比如,他在《源远流长的苦难美学》一文中,对孟子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作过深入剖析,指出这段话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似乎凡是想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必定要经受一番苦难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李工说:孟子的这一“告诫”,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不仅成为中国人建功立业的理念信条,还在民间通俗化为一种人人皆知的生存箴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苦难美学。实际上,就像李工所说的,苦难并不必然地导致伟大,经历过苦难的人并不一定有出息、有作为。李工指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类人物的生活经历够苦难了,但这些人除“神情麻木,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外,有什么出息?牛顿、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等伟人,这些人的个人经历却说不上苦难。他们的那些杰出的成就、卓越的贡献,都难以说是从苦难中磨炼出来的。实际上一个人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像胆量、意志、毅力、斗志等品质,并非都是在苦难里炼出来的,而是一种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磨炼和精神修行。就像高尔基所说的“哪怕是对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克制,也会使人变得强而有力”。
李工就是这样敢于“想别人不敢想,发别人不敢发”,惊世骇俗,特立独行,刚正不阿,发散着知识分子难得的批判、理性、锐利的气息和锋芒。
李工读书很多,且涉猎文史的大部分领域,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诸方面有关。他写下了一些颇有分量的文章,如《中国文化中完美的精神载体——续上古典诗词的香火》《源远流长的苦难美学》《人类近代以来几次重大革命浅析——对1990年代“反思”的批评》《〈绝代风流〉中的西南联大》等,发表在《书屋》《社会科学论坛》等国内有名的学术杂志上。这些文章动辄数万言,少则三四千,没有急就章,满篇浸透思考分析论证的严谨和灵动,可是稿费很低。李工对此心知肚明,他写作和发表文章不是为了钱,他淡泊名利,要挣钱几十年前继续当厂长就是了,何必退下来蜗居一隅自甘寂寞?他目前生活温饱有余,把主要精力都投到了无穷无尽的学术研究中。
李工知道,自己所写的文章其实读者群很小,基本局限在学术小圈里,但仍受到读者的喜爱。北京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很喜欢他的文章,经常索要新写的东西,先睹为快。在本地,写他这种学术文章的人也不多,所以有时他会感到很孤独。不过,李工对此的态度是,自己已年逾古稀,不求名利,只想安安静静地看书,专心地写点文章,自娱自乐,对读者有所启发,有所教益,仅此足矣。
原载《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
2021.8.16 A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