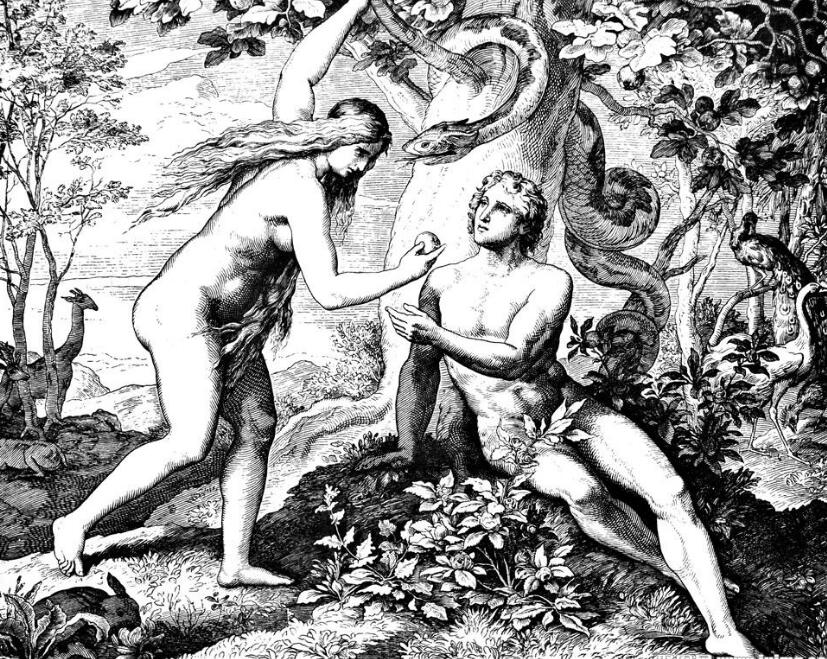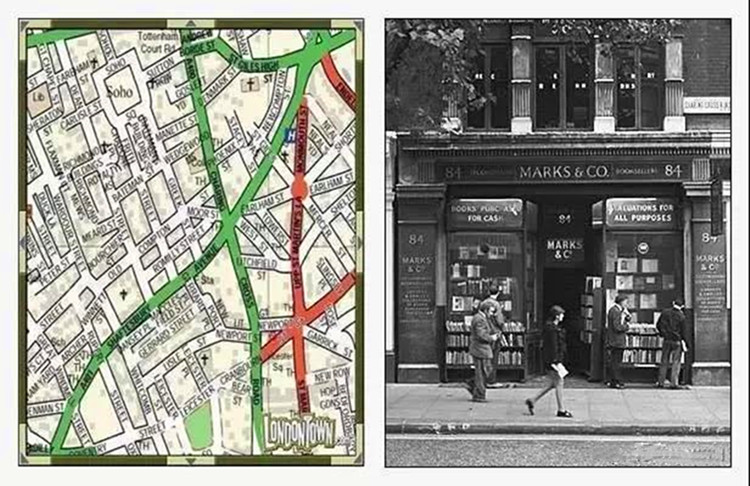八 人群
71
72
写WR:少年WR拿着高考成绩单找到学校,找到教育局,找到招生委员会,要求解释。他被告知:考试成绩有时候是重要的,有时候并不重要。他被告知: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你应当服从祖国的安排。少年WR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被送去远方,送去人迹罕至的西北边塞(陕北的清平湾吗?为什么清平湾呢?因为阅读这个笔记前,我只读过清平湾嘛,我不想起来又想起来哪个嘛,清平湾的印象太深了)。写到母亲做爱受孕(抒情沉痛无比,出于想象。想象的强弱源自共情的强弱)。
73
写Z:Z的母亲同样枉费心机。写到:写作之夜,空间和时间中的真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印象(这个笔记改成务虚印象,也不错。印象的现代性较多,笔记的古代性较多)。写到我和Z:与我同班。写到Z的书目(才初中一年级,我那时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黑格尔,就是大学,买到过小逻辑,硬是看不进去,还有美学,买到过两三卷,没有买齐,当然没有读下去)。写到Z:开始吟诗作画(才初中一年级),选定了出路(才初中一年级),选择了美术(才初中一年级)。
74
写Z的初中生活:住宿生。写我:我记得,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降临人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以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为开始。1966年8月8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7年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时候的大字报成了最恐怖的噩梦、最龌龊的表情、最邪恶的思维方式、最离间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最深的心灵的粪坑,最大的语言灾难,最肮脏的表达工具。这时候的中学生成了造反的红卫兵小将)。
75
写C和X的重逢。写我或者诗人L。写青春期的性意识的梦遗的出现。
76
写文革:在我的印象里,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风暴,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随着一群青春少女懵然无知的叫骂声开始的(从少女们的变化,角度不一般)。写到:一位不能寂寞的(寂寞?这个词太轻了,对于)伟人。写到L:诗人L呆呆地在那条小路边站了很久,在我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那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那一天风和日丽。那一天有一副对联震动了四分之一人类的耳鼓(哪副?)。
77
写对联。写到:F医生、女导演N、女教师O、未来的残疾人C、我和诗人L、画家Z、流放者WR。写到:不过,可能一个人不是这样。他就是画家Z。还有一个人不会这样——WR,但那时他早已不知去向。写到Z:此后好多年,我没有见到他(文革戕害了整个社会关系,一个没有涉入的没有,一个幸免的没有,一个干净的没有,个个都是受害的,又是害人的。有的人论证,21世纪后的中国,进入互害社会。其实不对,文革就进入了,就达到顶峰。现在不过又一个,这个频率超过伟人的预言:七八年就来一次,现在年年这样,月月、日日,这样)。
九 夏天的墙
78
79
写L:十岁。L十岁,爱上了一个也是十岁的小姑娘(天啊,十岁!初恋!这个比面海这个诗人早了五六七年嘛)。写到Z的十岁,和L的十岁,和我的进行比较,或混淆。我的角色好像场内的旁观者。写到未来的女导演N,和未来的女教师O,写到T(T没有一直交代清过,只提到过代称,到了交代的时候了吗),和我的进行比较,或混淆。我的身分好像场外的旁观者。
80
写到那座美丽的楼房(那儿有那个小姑娘、少女T)旁边有一家小油盐店。写L最愿意做的事,就是替母亲去打油、打酱油打醋、买盐。写L和T的对话,两次,美极了。写到L: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写T:这太像是O了,这很像是N,和我的进行比较、或混淆。还是写L的初恋,或单恋。
81
写L的十二岁或者十三岁的那个暑假的一个礼拜日。写写爱情故事的小说(我大约一半读过,一半没有)。写到母亲:母亲在窗外的夏天里喊他:“L,别看啦!出去,喂,到外面去走走。”“L,听见没有?出去跑一跑,书不是你那么个看法。”写到牛虻(记得好像看过,又好像没有)。多次写到母亲喊他,美极了。还是写L的初恋,或单恋。
82
写到十五岁的L,和T。写到答案:答案,在生命诞生的时刻,就已存在。只是等待发现。写到真理:怅然若失,是少年皈依真理的时刻。写L:L在河堤上坐下,不想回家。写到L的性幻想,具体地说,对女人的肉体或性器的幻想。写到L的性成熟:少年娇嫩的花朵在河岸的夏夜里悄悄膨胀(写得真的高雅,或高贵,这个不能否认,或否定)。
83
写到然后:然后,一场革命来到了。写到革命:革命,无论如何是富于诗意的(要知道,这的革命当然指的文革,富于诗意?这话怎么理解嘛?还是富于煽动性?富于颠覆性?富于狂欢性?富于群众性?富于盲目性?富于暴力性?富于摧毁性?富于毁灭性?富于?诗人L将怎么回答呢?另外,不论任何方面或理由,诗意这个词的能指和所指,所代表的语义或意义,现在令我都产生怀疑或厌恶)。写到诗人L:诗人L隐约感到,真正的生活提前到来了,还有真正的革命(要知道,真正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生活。二者不具有因果关系,而只具有相关关系。换言之,没有文革,真正的生活可能更将提前到来,可能更将推后。总之,它将到来,伴随着成长或发育,特别是少年的性意识。真正的生活或生命意识应当从产生了性意识的那刻——哪刻?几个少年印象深刻过:它出现的时间、场景?紧张或恐惧?惊讶或惊喜?不知所措的懵懵懂懂或心如明镜的蠢蠢欲动——,这里并不是扩大性意识的作用,而是说,性意识让一个少年觉得,它又美妙,它又难过,它指向着一个个眼前的性对象,可却不知道她或它在哪?也就是说,它唤醒了它是什么的问题意识:它来自哪儿?它要去哪?它——指问题意识——引导着一个少年进入认识它的进程,虽然可能一生都不可能认识它,它的作用仍将是引导。而且,它——指真正的生活的到来或性意识的到来——不受什么外部因素的影响,它和外部因素几乎没有关联。除非它真正地与外部因素建立或发生交织、交换、交融或交合的关系,否则依将独立或封闭的存在,它仍独立或封闭下去。它具有天然的成长性、开放性或侵入性,也就是到来性)。写到L:L,很显然,这时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或者说,性欲的产生使得一个人产生出表达的欲望,这个表达往往以诗的形式,这个欲望将产生出自己的语言。诗起始于性欲了吗?实现性欲的手段,还是目的?其实,目的即指向手段,手段即指向目的)。写到奶奶:只身一人被送去农村了(直接受到文革冲击的头一个却是奶奶:这个地主婆或地主家的女儿。这点和从少女们的变化入手,是对应的或呼应的。也就是说,女人们首先被影响或冲击。另外,对于少年们或红卫兵们,文革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或激情乱用的集体革命行动的机会或舞台,那么,对于奶奶,特别对于地主这个不可缺少的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或重要要素的女人们来说,文革则是一场冲击个体的反革命行动。文革恰恰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写到母亲:母亲说:“城里,好多地方在抄家了。”(我想起来我们家也被抄过,连我出生后得了大病,原尚村的大伯给我打得一副银的长命锁给都抄去了。那时候我大约才上小学,我就懂了,什么叫做害怕,什么叫做仇恨,什么叫做)。母亲说:“听说有的地方打人了。”母亲说:“听说有的地方打死人了。”(现在为止,奶奶和母亲这两个人物写的特别好,印象深刻,我感觉。另外,史铁生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或者初衷或着力的方面?我来去问他一问,又无法去问他了)。
84
写到L:诗人L沉默不语。很久很久之后他忽然问道:“可是为什么,性,会是羞耻的呢?”诗人说:“你敢说一说你的性欲吗?”写到亚当和夏娃:诗人说:“亚当和夏娃懂得了善恶,被逐出伊甸园,为什么他们首先感到赤身裸体是羞耻的?”(这让我惊讶,或者说,惊异,惊疑:那可是文革前后啊,史铁生或者诗人L,将从谁的那儿,听到过或看到过?前面我提到过,1949后,关了妓院,也关了教堂,当然禁止传播,大陆的基督教摧毁殆尽,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又一次从香港,进入,传开了。除非北京的地下,还有传的,说不定)。
85
写文革。写到打死了这三个字的语言学或社会学方面的意义或现象。写到全国大串联:那正是L梦寐以求的。写到L去串联啦!那年诗人十五岁(那年我才五六七岁)。少女T也去了。
86
写L在隆隆震响的列车上度过了十六岁的生日。在昏暗的车厢里,一辆运货的闷罐车,L和一个成年但是非常年轻的姑娘差点儿发生性关系。L只是摸到了乳房:不很大,但是挺耸、充盈,顶部小小的突起那必是乳头了,一阵风暴似的东西刮遍了诗人全身:“啊,你还那么小。”然后L下了车,离开了那姑娘,从此永远离开了她。然后L又上了车,他再也没有看见她:为此,诗人,是惋惜呢。还是庆幸?
87
写L的自责:罪恶,但这是罪恶呀!
88
写L:L开始给T写信。写诗。
89
写L的那个日记本不见了。写它被一页页撕开,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栏里。写我记得某一天夏天就要结束了,那一天诗人成为“流氓”。写L被带走了(这个无情、无知、无法的:国家还是社会,集体还是个人,种族还是文化,还是)。
面海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