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小片至少距今七千年的河床行走时,没有年代久远了的虚幻感,反而很实在。三个小时的行走,相对于已去的七千年和没来的七千年——假如有未来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实在太短暂了,连个屁都来不及放完——恕我吐出脏字,我只想形容看似挺长的烈日曝晒下的三个小时融入时间长河如同瞬间。生命附着于这样的地方,直观的感受是微不足道。因此,古河床上,生和不生,无限接近没有分别。在这里,源于同样的原因,也无死和死去——如果用物的思维沉入自然而观察。
怎么行走、看到什么都不重要,由于恒定的事物已然存在,非恒定之物只能做物是人非的参照。让我纠结不清的是人类意识的悲剧意念应该指向何处,是古河床还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时机努力生长的柽柳?
孤岛是河床的必有之物。孤岛其实是些沙丘,因为隆起,大水漫过,也不灭顶,植被树木依然存在,生长得很好。沙丘之下,水浸日久,植被和树木转换了生命形态。现在水已退去,走到一棵柳树跟前,四周是苇子和鸟鸣,有高过人头的苇子也有贴地生长的苇子,有水鸟如白鹭的叫声也有旱鸟如麻雀的叫声,组成运动的漩涡,让我晕眩。柳树早已枯死干裂,并非缺水而是水浸过久而进入腐烂阶段。进程缓慢而简单,尤其在古河床,如同虚设。我眼前的柳树只剩半截腰身,自然断裂,裂开的伤口新鲜安静,仿佛不曾经历什么。它的听和看属于过去,如今它以伫立,进入自身内部而忘却外界。“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侣,然后将心扉关闭”,难道它沉入了艾米莉·狄金森诗句里的境界?
沙丘顶部有间“沙屋”,不远处一艘“沙船”,搁置在河床。失去了水,它们成为摆设。假如不久大水再次漫过,捞沙者的活动还将继续。而对于古老的河床,这一切,相当于它孕育滋长的浮萍。此时我只想离开沙丘,进入“平地”,与古老一起,感受现在。
完全裸露的古河床,放眼望去如同沙滩,专业的说法是由亚砂土和亚黏土构成。它们在水下太久,无缘见到,终于连年干旱后,呈现我们面前,呈现的是新鲜而非古老。一面镜子擦掉了雾气,镜面洁净,似乎可以映照什么。它是朝气蓬勃的,绝无老气横秋。是面金色的历久弥新的镜子,搞怪地看着我,仿佛纳闷我为什么比它还苍老。白云和飞鸟在它里面驻足,而我是缓慢的爬虫。
比我还慢的是河蚌、河蛏、螺蛳等。河水不是一声唿哨,急遽消退,而是迟疑地、缓慢地后撤,如同迟钝的老人卷一张薄薄的纸片,打一卷看一会儿歇一会儿。可对于反应更加迟钝的壳类动物,还是太快了,它们被遗弃在河滩,很快死去。长而宽的河床上,它们凌乱又有些慌张,纠结困顿的表情被定格,身体插入泥沙,再也动弹不得。死去是我对它们的认知,也许古河床并不这么认为,但我的认知仅仅局限于此。
我在它们的队列中穿行,像要寻找古河床的故事一般。河床上如果发生过什么故事,也一定超出了我能想象的边界。我闯入这里,无异于外物侵入,打扰了此地宁静。此时观察那些蚌壳,只觉得美丽,与它们曾经的生命沧桑无关。
河水退去,留在古老河床上的是死亡,这个认识从一开始就被否定。正好相反,如果说河水带走了某些生命,那么它留下的,是更多的生命现象甚至生命奇迹。这可能与它的古老无关,但那些纷至沓来蓬勃的生命却附着在古老的躯体之上,展现的是此时和鲜艳。此时是古河床漫漫长途的一个环节,或者不重要的环节,而我恰巧到达这里,用自己所能把握的视觉和意识与之交汇,品尝了鲜艳的盛宴。
起初只生出水葒,单棵或几棵,怯弱又羞涩,慢慢长成了片,扬起了花穗,向四面颔首。后来,莎草、灯芯草等连片生长,牛筋草、棒头草、狼尾草等混迹其间,各种生命形态粉墨登场,密密麻麻占据河床,变成河滩草原。
种子的来源是个谜,只能惊异大自然的智慧。站立于淹没膝盖的草丛,我确信这智慧的存在却不知来自何处。河水才退去一个季节,它们便遮盖了河床,难道是为了隐藏某些古老的秘密?这里没有传说,难道是因为如德谟克利特所说“我们对现实一无所知,因为真理在一个深渊之中?”如果这里有传说,我们需要克服怎样的困难才能到达它?也罢,以我这等斗升小民,只能用感性逐渐接近梭罗切身的描述:“我看、闻、尝、听、摸与我们密切相连的永久的事物……宇宙那真实的辉煌。”
古河床真实的辉煌集中在柽柳身上。它们离开仅存的河水一段距离,或者说河水离开了它们一段距离。也许正是这段距离,它们才从古老的历史后面,来到了我面前。
蹲在它们中间,我像一只河蚌的壳,怀着饥渴,蹲在人类知识的字典里窥探自然的奥秘。头顶,深不见底的蓝天,白云飘荡。眼前,柽柳纤细高挑,白的粉的花束在沿河道流浪的风中摇晃。脚下,七千年前的沙子柔软如同新生儿的肌肤,向四周蔓延。柽柳扎根其中,楚楚动人,如远古女子的宣言,突然以花枝招展的形式,落满河床。
奇迹是,没有人栽种,它们却像被栽种过的一样,整齐地簇拥在一起,绵延数里,守护一份古老。
这条河叫潍河,从七千年前的远古流淌过来,流经高密大地,流经郑玄老先生的出生地砺埠山,流过现在。今天,由于难得的干旱,水位退缩,裸露出古老的河床,途径北甲庄、高家山甫、张家院、刘家沟等库区新村。我站在它古朴的脊背上,想象自古及今,有多少人也曾到过这里,看过一眼。
或许,用不了多久,几场大雨之后,河水将再一次淹没我走过的河床,淹没我遇见的一切,它呈现的生与死、存与亡,都将毫无界限也毫无痕迹地消失——如果可用消失界定——古河床退回它的原初,用沧海,用桑田,逐渐遗忘曾经在我眼前的闪现。
这闪现,即便我调动所有器官,也只能感知微小的一部分,更丰富的另一些,如风无形,难以捕捉,只能遗憾地对自己说:“我喜欢那些有形之物,正如喜欢人生苍茫;我喜欢那些无形之物,正如喜欢宁静无边。”
原载《山东工人报》2015年7月10日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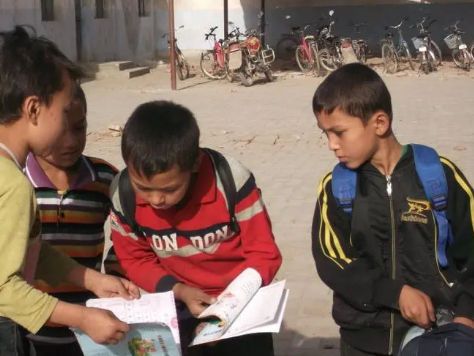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