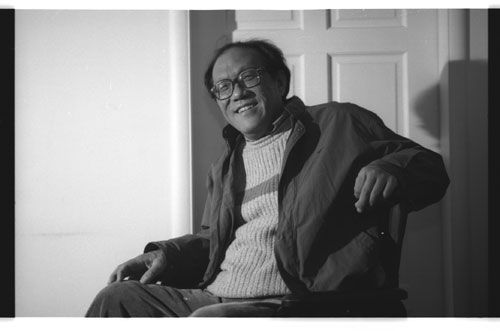十四 昨天
132
写N的父亲,他的记忆丢失了二十几年。写N的父亲和母亲的对话(重述前面写到过的。不同的只是前面到现在,二十几年的记忆不存在了,对于N的父亲,怎么可能的?怎么得以可能?失忆算不算精神阳痿?一旦出现的话,就永远下去,恢复不了,无法恢复?如果说,肉体阳痿还有蓝色药片可以得以拯救的话,我以前的前诗中,还为这个蓝色药片,我称为蓝哥,写过一个长诗,还可以,还鲜为人知。那么,有没有精神阳痿的蓝色药片?没有的话,怎么可以?有的话,在哪)。写到:“近期记忆丧失”还是“远期记忆丧失”(我想起来的是,选择性这个词语,比如,选择性地爱,选择性地恨,选择性执法,选择性记忆,选择性失忆。而失忆,失忆是选择性的吗?选择性意谓着主动性,有没有非主动性?这的非主动性并不是指被动性,被动性常常意谓着被迫性。而非主动性更多地和自愿的程度有关,它仍在自愿的状态或范畴。它只是比主动性弱了一点或隐蔽了一点。它只是另外一种主动性。我想说的是,这的二十几年指的是:1966到1976的所谓文革的十年,然后到1986的所谓新时期、新时代的前十年。这两个十年的转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巨大的什么?它不是分水岭,也不是人际代沟。我找不出比较恰当的一个概念或术语。在这个转换的时间段或空间,我想了好半天,想到的是防火墙,它推后了差不多又是两个十年,才出现。那个巨大的东西就是提前到来的意识形态的防火墙,它虽然是选择性的网络技术的新技术产生的新词语。它主要是为了保护软件,和用户的信息,防止黑客的进入,进行破坏、盗窃或恶意利用。它也在不断地更新,因为黑客的破解能力也在更新。这成了网络世界的两大力量,在进行竞争或较量。某种意义,这个竞争或较量也在推进网络世界的生态将长期性的处于暂时的阶段或发展的进程中,没有终结之日。可到了某些国家手里,这个技术又成了最新的国家统治工具之一,也就是建立局域网,以防火墙为隔离手段,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的通过和阻挡,公开和屏蔽。它是对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宗旨——自发的、自由的、快速的、共享的传播信息——的扭曲、背离和极大的嘲弄。其目的在于企图控制信息这个世界性的新资源,它具有颠覆性的反控制的新能力。而将这个功能用在那个转换的时刻,也是恰当无比的。它意谓着记忆这个东西的世界里也提前出现了如同防火墙这个东西,不管它来自国家记忆、社会记忆、个体记忆,它的作用都是选择性地,也就是自愿性地。而这个选择性的反面:选择性的遗忘,实际上是一个状态的东西。我说了好半天,或者说,对一个概念的定义及范畴进行了一次起码的追溯和语义分析。我想说的是N的父亲的失忆,仅仅是那两个十年的失忆,特别那个前十年,它究竟一种个别的现象,一个特例,还是普遍现象,一场传染性的精神病患?还有什么更好的说法?还想起来另外一个词语:穿越。它当然主要指的时空穿越,是人们对于宇宙世界的某种幻想性的探索,而人们又常常借用这个概念,在人世的历史间或人的精神世界、记忆世界进行穿越的尝试或无聊的游戏,像下跳棋似的,跳过某些格子,进入对自己有利的格子,那些不利的格子不存在一样,或者存在的话,仅仅为了利用它,然后忘到脑后,然后)。写到:F医生说:“近期记忆丧失”,越近的事情忘记得越快(没错)。“远期记忆”却保留,越远的事越记得清楚(没错)。
133
写对“昨天”和“过去”的语义分析。写WR也回来了。写WR和O见面(重逢啊)、写WR和O的对话。写我对WR和O说的昨天和过去的语义分析。写到:透明的高墙(这个短语好啊。它可能正是防火墙的同义词。这的透明指的仅仅只对建立和操纵的控制者来说,所有的网上信息,特别个人信息,是透明的,从而构成了对整体社会的全面监控,对个人世界的侵入或侵犯。它和史铁生写的透明还不完全一样。史铁生写的双向的,我说的单向的,区别就像玻璃和镜子:你照镜子时,你看得到的仅仅是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你却看不见镜子后面的那个,你意识都没有意识到。这有点像隔墙有耳一样,这非常可怕,非常恐怖,非常噩梦)。写到:互译的语言(这个短语好啊)。写到:抽象的会合,并没有具体地重逢(抽象的会合,这个短语好啊)。写到:他们握手告别。O含泪离开(我的暗流的眼泪啊哗哗哗哗地不打一处儿涌现过来,像我曾经站在深夜的海岸边所听到的那一阵一阵令人恐怖的漆黑无比的海面上传来的波浪声,仿佛从水下游过来的一个个将吞没我的巨型水怪。我从来没有在海岸边想到过美人鱼这个东西,听到过塞壬那样的歌声,不要说看到过了)。
134
写到:“这么些年,你都在哪儿?”“跟你的感觉一样,在这个世界之外。”(那么,谁又在之内?和之外的分界在哪)。写到:“或者,就在这个世界的隔壁。”“很像是在隔壁,”“但那是一道特别的墙,从那边能听见这边,在这边却听不见那边。不管我在那边怎么喊叫也是徒劳。”(这的描述指向的恰恰前面我预感到的防火墙的性质。我预感对了。史铁生预感对了。他提前预感对了。这个预感对了需要多么大的认识能力、知识能力、判断能力)。写WR的话,主要WR的。写得好得不得了,不,写的悲哀得不得了,不,是批判得不得了。写到:“我要当官!”。写到:权力。写到:民主。写到:还有什么自由哇平等啊法制呀,当它们都还是一个体操项目的时候它们不过是那么几个人获取金牌的机会。写到:政治(这一写政治的一段,说明WR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多么地清楚和强烈,思想观念秩序建立得是多么地早于或高于普遍低级的。这的低级没有歧视意味,它指的仅仅一种层次上的差异或人性论、认识论的差异。不,是史铁生的)。写到:“那么O呢?你真的不爱她了吗?”写到:“我很快就要结婚了。”“我需要她。”(爱是我需要她,是双方都认为。这里需要定义的是需要这个词语。史铁生没有定义。我也不定义了。我也定义不了。我仅仅站在信仰的基准上:爱和需要不一样。爱的范畴大于需要的。比需要更高。我认为。我信)
135
写到关于囚徒的故事(囚徒这个词好大,它好大得叫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会儿它的定义及范畴,也就是问一问,什么叫做囚徒,什么不叫做,囚徒和囚徒一样不一样,和非囚徒有没有界线,这是我学会已经应用的方法论,也是我学会已经建立的问题意识。这当然正是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近代欧洲人、现代欧美人建立哲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雄辩的方法论,涌现出耀眼的一颗颗认识论的星辰、一座座巍峨的知识论的山峰,促进着人类的智力不断发达,社会不断地繁荣。其它种族的、特别东方的、汉族的则缺乏这个基因或精血。当然我也缺乏,以至于无意也无力也无那个耐性去逻辑性的、去唯理的、去经验的、去综合性的、去辨析这个概念的涵义、定义它的范畴,建立囚徒学,像涂尔干那样,建立自杀学。是啊是啊,连自杀的出现和增加的现象都引得起来兴趣,建立得起来专论嘛。我只是看到这里,史铁生刻意插入的一小节,只是听说过、听人说起过、听说过,叙述得也无不望而生畏、恐怖至极、产生怜悯,叫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大约两类,一类国家机器的受控者,一类人的欲望的。也就是说,要么国家机器的囚徒,要么人的欲望的。比这个大约进一步的:人首先成为人的欲望的囚徒,还是首先成为国家机器的?成为国家机器的囚徒的时间比成为人的欲望的要长得长得长,还是相反?我思考的也就这个,没有更多的,没有进行过社会学意义的田野调查,收集出大量的证据或史料,作为研究对象。还有,我想起来的是:死屋手记,好久没有读过了。这里有个体会,就是,读哪方面的,不读哪方面的?其次,必须读哪方面的,不必须哪方面的?其次,重读哪些,不重读哪些?因为人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读得完想读的。人的智力有限,不可能只读人的。应当进行选择,是的是的,又是选择性地行为:读谁的,不读谁的?最终是,多读神的,少读人的。还有,我想起来的是:古拉格群岛,其实想到的是我交到过的前面提到过的可能交到过的下下的一个,表面上也热衷知识——狭隘得后来发现吃惊、热衷阅读——大众化得后来发现吃惊、热衷写作——肤浅得或装萌得后来发现吃惊。我可能过于苛刻了,接近于求全责备的边界,或改变他人的法西斯主义的企图。我必须警惕这个泛滥下去,我不能让他人成为我的囚徒。对,囚徒的第三个分类:成为他人的囚徒,或让他人成为自己的。我想说的是有一天,我自言自语,仿佛自言自语,我说,我想看看古拉格群岛,还有加缪全集,卖得太贵了。我说,算了,以后吧,反正不是天大的。她当时没有反应,没有说话。那时候,我去了广州,她请求我去,和她同居。我去了,和她过着同居的生活。没有过两天,快递到了,打开一看,新新的古拉格群岛和加缪全集。我格外意外,格外惊讶,这不是我买的,不是我的。那一天一大早,她出门了,说要去见一个姓黄的什么大诗人,谈一件什么合作的事,揽一部分什么写文案的活儿,挣一点外块。她走之前,主动地刚刚又做了一把,才出门。主动地又做了一把,当然不是问题,不算疲劳。我只是不想起床,又睡了一会儿,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我好像还做了梦,没有做完,电话进来了:下来收快递,快递说。我说,谁的?快递说,面海的,你不是面海吗?你是不是面海?我说,我是,马上下来。那一天她好晚好晚才回来,好像不是好兴奋。你的快递到了,我说。我说的可能也许,你的书到了。也可能,你又买书了?我说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她说,是我买给你的,没有想到对吗?我说,没有。我没有的还有,她这时显得兴奋起来,我也兴奋起来。两个这样的兴奋后,她又拉我上了她的那张她和前男友上过不晓得多少回的并不宽裕的床铺,又做了一把比较全面的,一会儿要前面做,一会儿要后面做,一会儿要下面做,一会儿要上面做。她痴迷的或成了习惯的是,她在上面做,不然就达不到。我呢,我又痴迷的或成了习惯的是最后,不口交的话,就不射出来。当然一谈这个,人们总是不亦乐乎,兴致勃勃。这的兴致勃勃,有的人写成了已经性致勃勃。这的人们包括她和女人们,我和男人们,她和男人们,我和女人们。其实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个,也就是那套多卷的古拉格群岛,才看了没有多少,有一天她又出门了,我才偶然发现扉页,写了几行字,写的什么我忘了,落款没有忘,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于广州网购,然后写的是她的姓名,又写到:藏书。我又翻了一眼加缪,也是。这个后来写的,显然为了表明归属:主人是谁,或者说,其所有权。我的感觉不对了,或者说,我有偏见。我的心胸不够。我从那一刻起,就没有去碰过了。我不喜欢去读属于他人的书本,在我的眼里,它属于私人用品,未经允许,不得使用。就算允许的话,也不能随随便便地乱写乱画。唉,又说多了,特别是这个一想起来不愉悦的。悖论:越是不愉悦的印象越深刻,越是愉悦的印象越淡漠。
136
写到:一个从政者他是谁?一个立志从政的人他是谁?诸多从政者中的一个,他要使所有的人都不再被送到世界的隔壁去,那么,他就像是谁呢?(这个天问啊,这个种族啊,从来只有从政者,热衷于从政,没有政治家,没有政治学,一个也没有过。活该嘛,活该)。
十五 小街
137
写女教师O和WR分了手,现在画家Z离O更近了:只有上帝看得见,由于WR与O的分手,在O走向Z的几十年的命途上,最后一道阻碍已经打通。写到上帝:上帝从来是喜欢玩花样儿的,这是生命的要点,是生活全部魅力之根据,你的惊奇、不解,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执迷和所谓彻悟,全系于上帝的这种爱好(我想起来的是爱因斯坦说的,他说:The God does not play the game which throw the dice.上帝不玩这个掷骰子的游戏。爱因斯坦可能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对了:上帝照着祂的意思——话语,直接创世,不需要掷骰子。上帝不会给自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不对:上帝在一直给受造物们掷骰子,叫他们永远未知或不确定)。写到:生命只有一次,上帝不喜欢假设(这的生命指的肉体。假设也应当在本体论上来理解,才对。而认识论上,假设指的在先验的公理上,恰恰是必要的展开思辨或论证的方法论。这就好像说一个人太坏了,指的人性论,说一个人太蠢了,指的认识论,说一个人又坏又蠢还是又蠢又坏,指的逻辑。史铁生在这说的不是这些,而指的是人们无中生有的习惯,和命运无常时的事后判断,和人际关系或男女关系出现障碍时将责任推诿到他人的那边从而给自己开脱的托词,当然他人不喜欢,不用说上帝了)。
138
写Z生来渴望高贵和美丽(这的渴望就是一种假设的另外一种表达。还有,高贵和美丽这样的词语完全是外来的,不在汉语的词典里,不属于这个种族的东西,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人的高贵,叫做人的美丽,或者说,叫做高贵的人,美丽的人)。
139
写(Z的)母亲的本意是改嫁一个普通工人。写他除了是一个工人还是一个戏迷加酒鬼、二胡拉得漂亮以及嗜酒如命。写小街:Z的继父从生到死都在那儿。写曾经的小街光景(多好的光景啊,那大明到大清到民末的若干百年的积累或遗留的社会秩序啊,起码,可1949后,倒成了取缔的对象,多大的野蛮,多大的罪啊,多反人类。可能这正是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重现)。写Z的异父母姐姐M:M是个早熟的女孩儿。
140
写Z的心里,从未承认过那是自己的家(本来就不是嘛,我就奇了怪了现在,绵绵不绝的这个种族的男男女女们特别男们,过球了一个千年两个千年三四个了,什么叫做父母家,叫做自己的家,没有从来分清过。父母的是父母的,自己的去建嘛,和父母的有个锤子的关系)。写Z开始恨母亲,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儿来?母亲怎么会愿意和那样一个丑陋庸俗的人一起生活呢(这个大爷的熊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懂个锤子)。
141
写Z倒是喜欢M。写Z的继父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里当花匠(这个继父越来越不普通了)。写少年Z常常坐在花前藤下画画。写M只要有空,总会走来站在一旁惊讶地看着Z画画,大气不敢出。写M便拿了弟弟的图画到处去宣扬、展示,骄傲地收获着众人的赞叹。写M转身对继母说:“家里的活儿都让我来干吧,让弟弟好好画他的画。”(女孩子比男孩子懂得早得早嘛,男孩子不懂,到了老都老了,也不懂,就好像男人们就是永远不懂的那种,不承认不行的)。
142
写M去街上拎(水)。写姐弟俩抬水(我想起来的是我小时候也是自来水还是公用的,没有通到家家户户,家里只有水缸,好大的缸啊。我大约长到六七岁,和大我两岁的姐姐去抬水,有时候又叫去挑水,区别在于,两个人去叫抬水,一个人去叫挑水。一开始抬一桶,好大的桶啊,我在前面,姐姐后面,水桶在中间的扁担上。姐姐把桶拉近她的那边,怕我抬不动了,她一个人怎么办呀?后来姐姐长到已经可以去一个人去挑了,后来我也长到已经可以一个人去挑了。特别是冬天,路上结了冰,不小心又滑倒了,满满的两个桶嗵嗵地两声倒在地上,水哗哗地泼在那儿,一会儿又结成了冰,好厉害嘛,冰可以把桶冻在地上,连棉衣、棉裤、棉鞋、棉手套,连棉帽,那才叫一个惨兮兮嘛。没有什么办法,还得爬起来,还得回去,回到公用的自来水那儿,那儿的冰其实更大、更滑人。还有水缸,冬天的时候不能太满了,太满的话,到了三九天气,一夜间也结了冰,可能会裂开。我爸我妈他们说到过,要是裂了,那就没有存水的了。他们没有说到原因,他们知道不知道,就算不知道,他们就是知道这个危险。而我们知道的话,那要等到我和我姐上到初中。那还是几年后的事儿,还要等待。那时候我弟弟才几岁啊,他懂个锤子嘛。他什么都不知道,活儿都不叫他干,都不用他,就是他都老大不小了,还是不知道,知道个锤子嘛。他还不承认,大人惯着他,姐姐哥哥为他付出过。你说说看,拿他什么办法嘛)。写M差不多已经长成了女人。长起了修长秀美的身材。流溢着的诱惑。写不料这样的欲念也在M亲生父亲的心里生出,且难以疏浚(好陌生,查了下,工程术语,疏通、疏散阻塞,开挖、清理)。写M洗澡时生父偷看。然后Z看见:茁壮鲜活的女人的裸体:“姐姐你快穿上,我去杀了他!”写Z喜欢M,对M有着强烈欲望。
143
写M和Z的对话(多好的M嘛。我担忧的以后,怎么写以后)。
144
写不久,M去插队了(对,又叫插队。这个比上山下乡,比知识青年,比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准确得多,形象得多。它引得起人们对插的联想。它表面上是知识青年的青葱岁月插入了农村的农民生活中,实际上是农村的农民生活插入了知识青年的青葱岁月。特别是好多的大大小小的农村干部们的脏手和脏鸡巴插入了好多的女知青的肉体。这个不是瞎说的,造谣的,而是好多好多年后才公开的内部控制的消息)。写M和十几个男女青年领了潮流之先,成为知识青年的榜样(M们的嗅觉不可小看啊,这意味以后的人生轨迹的悬念)。写Z的异父同母的弟弟HJ已经十三岁。
写T(一个一直若隐若现的人物)。写HJ十八岁,给T写了第一封情书。写HJ成了厨师。写少女T爱上了谁呢?写她的独特选择是:为了能出国,就嫁给HJ吧(出国这个热词出现了。这时候到了应当上世纪末或新世纪初,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经历了两个十年,又是两个十年,一部分人也真的先富起来,可以说是富得钵满盆满,富得金山银海,富可敌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存的权贵阶层。这个极大的具有欺骗性的手段隐含着让一部分人先出国、先移民、先转移资金的谋略。这么阴险的谋略却蒙蔽了广大眼睛,受到广泛赞誉。这个越来越浮出水面的冰山已经不是新闻了。多么大的嘲讽嘛。而不管T属不属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权贵阶层的一部分,T又领了潮流之先,像M一样)。
146
写HJ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再不断地(七个不断地,为了追T)。写Z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四个,为了阻止HJ):“你要想让她爱你,你就得让她仰望你崇拜你……”写到“高干”:T的父母都是高干。
147
写到牧师。留学。HJ非常兴奋,“妈,你说我去哪儿?”(前面就想说,Z的继父,也就是M的生父,是个酒鬼,是个偷看者,是个花匠,是个戏迷,二胡拉得漂亮,全才嘛,还不仅仅,还做过更大的善事:救过牧师,天大的德嘛,回报是牧师留下遗嘱,恩典啊)
148
写HJ与T终成眷属。写HJ说:“不爱而被爱,和爱而不被爱,我宁愿要后者。”(HJ的层次比T的高得高得高点儿)。写HJ出了国,继而T也出了国。T的母亲也出国。这时候T的父亲和HJ的父亲也就是Z的继父M的生父那个全才成了晚年的知己。他们对故土的留恋好像比女人们多得多得多点儿。
149
写如果(主要是几个男人们的混淆)。
面海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