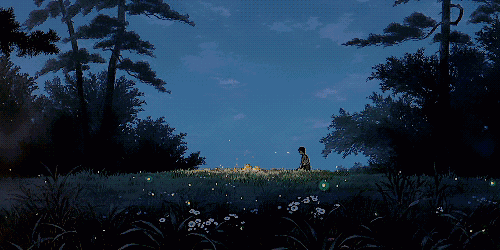“喂!”他顺便瞄一眼墙上的挂钟;表上的时针、分针,恰巧耷拉在6点半的位置上。他猜测电话那头大约是早晨的七点多钟。他对着话筒说:“老婆,情人节愉快!”
那边打了个哈欠。听声音似是哈欠连连,没睡足的样子。
“刚回来?”
“刚刚进门呢。”
“为什么不主动慰问我一下?”
“老惯例了。”他说,“这不,你往这儿打便宜嘛。”
“今天可以破例。”
“我是这样想的,”他对着屋内正不知怎么下手的女人朝厨房指指——意思是你慢慢忙吧。回头对话筒说,“这不是你先打进来了嘛。”
“吻一下。”
他对着话筒打了个啵。
“上年情人节你是在我家过的。但你回去的很早。”
“是啊。”他说,“今年,今年……这不……不方便了嘛。”
“我妈怎么样?”
“挺好……”他说,“我昨天还买东西去看过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似有点难过的样子。她说:“你要去多看看我妈。”
他对着电话点头道:“知道。”
“我爸有消息吗?”
“双……”这个词他拿捏不住了。他说,“这期间,只能是落实。大概没什么大不了的。多少人为人从政比你爸差多了。”
这次,他听出话筒里的声音有点哽咽,他劝慰道:“别,别难过。也或许是别人眼红诬陷的呢。”
“别,别……噢……哈里……哈里!”
“你在干嘛?”他耳朵竖起来了,“你在叫谁呢?”
“没事儿……”电话那头似是有拍打皮肤的响声。接着似是又啜泣了两下。那边又凑近了话筒。“涛!……我只是挺难过。想到我爸妈。……真是……想到我爸妈为了我……为了我做了那么多。此时……我也帮不了他们。而且一点也帮不了他们。……我真的很难过。”
“是,是啊!”这男人说,“我也是。”
那边抽抽嗒嗒的哭出声了。
“好了。别哭了。”他说,“你要是哭坏了,这不是更对不起爸妈了。”他强调着,“你是爸妈的希望。”
她喃喃道:“希望有什么用?”
“好了。”他说,“他们俩口子还指望你活得更好,还指望你带他们出国旅游来。”
“可……”话筒里面擤一把鼻涕。“可我在这儿也混得好不到哪去!”
“这……”他抻头瞅一眼厨房。“当然,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那边沉默着。
“学业怎样?”他又缀上句,“能应付吧?”
“差不多。”
“经济上应该问题不大?”
“这……倒没什么。哦……”她说,“我忘了跟你说,我养了一条狗呢。”说到狗那面好像抹一把脸心情好起来了。“这狗一身黄毛,腿特长,特通人性呢。”
“哦……”
“哈里!”话筒里面说,“叫叫。”
可话筒里没传出狗叫的声音。也没传出特有的口条哼哧哼哧抽嗒的喉音。他瞎猜测着说:“洋鬼子也一身黄毛呢。”
那边笑了。声音爽爽的,似乎是一扫阴郁并打开了窗。
他担心她说起狗又来了说话的兴致。他说:“老婆!”他现在实在是想挂电话了。“老婆……我先做点吃的。半小时,半小时我打给你好吗?”
那边倒是干脆,啪嗒一声,电话挂了。
于是,他放下电话,搓着手,一头扎进厨房。
厨房里的女人此时才打开了水龙冲洗着摘好、剥好的菜、鱼、姜还有葱花等。他先是在女人的脖颈上亲吻着。那女人躲避着戏痒,对他接下来伸过来的嘴唇回应了两下,似乎也释然并绽开了微笑。
“别的我做,鱼你做。”那女人说,“我对你好吧。你接电话时,我都替你悄悄收拾好了。”
他又轻啄一下她的嘴唇,人也畅快地撒了欢,仿佛一扫佯装的重负,手脚不勤快的干点什么就不得劲了。
“ 我来做饭。”他提议,“你去布置好桌子并点好蜡烛。”
女人笑了。“这可是你说的。”她说着冲冲手,一边回答着,“忙完了,我要去冲个澡。”一边摔着湿漉漉的手掌走进客厅。
他开始在厨房内忙活着。
他听懂了这种暗示。炒着菜的工夫,他瞅一眼从厨房可以看到客厅墙上的挂表——那钟表和他两腿中间的物件似是有了某钟契合或回应;时针和分针悄悄地跑到七点二十的位置上。他开始热锅,倒上油,葱花、盐,油菜和香菇,舞动了铲子。他本想多炒几个菜,唤醒一下已经挺丰富的胃口。但身体的质感知道只是为了那种事儿的点缀,实属瞎掰。便把菜只炒了两个。他甚至把准备煎牛排的生牛排也扔进了冰箱,只煮了新鲜的虾、海螺和蛤蜊,然后闷上锅只等着开锅做最后一道讲究火候的清蒸鱼了。
他将鲳鱼的鱼身勒几道能揉进滋味的口子。把生抽、料酒、白糖、葱花和生姜、大蒜,肉片洒在鱼身上。水一开,他把蒸鱼的盘子放进了蒸锅。这时,客厅的灯光突然暗了。他看到这个女人像条鱼儿披一头尚未擦干的头发半裸着点燃着蜡烛。桌上的蜡烛渐渐把鱼身映红,并跳闪着火苗,身子像熟透了一样,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屁股。嚯嚯!……他感到两腿中的物件也如火苗般悄悄跳闪着。
他干脆说:“先吃吧?”说着便把做熟的菜、虾、海螺和蛤蜊端上了桌子。他们正儿八经坐下来的时候,这边已经倒上了红酒。他们碰杯。
“为情人节!”
“为今晚。”
“为很多事能如愿顺利吧!”
他听着也是。有什么事儿能比如愿和顺利能好呢?他干掉了这杯红酒。草草地吃了几口,或者可以说他们双方也就捣了几筷子。回头,再临去厨房上最后一道鱼之前,他叮嘱着这个身上跳动着火光的女人说:“你也要干杯!”
女人说:“你去吧。”她转悠着手中的玻璃杯,眼睛让烛光撩动的发亮。“……你回来之前,我干掉这杯。”
他回身将锅里闷好的鱼端上桌子,然后说:“你喜欢的蔬菜色拉,我们宵夜再吃。”
这次——坐下来以后——他不想正儿八经吃饭了。他端着酒杯站起。
女人说:“你想干嘛?”女人说着用屁股后推着椅子。“吃完饭嘛!”
“先吃点汤料嘛!”他走到身子已站直的女人身边。“我没法等到吃完饭了。”
于是他们开始接吻,然后他把红酒滴落在女人的乳房上开始吮吸。待女人的呼吸变得急促,甚至身子酥软了。这当儿客厅的电话又叮铃铃地响起来了。
这一刻,他两腿之间也掉到了抬头间指针所显现的八点三十五的位置上。
他们彼此都沉默晦气。
“你不说是半小时给我电话吗?”
“当然,”他看着自己已熨平下来的裤裆。“没事儿,我只是自己想喝点酒呢。”
“你没事吧?”
他望着窗外。他现在不想也不忍心看女人的面色和身体了。窗外的月亮挂在树梢不上不下的,一些住宅和酒店的房子早早也亮起了灯光。他说:“ 我能有什么事啊!”
“听声音好像不太高兴似的.。”
“没什么。”他说,“真的,没什么不高兴的。”
“不过,说真的,你不高兴我也理解。”
“算了吧,一听你就在装样。”这会儿,他的余光看见房间的女人已经披上件上衣。“你能理解我什么?”他问着。
“我正想问你呢?”电话那头传出一两声轻轻地啄吻声。
他敛声屏气地问:“你问我什么?”
里面又传出拍打或推搡的悄悄声。那边清清嗓子道:“这两年……我不在家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开始烦了。“你说,我是怎么过来的?”
“你能没有点事儿?”
“哼!”他齿冷甚至嘲笑自己,“我能有什么事儿。”
“性事。”她说,“性的问题怎么解决?”
“唉……”他叹口气说,“这事儿,你问过八百五十遍了。”他又问,“你还在床上?”
“你别答非所问。”
“你就想找茬?”
“还有二十分钟。我就想听听这个。”
“好吧!”他说,“我先去倒杯酒。”
他放下电话,抻抻脖子,跑到坐在餐桌前背对着自己的女人。那女人正无聊地吸着烟,桌上的烛光把尖翘的鼻子晃动的忽明忽暗。他从身后亲吻着女人的脖颈和嘴唇,然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对不起。”他说,“很快,”接着又趴在耳边强调着,“很快就完了。”
这期间——也就这么短暂的叹口气的工夫,他豁然醒悟:他与女人亲吻所发出的声音和与老婆在电话里所发出的声音不二,或基本相仿。这令他因顿悟而羞愤了。他甚至想起她叫着“哈里”的那条狗,不知不觉由其一股羞辱又羞愤的隐痛。当然,这隐痛仅持续了几秒因身边还晃悠着一个让他平衡的东西,这倒也令他自负且释然了。于是,她从后面抱起了女人,转过身,让光脚的女人脚踩在他拖鞋的鞋面,然后俩人一人端一杯酒轻轻地挪回到话机跟前。
他按下了话机的免提键。“喂!”他说。一面抿一口酒把嘴凑到女人嘴上互换着酒,一面嘟嘟囔囔着说,“我给你读一段我写的诗吧?”
“不,我不要听。”
“不算是诗,算是心灵日记。”他说着,也不管她愿不愿听,一面用遥控器开启了音响,一面与女人在客厅里悠悠荡荡的跳起来……
我把黄昏钓上来的时候
朝阳走了
我用皮肤 眼袋兜进了时间和爱情
时间只追逐活着的东西
——爱和偷情 错误与觉醒
也是二月十四日
这一天
光阴即将被缝合的时候
大海有了豁口
土地张开了喉咙
于是
我要做不明生死的远行
……
蚂蚱眼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