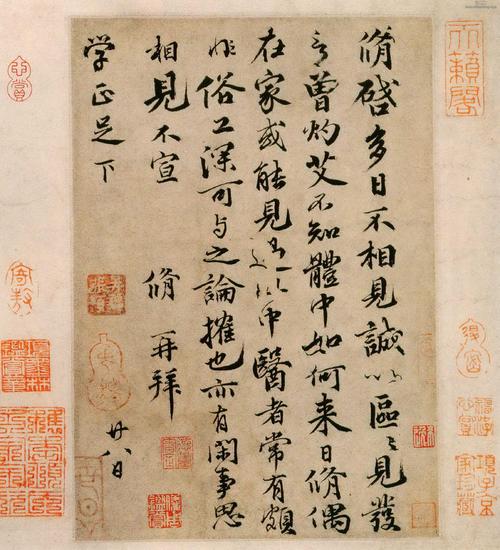天,炽热的时候,人烦躁,上火,也容易懒惰,草木也是。这时候我企盼的就是下雨。
几天前同事说:这两天有雨,而且据广播说,是大暴雨。我听后没怎么表示,但毕竟是暗喜了。
晚上,酒后,回家。迷糊中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变成一只肥胖的蜘蛛。这蜘蛛的颜色是黑褐色的。
这肥胖的蜘蛛织出了网,象网络一样,联接在两颗树梢与树枝之间。树是果树,一棵是杏树,一棵是无花果树。
我倦怠在蜘蛛网的一角,几月无雨,阳光烧烤了熔岩、沙砾、草木,又被夜间的微风卷扬,一些附灰沉落,黏附在蜘蛛网上。这蜘蛛网就是我生命的吊床,它凌乱不堪,又污浊不堪;它甚至让苍蝇、蚊子、蟋蟀和其它爬行的物种也能看见。
一天,是一个临近傍晚的白天。阳光在瞌睡的时候我正在迷糊中苏醒,陡然间一阵微风令我身子发晃,树叶把树枝也拐带着摇曳曼舞,也没有雷电打声招呼;雨穿透枝叶,用雨点击打在蜘蛛网上,终于下起来了!
仿佛就是一种久违,见着了,碰到了,淋到了。我像嗷嗷待哺的小鸟,贪婪在这种爽人肺腑,享受在这股淋漓地酣畅里。
渐渐地,通过游走,我知道吊床被雨洗得晶莹、透亮。一些水珠盈盈闪闪,一排排的,映射出我一路爬行的影子。我开始吐丝,攀爬,像编织梦境一样,绘制我的理想,恣情我的渴望。
我从杏树又移到了无花果树上,仿佛没有了疆域又拓展了疆域。我在回头看自己的吊床,发现这吊床又拓展成有棱有角的地图。这地图是自由世界巢穴的模样,有东西海岸,粗看上去平安有序,像自由的家园。一只绿头苍蝇捏一本绿色的护照撞到了网上。它起先是骄横,嚣张,甚至狂妄,但翅膀仅扇动了几下,一种理性认识到的逃脱无望让他臣服了。它开始诉求,又开始乞求;甚至坦露背景,暗示另外一种利诱和允诺。
我无语,甚至无视。我只是默默地抬起螯肢,把螯牙伸进它的体内,像打蛋器打蛋一样,搅合了一番,把它吸成个躯壳,然后遗弃在我的吊床。
我吸干一只苍蝇,又吞噬几只蚊子。这时,黑夜已薄溜溜地挂在了天上。我在吊床上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这点食物只打打牙祭,饥饿像干瘪的树干仍时时袭来。此时,树叶在擦拭一些窗户上的灯光,其中一个像早晨和傍晚太阳一样的颜色。几个大大的影子在里面晃动着。这些影子一会儿变大,移动,一会儿又缩小停滞在一张我似乎是床和沙发的东西。由于视力所至,我开始后悔在变成蜘蛛以前,我没把眼镜也捎带过来。于是我只能尽视力与身躯只所能,瞪大着眼珠看着。但我听力很好。
“差不多了,”那男的说,“你瞎磨蹭什么?”
这男人的嗓音却让我熟悉,我只是跟提笔忘字一样,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说,”那女的回头,从镜子前移开,屋内的人影已变成两个。“我想和你谈谈。”
“又来了。谈什么?”
“我不想跟你这么下去了。”
“我说过。你要给我时间。”
“你认为给的还少吗?”
他好像坐起来说:“签证还没下来呢。”
“亲爱的!”那女人走到窗前,“不是我催你。”她叹着气说,“我认为我等不及了。”
“有什么问题吗?”男人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剑刚!”
听女人称呼:剑刚。我对上号了。我身子不由得前倾,屁股也抬了起来。
“我曾经有过理想。”女人说着,贴近窗户的脸又背过身,一席长发披在背上。“你也曾给过我理想。可是,生活到这个接骨眼上,我真憋不住了。我想跟你坦白。我又爱上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是谁?”
“这人你可能认识。他所能给我的正是你给不了的。我们相处不长,但他赋予我阳光和激情。你知道,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智商和能力却超群的人,他所能带来的是什么?
“他有使不完的能力,对生活又没有退缩。他的家人和家境也十分友善和富裕吧!他爸妈很喜欢我。”
“不会是他爸妈我也认识吧?”剑刚注意到她缺乏底气所说的富裕,但他还是忍不住落寞地想问,“你们上床了?”
“无论怎么说,我毕竟未婚,没有过婚史。我不受束缚,也敢爱敢恨。”她没回答他,仿佛在刺激他,“我父亲曾经说:‘男人,千万不能用爱给惯坏了。男人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现在想想,我爸真可怜!我爸一辈子只有我妈这么一个女人。你呢?”她离开了窗户,“不用我说,你有无数个女人。尽管你哪圈朋友里面你还算是好的,不错的。像杜帝,瘦人,姓台的,和与一座破山同名的,还有那个跟老太太姓氏差不多的……我数了数,也就姓马的那人还挺好。尽管嘴巴上胡说,胡咧咧,但那人面相一看,就是忠厚,老实。我记得那次喝酒跳舞的时候,我还故意用胸蹭他几下——这,当然这是挑逗了。但那姓马的可真老实啊!自始始终,没一点歪歪的举动。尽管后来我听说,这人喜欢男的,属同志。”
“好了。”剑刚摆摆手说,“你那会看人。哪姓马的才不是个东西呢。”
(吃饭。)
蚂蚱眼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