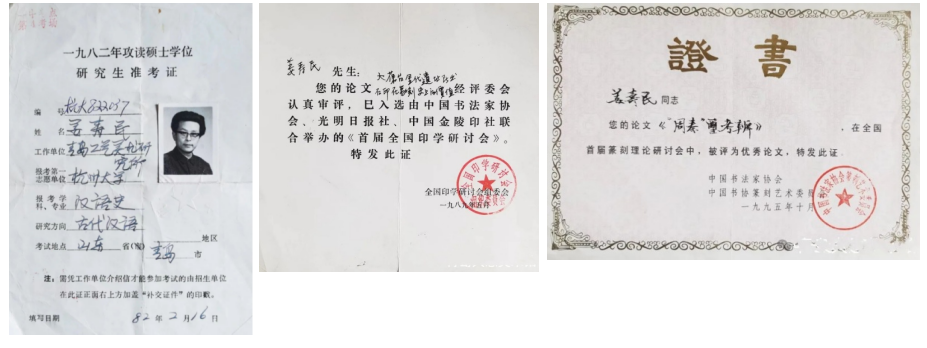解老是济南人。退休前是山东出版集团东方图书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再往前,他是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印刷厂(原青岛师专印刷厂)业务副厂长,再往前,他在山东海洋科学仪器仪表研究所(就在著名的天主教堂下)工作。
解老是个性情和蔼的老头儿。他个子不高,脸上总是堆着笑眯眯的神情,认识他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见过他对谁发过脾气。
解老是业务能手,无论在退休前的单位,还是在原单位,论印刷业务那是大拿。也是单位的台柱子。他也熟悉省内大部分的印刷厂。
我跟解老认识是我在团青岛市委做机关刊物编辑期间。那天,在太平路37号大楼五楼办公室,我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当时,不知道谁介绍他到我这里来,那时印刷厂业务不好,吃不饱,学校有意想把厂子转让出去,好像开价是5万元。跟领导接触后,大概领导没有想到此后印刷行业的火暴,没有答应。但是,从此以后我跟解老成了好朋友。实际上,当时解老已是人到中年,而我还是刚刚迈出学校门的毛头小伙儿,对于印刷业务几乎一窍不通。正因为有解老这样的依靠,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要涉及到印刷品报价,我一律直接打电话找解老,觉得是个现成的参谋,自己不必劳神去学。甚至直到前不久,大约四个多月之前,在筹备这份杂志之前,我还到他家去过,就有关印刷成本向老先生请教。解老当时刚刚大病初愈。据他说,前年他差点挺不过来了,为了抢救,花费了十来万元。那天,他带我到他家附近的一家酒店,请我吃饭,叙旧,真的是感慨不已。没有想到,仅仅四个月的时间,他就告别了他的家人,朋友,自己心爱的事业……
记得在团市委工作期间,不管我做机关刊物的编辑,到他们厂子送稿子,看校样,还是去印会议材料,也不管文件的数量有多么少,他都不厌其烦躁地给我核价、计算成本,要是在他那里不合适,他总是耐心地拉着我到各家印刷厂去询价,直到我满意为止。从1985年开始,团市委开始编纂《青岛青年年鉴》,这类书的特点是字数多,印数少,四五十万字的书往往只要1000册,印多了没有用啊。市内的印刷厂不给印,他就带我去黄县印刷厂,或是昌邑印刷厂等县级小厂——那些厂子像欢迎财神一样迎接解老,因为解老不仅给他们带去像我们的书这样的鸡肋,还能带去教材或辅助读物,那可是大买卖,甚至还有西藏寺院的经文——僧侣常常是带一大旅行包,里面全是现金。到那里以后,厂长热情地招待解老和我。解老有事先走以后,我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每天中午厂长都安排客饭,像尊神一样招待我,弄得我这个小青年很不自在:顿顿有酒,餐餐有肉有鱼。连续三年的年鉴在黄县印,青岛到黄县往返要440公里,印一种书我就要往返跑差不多10次。那时我吸烟,而且抽雪茄,我一上车,满车的人都提抗议,解老也劝我不要吸烟这样凶。在他的劝戒下,后来我终于在1997年1月1日戒烟,至今未抽一口,真的很感谢他啊!
近日,为编一本书,想了解一下有关印刷成本的事情,顺手就拨了解宏的电话,刚拨完号码,忽然想到:解老已不在了!赶紧扣下了话机。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时请教解老了!
解老!一想来,就难过的好朋友!
窗外又刮起了寒风,耳机里响彻着回肠荡气的《海阔天空》《渔火闪闪》等名曲,心里不禁又想起了与解老交往的往事。
那也是一个春天。我受命编写上一年度的《青岛青年年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熬,最终完成了五六十万字的书稿。这时又为印刷发愁了:只有区区一千册,哪个厂子能承印呢!于是顺手拨通了解老的电话。很快,解老带领我踏上了前往昌邑一个小厂的旅途。好在这些厂的位置距离青岛都不远。这次是昌乐县印刷厂。紧靠潍坊市不远,于是就有机会去观赏一年一度的潍坊风筝节。
安排好了印刷业务。解老带着我,跟随印刷厂安排的一辆130客货两用车,一早就从县城出发,赶往风筝节的主会场——潍坊市,不用说,跟中国所有的大型节会一样,照例是礼花,文艺演出,喧嚣,进场前人山人海,散场后也是人山人海。记不得车子在潍坊市转了多少圈子,印象中潍坊只是个小城,怎么走了那么长的时间,恍惚中好像走了一整夜。
进潍坊城之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车龙,从车牌号看,几乎都是外省的车辆。初春的潍北平原,风是暖的,刮起阵阵尘土,远处,在宽阔的北海边上,是放飞巨型风筝的场地。
车子在慢腾腾地挪动,解老提议,车子拐个弯,顺路到潍北农场去看看他的老同学。
车子暂时离开了慢腾腾的车龙,沿着一条颠簸弯曲的小路,大概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建筑前,近旁,好像有哨兵站岗。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解老神秘地一笑: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进一排平房前停下了。车停了,四周立即沉静下来了,静得可怕,呼吸声能听到,风停了,空气里弥漫着死一般的气息。少顷,一间平房里跑出一位身着警服的老者,斑白的发迹从戴得不正规的大檐帽下凌乱地冒出来,警服的风纪扣也敞着。他慌张地迎了出来,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憨厚的笑容,解老也快步迎上前去,他俩握手、拥抱,边招呼我和车上的其他几位进去坐坐。
解老介绍说,这位就是他要来看望的老同学,他在这里干了三十多年了,这里是著名的潍北农场,即劳改农场,其实就是一座大型监狱,被判刑的人在这里劳动改造。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青纱帐、芦苇荡,就是阻碍被监禁者逃逸的天堑。
老哥俩品茶,叙旧,一肚子说不完的话。环顾四壁,空荡荡的,屋内只有不多的几件简单家具:单人床,写字台,台灯,水缸,马扎子,脚下是农村常见的坑洼不平的土地,喝完茶根,往地下一倒,眨眼就渗到地下了。
分别的时候到了。老警察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嘴巴翕动着,嗫喏地,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再看解老,眼眶也是红的,当时对这种老年人的分别似乎感到不可思议。直到自己也离中老年越来越近,才开始体会这种情感。
车子发动了,远远地,老警察还站在原地,呆呆的,直到开出去很远,还隐约能见到天际有一个黑点……
2006-02-18 2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