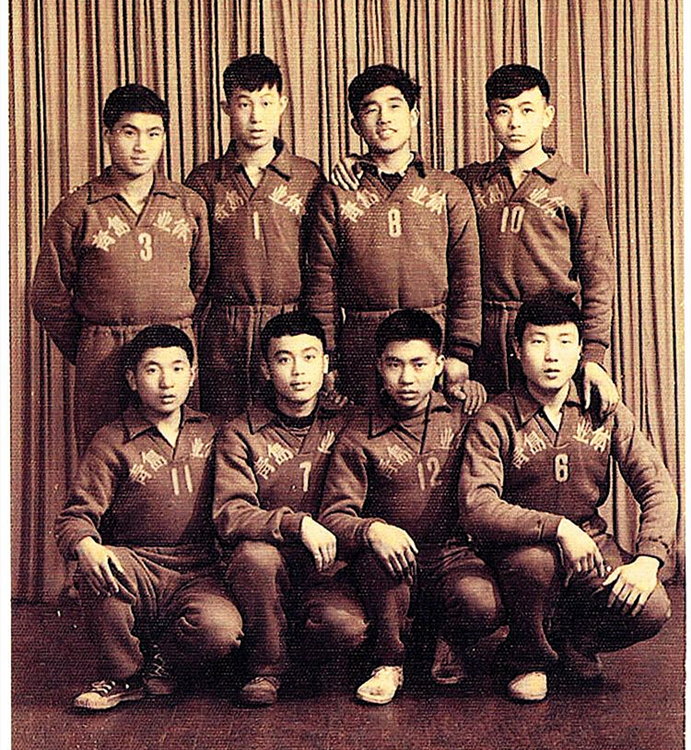民以食为天,有关于“吃”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碌碌红尘中的你我周遭上演。有道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大部分穷僻的乡村来说,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讲究养生,都是能有东西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下面我就将那个年代身边亲人的几则跟吃有关的小故事分享给读者。
妈妈的故事
两个肉包子
有一次下午妈妈担上蔬菜返程的时候,曾外婆从集镇上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塞在她手里。妈妈曾有一次跟外婆赶集远远地见到过肉包子,但肉包子那柔软而温热的体温被触摸在手里还是头一次。那令人垂涎的香味令她深深吸了口气,一瞬间妈妈觉得再也没有比那个下午阳光更明媚温馨的时刻了。
可是曾外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像给她心里吹进了一丝凉风:“把这两个包子拿好,带回去给你俩弟弟吃,记得一人一个啊。”
妈妈怔了一下,只好点头应着。曾外婆的背影已走远,空气里却到处飘扬着肉包子的香。她用扁担担着两个盛放了蔬菜的菜篮,一路走一路咽着口水。走了一段路歇肩的时候,她拿出那两个用小塑料膜包好了的包子。——自己可从未吃过包子啊!她想到那两个肉包子现在是在自己手里。——吃了吧,多香的包子啊!——不行,是带给两个弟弟吃的。你是家里老大,闻闻香味就成了,让着顾着弟弟可是本分!
她的内心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斗争里。几经犹豫,最后,她对自己做了妥协——对,就吃一丁点。
于是她把其中一个包子用手抠下一点放进嘴巴里,然后边嚼边继续赶路。——嗯,待回去,这个抠了一点的肉包子就给大弟弟吃。——啊,肉包子味道实在太美了!她犹豫了一会对自己再次做出妥协,将刚才那个抠了一点的肉包子又掐下一点放进嘴里。
她吃完便有点欲罢不能了。她的犹豫的心绪也波动得越来越频繁。啊,不能再吃了,大弟弟的肉包子就被自己吃光了。——若再吃——就只能吃小弟弟的那个!
于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肩挑着两篮蔬菜的不足十岁的小女孩,一路怀着对两个弟弟的歉疚,一路轮番将那两个肉包一点点地抠下来送进了自己的嘴里。
快到村口的时候,妈妈猛然醒悟过来。低头看看手里的两个肉包,已被她抠成两个如指甲般大小的圆丸了!她的两个弟弟——我的大舅和二舅——那天好像心有灵犀似的守在村口等着姐姐,见到她便异口同声地说:“姐姐回来了!”
于是她迅速将两个小丸子一人嘴里塞一个进去。
“太好吃了,姐姐,这是什么呀!”
过了很多年后,大舅和二舅才知道那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吃肉包子。
没吃成的肉
那时的人结婚都早,妈妈十六岁就出嫁了。虽然婆家和娘家相隔不过个把来小时的路程,妈妈婚后却不太愿意往外婆家跑,因为我们家里吃的是香喷喷的白米饭,而外婆家里经年都是难以下咽快霉变的红米。
怀上我那年妈妈才十七岁。那年十月,挺着大肚子的妈妈收到外婆托人捎来的口信,说让她回去一趟。原来生产队里要杀猪了,那年头猪肉难得吃上一回,外婆挂念着妈妈能过去吃顿红烧肉调补身子。
妈妈开始有些犹豫,因为不几天就要临盆,这个时候去邻村的外婆家有些不大方便。可捎口信的人说了,猪明天就杀,吃了肉赶紧回村里来就是了。
妈妈毕竟没能抵住吃红烧肉的诱惑,收拾下东西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个把来小时的田塍路,那时对一个生活在乡村里挺着大肚子的农妇根本算不得什么。哪个大肚子女人不是这样终日为家事为田事忙碌到身子快发动了,才肯停下找人叫来产婆的么?外婆生二舅当天还在井边担水呢。
妈妈在外婆家住下后次日,却不凑巧,生产队里那个主要负责杀猪的临时有事出去,说是等到明天杀。妈妈在外婆家于是不得不再住上一天。
又过了一天,生产队准备动手杀猪了,却不想那头猪性情顽劣,几个大汉围追堵截了好半天,都把那猪按到地下准备开杀了,那头猪竟趁人手松一会挣扎着爬起来跑了。
猪跑了的那晚已是妈妈在外婆家入住的第三晚了。不过外婆也说了,晚上那猪回来了,第二天保准会杀。可是到了晚上九十点,妈妈的肚子开始剧烈疼痛,我着急要出来了。那时的农村,嫁出去了的女子是忌讳在娘家分娩的。临危不乱的外婆连夜发动住在附近的叔伯妯娌还有左邻右舍过来帮忙,他们临时支起一张门板当担架,大家七手八脚把妈妈抬到村里的机米场暂且安置下来。
机米场是稻谷脱粒的地方——一间比牛棚稍宽敞些的破屋子。低矮的顶棚结满了如迷宫般错综的蛛网,铁壳的电动脱粒机和木制的手摇风车漫扬着厚厚的粉尘。机米场的一角放置着几张破旧的箩筐,地上摊着从风车里扬出来未收拾干净的混着土灰的秕糠。屋外不时的夜风从门板和墙面随处可见的的孔隙中穿进来。子夜时分,我睁眼看这世界的第一眼,就是这么个地方。
次日清晨,已得到音讯的爸爸急急赶来机米场,和几个亲友一起把妈妈和我抬往自己村里。那时才八九岁的大姨也一路跟了过来。一亲友边“吭哧吭哧”地抬着担架边对尚是孩子的大姨玩笑道:肉又没吃成,还害我们几个抬得肩酸脚痛,干脆把你姐这个刚生的小妹妹抛河里去算了!
大姨听后当即就伤心大哭了起来,几乎是一路哭不停跟到我们家,小留片刻又跟着众人一路嚎啕返回自己村里。
二舅的故事
没吃到的第二碗粥
外婆家人口多,粮食不够,每天吃起饭来总是抢抢攘攘。好在那时多养个孩子不过多向粥锅里加瓢水的事,如果再多加几瓢水,每个人都可以吃到两碗粥了。——据说以前吃大锅饭有经验的人,第一碗饭只盛半碗,且迅速吃完,在第二碗时再添满满一大碗,然后坐下来慢慢吃。
我不知道当年外婆家尚是孩子的舅舅阿姨是否得知这个秘诀,反正通常情况下他们早餐时是可以去灶房添到第二碗粥的。许多人家孩子多且幼小,家里碗不够且防止被打碎,做父亲的会在一张长条凳的凳背上挖出几个凹槽,开饭后就把饭菜一勺一勺分别倒进凹槽里,孩子们就围着这长条凳挨挤在一块吃饭。舅舅阿姨们那时还好,吃饭时可以各自拿上碗筷去灶房盛粥添饭。
那时人们吃饭偶尔会“走家”。——“走家”就是窜门,在吃饭时才偶有闲暇端上饭碗去附近邻居家转转,边吃边与邻居闲聊上几句。通常吃饭时走家最勤的是小孩子。添了一碗饭可以满村人家屋里跑。不过我的那些舅舅阿姨难得吃饭时去走家,因为返回时添饭弄不好锅底就空了。粥是“过肚消”,第二碗也未必能完全吃饱。
二舅就几乎不走家的。早晨在灶房添了粥,经常就坐在家门口一侧的门槛上吃。住在外婆家屋后有个名叫端生的小孩,跟二舅相仿年纪,有段时间天天早上端着碗粥穿过自家的大门,再穿过外婆家的后门,经过灶房走向堂屋,然后坐到门槛上来和二舅说话。
端生端粥来走家的时候,有时二舅这边还在等着盛第一碗粥;有时端生来的时候,二舅已经在吃第二碗了。端生有时第一碗粥刚盛好就过来,有时盛了第二碗才过来。端生来了,就自动坐在门槛的一边,然后边吃粥边和二舅说话。小孩子之间对话的内容,无非是飞机和火箭哪个速度更快,谁家的铁环滚得有多远陀螺转得有多久,田里的螺丝水里的蚌壳哪个更好摸捉。
这些话题其实并不新鲜,因而二舅并不很盼望端生来,但端生来了,二舅也不排斥。好在端生也并不待太久,一碗粥不到的功夫,就从门槛上起身,穿过外婆家的后门回到自己家里去。然而有一天早上,端生端粥过来挨在二舅坐的门槛的另一侧坐下时,他的话语显然比平常要久得多,一碗粥端在手里吃了好久还不曾离开。等到端生终于离开,二舅也起身去灶房添第二碗粥时,发现锅里已经没有粥了。
为没能吃饱的那顿早餐二舅心里有些耿耿,次日端生再端粥过来走家的时候,二舅有点不高兴地大声说:“你不要再惹我说话了,昨天害我粥都没添到!”
二舅的话惹得正在吃粥的外公外婆和其他舅舅阿姨哄堂大笑。端生于是像做错了事一样讪讪的端着粥返回自己家去。
后来二舅考上重点大学进城了,而端生日常的生活一直拘囿在那个闭塞的小村里。最终云泥异路的两个小伙伴那样在同一个门槛上吃粥的情形,恐怕今生再不会有了!
没吃成的鲜桃
二舅年少时的记忆里,肚子总处在半饥半饱状态。一有空他就跟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在野外寻找能填肚子的东西。细梗蔷薇的茎刺,小心去掉一层薄薄的表皮就能放嘴里嚼;谷树上状如球乳的红色果实,伸手摘下就能送进嘴里吮吸。——这些食物是在枯燥的课堂上寻找不到的。在上完小学一年级那年,二舅死活不肯再上学。于是八岁那年之后,他开始给家里放起了牛。
不上学的快乐,是可以随处去寻找入口而食的东西。最美味的莫过于桃子了。那时并不是家家都种桃树。就算种了,许多树上结出的桃子也是青涩不堪。可这丝毫不影响村里那些调皮的男孩于夏季到来之际偷摘桃子的兴致。
有一年夏天,二舅有一次在野外放牛时,把家里那头牯牛骑到了很远的地方吃草。他远远看见前面的一丛灌木里有一棵桃树。一般人家是不会把桃树种到这而来的,一定是什么时候有人吃了桃子,随手把桃核丢在了这里,无意里就长成了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桃树。等他走近些时,他欣喜地发现树上结了好多硕大的桃子。他敢肯定,村里所有人家屋后的桃子绝对都没有这般大。但不巧的是,桃树前面居然有个盛满猪粪的露天茅坑!桃树的枝杈向茅坑这端斜逸过来,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鲜桃呈现在他眼前。
那满是荆棘的灌木丛和这露天的茅坑无法让他绕到桃树下去摘桃。夏天的热风一吹拂,鲜桃诱人的香味和茅坑难闻的臭味同时刺激着他的鼻观。但那鲜桃的香味显然更占上风。二舅小心翼翼靠近一点那个露天茅坑,伸手就抓住了一棵斜逸过来的枝梢。可是,他够不着那桃子,还需再向前一点。他小心翼翼向着茅坑再靠近一点。差一点就可以够着了!他一时兴奋,往前又挪了一步。——不想脚下却忽然悬空,他失足掉进了茅坑里!
他一身臭烘烘爬出茅坑。好在附近不远处还有个水塘,他飞速跑过去洗了个澡。
过了没几天,二舅放牛时第二次来到那个有着茅坑的桃树附近。树上那硕大的桃子像一个个惑人的妖女等着他走近。
他还想着去摘那枝上的桃子。他和上次一样向着茅坑往前慢慢靠近。他不信那个邪,这次还会失足掉进去。他抓住那满是桃子的枝杈,一只脚尽量在后面着力,一只脚小心地往前挪动一点,双臂尽量用力将那枝杈揪过来一点。这次他的手已经够着桃子了!他心里一阵兴奋。就在他准备将那棵桃枝扯下来的时候,他靠前的那只脚不知怎么一滑,他再次落进了茅坑里!
那已是二舅放牛的第三年。那年夏天过后,他就闹着坚决不想再放牛了。同年九月,已是十多岁的二舅如愿以偿重返学校升入了小学二年级。
阿姨的故事
炒米糖的晚餐
我有两个阿姨,小姨比大姨小两岁,做女孩儿的时候,两人同吃同睡同在一起做坏事。这里指的做坏事,是她们总合起伙来蹭小舅碗里的菜吃。小舅三岁那年就被过继到了隔壁屋的七阿公家里。外公七兄弟,七阿公老末,却一生未能婚娶。小舅在七阿公家,吃的穿的都比在外婆家这边好得多。两家共用一方墙,七阿公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两个阿姨用鼻闻闻就知道。她们不好意思直接上七阿公家里去,就伺机等小舅端着饭碗出来,然后两人将小舅团团围住,软磨硬泡吃上几口方罢休。小舅若躲在堂屋不出来,两个阿姨也总有办法把他骗出屋。小舅常常端着一碗没吃动几口的米饭又返回屋里来夹菜。
几年后大姨跟着同村的大姨父私奔去了城里讨生活,小姨失去了协助,一个人就不好多缠住小舅了。有一年正月,小姨跟着大姨进城来看看。那是小姨第一次进城。同进城的,还有大姨父家几个亲戚。他们是乘坐渡轮来的,抵达城里大姨的租屋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大姨说傍晚买不到菜,权且吃些炒米糖充饥吧。
炒米糖有的地方叫冻米糖,是我们乡下人过年必备的点心。制作炒米糖的工序很繁琐,要将洗净的小麦浸泡后捞起用水淋芽数日,切碎调入蒸熟后透凉的糯米,压榨出麦芽糖;要将洗净蒸熟晾晒至干硬的糯米在锅里爆炒至膨胀金黄,然后和熬煮拉丝后的麦芽糖一起搅拌,最后放入盆内压紧夯实,待散温凝固再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有条件的人家,制作炒米糖里还会撒入黑芝麻。
到舅舅阿姨都长大后,外婆家生活条件稍好些了,炒米糖里也有黑芝麻。——大姨家的炒米糖是从乡下带来的。小姨喜欢炒米糖,可那只是作为零食的喜欢。到了饭点,她还是想吃米饭。对于大姨的建议,她心里有点淡淡的抵触,但也只有点头。她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在这个已在城里安家的二姐面前无所顾忌了。而况,很多人在。想到次日要在城里逛一整天,小姨其实兴奋不已。
次日他们睡到半上午才起床。早餐又是炒米糖。这于小姨来说已无所谓了,因为吃完炒米糖,大姨和大姨父就带着小姨和另外几个亲戚出门去逛了。
那一天,小姨跟着大家一起,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条街道,穿过了多少个里弄——直至那林立的高楼和奔跑的汽车带来的兴奋在她两腿逐渐发酸后的意念里逐渐减弱下来。尤其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一个疑问渐渐在小姨脑海里升腾——都到午饭时间了,为什么没有人提吃饭的事?
小姨不敢问大姨。在过年这样的氛围里说饿显得多难为情。似乎饥饿与他们都无关,除了自己。就这样怀着越来越深的疑问与饥饿,小姨跟着大伙又一路从纵横的大街逛到交错的小巷,直到临近傍晚才返回大姨的租屋。
一整天的徒步,大家都显得疲惫不堪。又是炒米糖的晚餐。没有人表示异议,小姨自然也不敢说,她想吃米饭。
小姨的疑惑在大姨在城里过上了富足生活的许多年后才释然。原来,去了城里的大姨最初的生活条件并不比在乡下更好,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次那些亲友逛一整天的街且仅吃着两顿炒米糖,只不过,无米下炊而已。
不敢添的第二碗饭
小姨做女孩儿的时候,身材有些微胖。好在那时还没有减肥之说,小姨也从没意识到自己胖。那时她特能吃,一顿能吃三大碗米饭。油水不够的年代,又不得不经常干体力活,吃三碗饭其实也属正常。好在那时吃饱饭已不成问题了,小姨也从不看菜下饭,有没有可口菜肴都是三大碗。
小姨有时会上我家来。小姨喊奶奶做伯母,但她在奶奶面前一直有些拘谨,经常午饭也不敢留下来吃,处理完要办的事就着急赶回家去。记得有一次已临近中午了,家里也做了点好菜,小姨终于留下来吃午饭。奶奶帮添好一碗饭递给她,小姨坐下来只顾埋头吃饭,一会,便比所有人都更快地吃完放下了碗筷。奶奶说,快去添饭吧。小姨道:吃饱了,不吃了。
奶奶也就不再劝小姨。我在一旁奇怪地说:“你不是能吃三碗的吗?”我丝毫没留意到小姨听了这话有多窘。小姨忙说:“很饱了,真的不吃了。”
没多长日子,我和奶奶就辗转听到回到自己家去的小姨对外婆说的话:“伯母喊了我添饭,我很想吃,就是不敢再添。”
原来不止是在我家,小姨去别的亲友家做客,也经常是那样吃了饭但又饿着肚子回自己家来。
小姨后来一次上我家来的吃饭时候,我打定主意要帮小姨添第二碗饭。
吃完一碗饭,小姨准备放下筷子。奶奶也忙放下手中碗筷,说:“我去帮你再添碗。”
小姨推辞了一会,说:“还是我自己去添吧。”
奶奶于是嘱咐我:“你去帮你姨添下饭。”
我放下手中碗筷迎上来时,小姨已自己拿好碗筷走向灶房,边走边坚决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添就行。”
小姨客气,奶奶也跟着客气,仍嘱咐我去灶房帮小姨盛饭。
于是我也往灶房走。到灶房门口时,我停了下来——因为我惊讶地发现,小姨正低头站在灶台边,用锅铲把添进碗里的饭边边角角压了又压,压紧之后又添进一勺饭,然后再用锅铲压了又压。
也许是忽然意识到背后有人在看着,小姨吓了一大跳,待发现是我,吁了口气,小声道:“千万不要让你奶奶知道啊!”
这一次小姨来我家终于吃饱了饭。
后来小姨也嫁入了我们村里。结婚后的小姨身材竟变苗条了。当然,现在她一顿肯定吃不下三碗饭了。
何美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