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著名的游览项目叫九曲溪漂流。两条竹筏绑在一起,成船,由艄公撑着行于溪中,顺水流方向从第九曲漂向第一曲,历时两个多小时,行走十八道弯,一路下来看的多看的少,全在自己,都算阅尽了武夷山水。竹筏放两排竹椅,椅子不固定,人坐竹椅上,靠自身稳住平衡,可目视前方,可左顾右盼,往后看困难些,自由走动难度较大,因为站立不稳。筏上竹椅六把,一般六人同行,如胖子多,只能五人同船。漂流者穿上鲜艳的救生衣,预防落水,艄公提醒大家不要失身。凡在武夷山旅游的,无论逗留时间长短,大都会选择这个项目,在水上看山水,只动眼目,不劳双腿。
漂流码头设于九曲溪上游星村镇,码头三个,相距不远,可任意选择,凑够六人,即可登筏。与我们同行的,一对来自蒙古西旗,年轻人。另一对来自河南,已经退休,女士的腿有点跛,拄着拐杖。千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六人搭配成老中青三代,有缘同筏漂流武夷山水,该算千年老妖了。
看山水,古人说了三种境界,都在我们筏上。年轻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中年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老年人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不是这样,我没询问那对年轻人和老年人。至于自己,我觉得既看到了山,也看到了水,它们真实地存在于自然,我真实在它们里面。无非是人在山水间,或快或慢,起起伏伏,只可顺流而下,不可逆流而上,满眼风景没来得及细想,一路风光就尽过了,像浓缩的一生。
年轻的艄公举起他们熟悉的撑杆,竹筏之舟轻松漂进九曲溪,我们便如收拢了翅膀的蝴蝶,浮于碧水,不用飞翔胜似飞翔地飘去远一点再远一点的前方。这湾水大概可以称为碧波荡漾了吧,雨后青山可以称为新娘出浴了吧——先不要忙于去看去想这些,此时,闭上眼,仰躺在竹椅,深呼吸几口,便认为,应该再掏一百三十块钱给武夷山旅游公司,我相信今后好的空气也可以卖张附属门票,注明允许呼吸几次,一次几口,不能超过多少次多少口,但可以花钱像买纪念品奢饰品一样买一些装进口袋带走,赠送亲朋好友。想到此便有些痴了。可惜空气暂时不能完全禁锢起来——所以我又使劲呼吸几口,毕竟是免费的,真甜,还有香味,这才睁开眼睛,去看花钱买来的自然山水天赐美景。艄公们卖力撑竹筏,保持平稳,给观光者好的感受。他们每个人练就了一副好口才,除了景点传说介绍,还加入不少黄段子,让观光客笑声不断。比如把双乳峰说成“女人的骄傲,男人的嗜好,小孩的饮料,当官的圈套。”把笔架峰形容成三个代表:电表、水表、煤气表。把岩石下小小的土地庙叫土地局,武夷山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一百零八庙,在这些“骚公”嘴里成为讽世态、贬艳俗的对象,诙谐幽默中又总有那么点欲言又止的沧桑劲、辛酸味。据说,一船七百八十元收入中,艄公最多可得三十元,一天下来,撑四趟六至八个小时,累个半死,也不过一百多元收入,因此他们把自己说成起得比鸡早,叫得比狗响,吃得比猪差,睡得像个小领导。发发牢骚自是可以理解,同时那些不带脏字却入骨三分的讽刺让同船渡的人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共鸣、感概,旅途自然变得融洽,成为和谐小社会了。
坐在几根竹竿上漂流,屁股需要专注,认准了坐下,不能乱换座次,否则容易落水湿身。脑袋则可以三百六十度转动,只要能做到。脑袋里最好想点别的,比如美景、美女、美事,比如华兹华斯之类的诗人等等。但要坐稳了再去想,坐不稳掉进水里真成了水里漂就是空想、白想。华兹华斯的诗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我向往华兹华斯热爱山水、钟爱自然的执着和勇气,虽然没有能力效仿。据统计,华兹华斯一生走了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英里路程,每天在乡间和湖区行走,很多乡下人说他走路像只大谷盗虫。那是一种斜着行走的昆虫,类似螃蟹,或类似我坐的竹筏,斜行九曲溪之中。别扭的行走却给诗人带来灵感,成就了他关于大自然的诗作,如《致蝴蝶》《致布谷鸟》《致云雀》《致雏菊》《致小小的白屈菜》等等。城市的乌烟瘴气、拥挤、贫穷和丑陋,让华兹华斯抱怨,1789年夏天,诗人和他的妹妹再次来到威尔士的瓦伊河谷,亲身体验了自然的力量,并在随后的诗作中流露出来,伴随了诗人的一生。今天,在武夷山九曲溪漂流,我会不会体验到神奇的自然之力呢?
行于溪上,坐看武夷山峦,大大小小从眼前飘过,饱览美景之余,免不了生出恍惚感。这感觉来自周围的巨大空间和一个人蜷缩竹椅中的反差,有帕斯卡尔《沉思录》所说的“被无垠的空间吞噬”的惊恐。我在其中吗?这问题有点蠢。可是,武夷山水如何知道我在其中呢?我来过,我们来过,但这些山山水水不曾记得,最终我们自己也会遗忘。古人们把他们表达来过这里的字刻在石头上,刻得很深很遒,躲开了岁月的消磨,留存至今,我们看到了他们,可他们看不见自己。忽然明白华兹华斯鼓励我们走进大自然,体验真情,滋润魂灵,其实也让我们从中体验了自我的渺小、价值的可悲。大自然面前,人类其实很不堪。
一队队竹筏满载一批批旅人,前来又远去,玉女峰在九曲溪某个弯道上,沉默着目视他们靠近又目送他们远离。或者,她什么都看见了,或者,她什么也没看见。加在她身上的传说,是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随风飘散,流落民间,广为传播,只有她只字未提。沉默是自然界一致的声音。1712年,艾迪生《论想象的乐趣》说道:“广阔的空间让我思考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1835年,美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柯尔《论美国风光》写道:“这些孤绝之景不是出自自然之手,上帝才是它们真正的创造者,这是他完美无瑕之作,让人思考永恒之物。”当玉女峰、大王峰逐渐消失于视野,我再一次肯定所经历的山水,绝非人的创造。人类只能将其想象附着在它们身上,让自身演绎悲欢离合。可是它们,那些巨石,并不为之动容。最终,物质论者在无奈中,只能从编造的神话中持续物质索取,而非精神奉献。
我们常说人在画中游,因为看到了自身不具备的自然之美。我们在九曲溪现实主义的画中漂流,体验到不同程度的快乐,并且沉浸在自身的快乐之中。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画作,它源远流长的写实是不是表达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这世界是永恒还是瞬间?我们留下了永恒,带走了瞬间,还是带走了永恒,留下了瞬间?
写于2014年
整理于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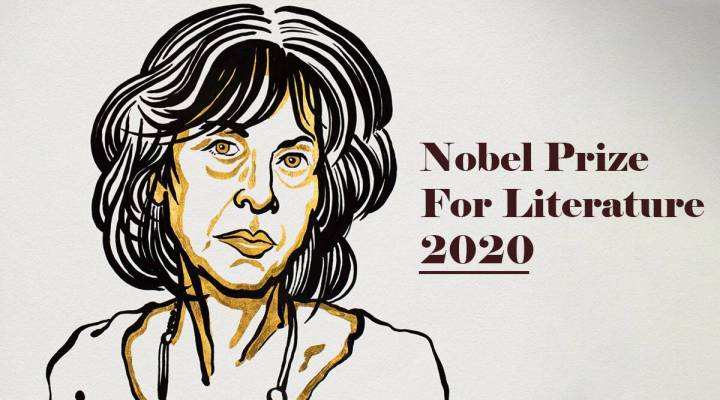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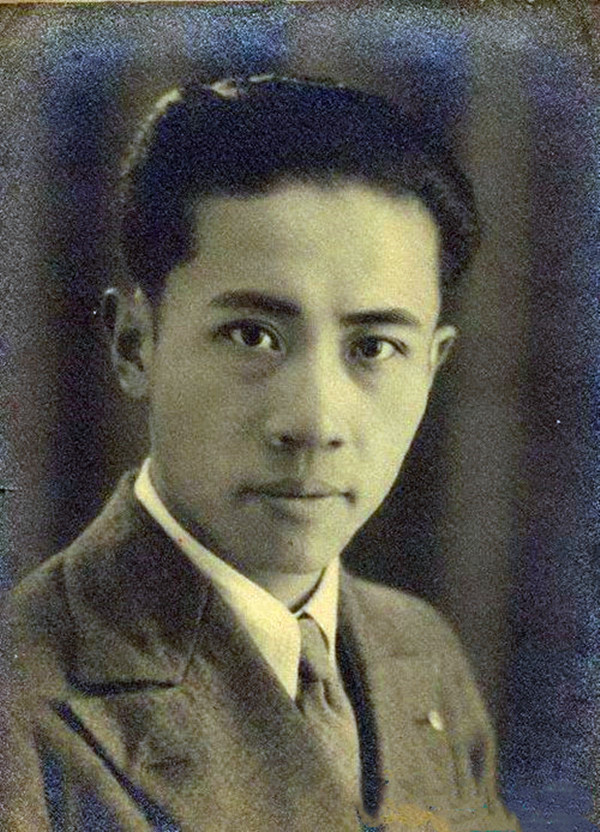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