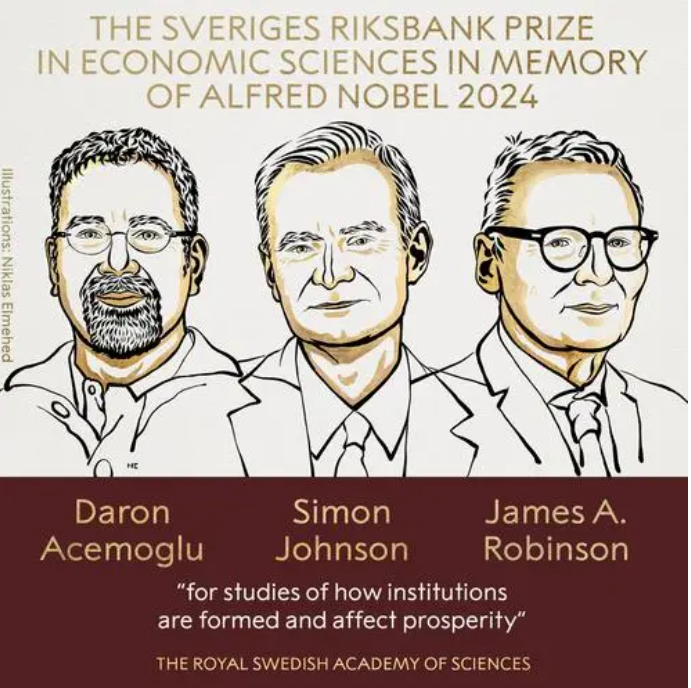拐一个弯路,我与主人上了马路。马路上一些咬不动的大铁盒子跑来跑去,穿梭熙攘。上一段坡,拐到下沿,走入一段破烂的比我以前的狗舍还旧的老区。那些只有人叫它房子的东西;墙面斑驳,有的裸露出红砖,有的自墙缝都长出了绿苔。一些和主人面孔差不多的人蹲坐在路的两旁,面前摆放着一堆堆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有活的、有死的、还有青草和在水里游动的东西,像是叫卖着什么。这些声音我不熟,我只知道他们吆喝的嗓音相比于我差得很多,那声音既不嘹亮也不高亢,而且丝毫没有一点儿威慑力和穿透感,声音小的像我放屁。他们蹲下的身高和我差不多,没有我主人高大,我和主人像检阅他们一样。
我的主人待我没说的。他把我从穿一色制服的人堆中领回了家。我在以前的地方很苦,那些剃着小平头的家伙,没事就让我闻闻这个闻闻那个,然后扔出个东西老远,让我跑来跑去地来回折腾;时常还克扣我的伙食,用饥饿的方法强化我的记忆。不像我现在的主人,随我吃、随我玩,对我像对待儿子一样。而且我与主人相处的时间,比他与儿子相处的时间还要长很多。
我每天一早,是我与主人送他儿子上学的时间。他的儿子个头站起来比我高,双肩背一个不知里面装什么东西的包包。每天我与主人送他到马路上,看着他爬上一个大大的铁盒子喷着烟走了,我才与主人溜溜达达地回家。
我的主人脾气很好,也不知是我依赖他还是他依赖我,每逢他出门,我都在家静静的等他。即便我等得时间太久,困了,门外有一丝响声,一缕他的气味,我都会飞跑到门边,与他嘟囔几句,并用我的前爪挠门。
通常主人开门见到我,会抱我亲热几下,用满嘴刺鼻的酒气,熏我的嘴巴与鼻腔。尔后他会自身后拿出一个塑料袋,高高地举起,让我上下、站立、跳跃,引诱我。从袋子里飘出的味道,我知那是给我特地打包带回的骨头和肉食,那股雀跃、亲切、喜兴,让我不知如何缠磨、舔吮、亲热,这位同我一样站着尿尿的男人。但有时我认为我的主人很可怜,常看见主人的女人和他争吵。通常吵架时,我的主人是唉声叹气地坐着,女主人是站着。有时女主人嗓门特大,争吵一番,气不打一处来,她会用手指向我。有一次女主人气头上还踢我屁股一脚。我惊恐了,慌忙躲在主人身后,瞪大眼珠看着他们。虽说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但隔三差五的吵架,耳朵过滤了几十个来回,大致就是这样的语调。
女主人伸直食指指着我的鼻子时,通常是在骂我的男主人。
“你整天游手好闲。”女主人伸手一戳我的鼻子。“就它,这条破狗,是你爹,是你娘,还是你的老板?它能给你带来工作,还是能给你赚钱?”
我的男主人搓着自己的头发没应声。
女主人用手指指向他后又指向我。“你快跟它一块过吧 ?操!人还没养活,还有精力养狗?下岗也不赶紧找找工作,难道你一个男人(又指向他)还要指望一个老婆养你吗?”
一次,他们吵骂厉害的时候,我叫人尤其是女主人给吓着了。看女主人的指头随着骂来骂去的声音,在我与男主人之间指来指去。我不敢吼,也不敢发声表示委屈,因为我从没有向他们索要过非分的东西。我没要过钱,也没要过什么女主人脖子上、手上戴着的东西,也从没给他们摔过脸子。我基本上是任劳任怨。在这个家我首先是听男主人的,因为男主人最关心我最照顾我最疼爱我。男主人高兴了我会陪他玩,陪他跑。有时男主人抑郁了,我也会老实巴交地坐着,一声不吭地陪他抑郁。他们时常地争吵,有时都减弱了我的听力。有时我用眼睛来回瞅瞅我的男主人与女主人,看到男主人一味老老实实地不应声,我也只好跟着他窝窝囊囊地听着。
女主人时而罄竹难书的数落,时而悲愤满腔的责骂时,我甚至不敢用前爪挠自己的耳朵。
时常我看看我的男主人,一个也是站着尿尿只是不用抬腿的男人,头上也不知被长头发的娘们用指头戳了多少个窟窿,且还一昧忍受着。我认为男主人活着还不如我。
至于谁生下的我,我不记得了。按照人的说法,我是自小就当兵了。在那个军营,他们用骨头和肉诱惑并折腾了我好几年,且从没给过我工资,劳保,甚至也没办理过离退休手续,医疗保险,就把我打发给了我现在的主人。
再说那鬼地方我也呆够了;缺乏狗道,折腾体力。我要感谢我的主人,如果没有主人接我回家,很难说我的命运如何?人通狗性,狗通人性。人时常和我一样,有时是他看我的脸色,有时是我看他的脸色。有时我的主人手一挥 ,我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时他吆喝或咳嗽一声,我也知道他哪不舒服或者该去大解了。我活得简单,不像人解决了这个又想着那个。除了吃,我从没有也不需要有其它的要求。随遇而安的是狗而不是人。人有舍弃狗的,而狗却从未舍弃过人。有时看到人好像羞于做狗,耻于做狗,时常随口而出“狗逼养的”,我认为这是人对狗的嫉妒。其实人和狗不分彼此,每个人都当过狗。你看只要是人,谁没当过狗呢?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即便是他人地位到达了顶峰,也未尝没干过狗事、狗活、吃过狗屎。
很多人吃无数的狗屎,干无数的狗事、狗活,才开悟到如何聪明、灵性、忠诚。而且人的忠诚不单纯是为了吃,他还有很多欲。人呢,包括夫妻吃不好就会开溜。
有的狗与生俱来就是宠物。有的狗生来就是被人驯化着看门、出力的。还有的狗生来就是被人宰杀填饱奇异口味肚皮的。
人呢?当宠物,即便是有,这当宠物的时间太短,也就三五年的光景,且还是家境优越的人家。当思想与体力的苦力是正常。至于人被人为的宰杀,我认为比惹怒了自然宰杀的要低。
我的主人常带我逛这条菜市,很多人看我气宇轩昂地路过,他们有时趁机在我的头上或屁股上摸一把。菜市脏污,路面泥泞,气味混杂了世间的一切。有站起来比我高的,也有蹲下和我一般高矮的见谁就吆喝两声的摊贩。他们的皮肤比我的主人都差很多,衣服的毛色,好像饥一顿饱一顿的野狗一样。我与主人走走停停,走到一个宽敞的那儿都可以四瞅的路口,一个我先看见肚子后看见个头的人,将我主人拦下说话。我想自己走走,但主人套在我脖子上的项链,栓住了我。我不熟悉的人,也没兴趣搭理,自然也不知俩人瞎叨叨些什么。不一会儿,和我主人说话的人,蹲下身子,摸我的头,也不知是问我还是问我的主人。
“它叫什么?”
“鲍勃!”主人说。然后给我介绍。“鲍勃,叫大爷,大庙山大爷。”
这个叫大庙山的人,用手捋着我脑后的毛,微笑起来许多器官往中间凑,像肉包子一样。
这种人我见多了。我没应声,只是让舌头在空气中凉快着。
“鲍勃!”大庙山说,“名字怎么像我认识的蚂蚱眼。”
我瞅着远处,偶尔瞟一眼眼前的这个胖的蹲下都摇晃不稳的人。
“鲍勃。”主人又唤我,手指着他的鼻子。“这大爷是副厅正局级……是大干部。”
此时我两眼并拢,看看眼前这位主人介绍是什么级的大干部,后腿不知怎么,一条腿本能地抬了起来……
蚂蚱眼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