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欢喜散步,用清晨时间。1931年,他来国立青岛大学讲授“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不到三十岁,散步不像闻一多、梁实秋二先生那样携带拐杖。拐杖自然和年龄没必然联系,握根拐杖戳点草木、石头和季节,走走停停思忖点什么是种调调,如同有的人抽烟斗写文章,或写文章就抽烟斗,火灭了也含在嘴里吧嗒两口。沈先生的“牧歌”式调调都展现在他的小说、散文等文字里,也喜欢“牧歌”式散步。他一般顺福山路往南走,就是我眼前有点狭窄的车辆单行山道。山道目视中仿似直的,实际绕行在八关山麓,不知不觉转着弯,不知不觉让人迷失。日占青岛时开辟了这条路,在半山腰,叫敷岛町,正好躲开两侧德占青岛期间盖的红帽建筑。靠上山一面石墙陡立,足三米高,垂挂枫藤或迎春等藤蔓植物,也有树木枝杈摊在墙头,颜色青绿,山顶散居各种建筑。往山下是一条条石阶叠起的巷子,两边堆满房屋和围墙,从福山路崖朝下望,如韩剧,浪漫悠长,看不见底。沈先生沿福山路南行,很少拾阶而下,拾阶而下或拾阶而上其实愈有“牧歌”感,或可把自己飘成一朵音符。
沈先生每天清晨散步到太平湾,沐浴海风,听白鸥独飞的啼鸣,看海浪鼓噪的波涛,最后再折回来。“海边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孤独是不示人的情感,与人生寂不寂寞无关。在青岛的山海之间走来走去的沈先生并不寂寞,那时他在恋爱,热恋苏州闺秀张兆和。有情书写不言寂寞,即便言寂寞也非寂寞,而是调调,类似用拐杖散步。如此说来沈先生多少有点矫情劲,还好没到做作的份儿。他这样写:“学校离我住处不算远,估计只有一里路,上课时,还得上一个小小的山头,通过一个长长的槐树夹道。山路上正开着野花,颜色黄橙橙的如金子。我欢喜那种不知名的黄花。”一里路和不知名的黄花不重要,重要的是“欢喜”。苏州人说喜欢不说喜欢,说爱不说爱,而说“欢喜”。“我欢喜你!”一句顶一万句。张兆和这样说属自然流露,自是喜欢得很,一个湘西人如此说,便有矫情的嫌疑,在这里,寂寞孤独的只有黄橙橙的花了。由此,我琢磨沈先生去授课,进校园不会从海大四号门和五号门进出,因为有条“长长的槐树夹道”从山头直通校园,不说一里路,就是三里五里,沈先生都会乐呵呵地走,因为在远海和天地之间有块草坪,草坪需要一点儿黄色,便真的有了一点黄:“那是一个穿着浅黄颜色袍子女人的身影。”
我很想推开福山路3号沈从文先生故居的铁门,进去走走槐树夹道,找到黄色的野花和身穿浅黄颜色袍子的女子,可内开铁门关着。等了许久,一对老年夫妇外出归来,用钥匙开了门,我赶紧走过去,打问是否可参观沈先生故居,回话说不能,因是私人地方。铁门又关上了。此刻220路巴士驶过故居门口,停在故居南侧齐河路站牌下,一位撑阳伞的中年女子上了巴士,无人下车,巴士很快开走了。一年后,经过三年半悠长的恋爱,张兆和撑开油纸伞,素面低首,拾阶而上,迈过最后一级花岗岩台阶,朝海边散步返回的沈先生款款走来,像个素雅的音符,让沈从文先生在青岛收获了顶重要的一句表达:“我欢喜你。”
我盯着那级秋阳下竖条纹的台阶发愣,也想顺福山路散步去了,手里有根拐杖拄当是更好。
写于2017年
整理于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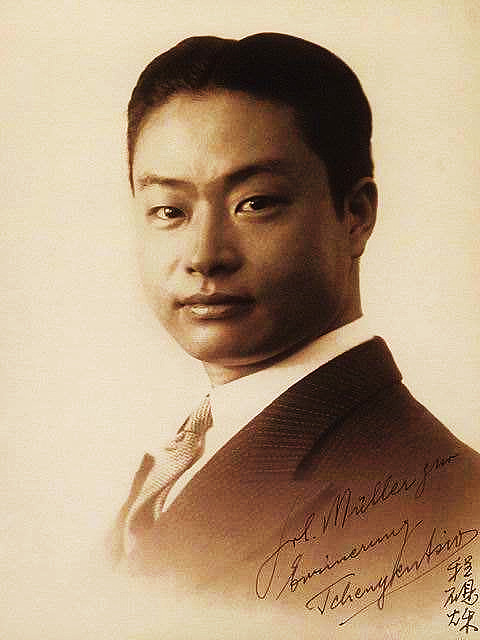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