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鱼山不高,像块岩石,从海中凸起的略大点儿的一块。说它像位老人蹲坐海边也行,说它少女般玉立海边也行,状态似沉睡,神情却宁静。海风吹过或海鸟盘旋时,意识到它大概是有生命的,体内的生命元素是沉默,竭力与时间抗衡。这沉默与生俱来。它望风景不言,不像我,总想说在看什么和看到了什么,此为岩石与我的重要分别。长此以往的结果是,它一言不发,却诉说了全部,且说得明白,我看到和说过的再多,不过其中一部分或微小的局部,且说不明白。或者这样认为:小鱼山看见了与它同样静思默想的时间,我却只能得见时间中存在的事物。它望见海洋,我望见半瓢咸水。
由于特别接近海沿,小鱼山就成望风景的高点了。山顶上,一座飞檐碧瓦的八角三层塔,名“览潮阁”,十八米的高度高出六十米的山体一截,每一层一圈汉白玉围栏的平台,围成观景回廊,供环绕瞭望之用。这样凭栏望风景,既有瞰视感,又有全景视觉,边转圈边极目,收入视线的就是三百六十度立体图。当然,这图景最终在记忆拼成的画面比抖翅升高的海鸟俯视到的景观,饱和度、灵动性和立体感可能都欠缺,人的视觉能力和由之创作的艺术作品比鸟类一瞥仿佛少了一次本质性进化——虽然这类进化不存在。可正如总有人相信自己来自猿类或一只落地的猴子,更深夜半逃离密林,裸奔中开始进化,大平原上成了人,嘴里含片树叶,双手高举,挥舞成胜利状。在小鱼山穹形门入口,我摆过这个形状,两腿叉开,双手举过头顶,相机胸前晃悠,表示顺利到达这里,用的是人的足迹,摆开的是人的体态,在别人眼中,或悬空掠过的海鸥眼中,可能貌似一只大猩猩逃脱公园铁笼,一路没进化好,流窜到这片丽景之地也说不定。
潮汐漫过一块礁石,又漫上一块更大个的。赫拉克利特还有一句名言:“万物流变,无物常存。”如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说的是瞬间,此处则在说永恒,和进化就没多大关系了。“永恒的流变”从我的左肩到右肩,又从右肩到左肩,不停地来回,我却毫无察觉。这并非我看到,而是登上“览潮阁”第三层观景回廊首先想到的。一群海鸟仿佛明白我的心思,树叶般飘去汇泉湾,于是,我最先把目光投向了它。飞鸟没落去海滩,它们回旋了几回,又升高了,冲去它们更想往的蓝天。落在海滩上的是些大大小小的人儿,大概高度和距离的缘故,看不清他们的眉眼鼻嘴,来自何处,却能看清他们躺着、站着,或在行走,当然有的在游泳,金黄色海滩便多了斑斑点点的颜色,海水里也像撒了彩色纸片,被海浪簇拥着移动,如漂浮物。这些当然不是视觉的中心,因为他们太小了,不过似秋天几片落叶,不管什么角度,一阵风过就能吹走。视觉的中心是汇泉湾本身,它有个让我着迷的轮廓。这轮廓与高高矮矮的建筑物无关,也与绿树和树荫中蜿蜒的海滨大道无关,而是海水划定的游移不定的白线条。这线条是根内弯的弧线,内弯指海滩而言,就海水或大海而论,弧线是外凸的,是圆的一部分。趴在“览潮阁”的栏杆上,一方面理解了“览”的含义,因为那条划定大海和沙滩的白线,是水的泡沫,是潮汐鼓荡的结果,它在不停地撞击中变化曲线,却毫无声息。闻一多先生住海边时,因海浪噪音难以入眠,怕是万籁俱寂之后的事,可以想象海浪一刻不曾休息,这让闻先生不能忍受,若海浪忽然休息了,随万籁一同沉寂,能不能忍受呢?他深夜该到“览潮阁”睡觉才对。另一方面,趴在栏杆上,海风擦过耳垂,我眨巴着尚未深度进化的眼睛,琢磨那条白色弧线,假如换一种弯曲方式,即反过来,让沙滩外凸,海水内凹,该是怎样的风景,我想,假如这样了,世界一定发生了深刻的变故,或进行过一次重大进化,那样的话,人会不会多个脑袋出来?我重新振作精神,感觉一切还算正常,望见的还是我们常识中正确的风景:汇泉湾海滩像个弦月,在小鱼山看是右弦月,在太平山看是左弦月,从大海上望是下弦月,从信号山望是上弦月,总之是弦月就非异常,而大海,汇泉湾的大海,始终是个由海水灌满的太阳,饱满地舔舐弦月,既不完全吞噬也不彻底远离它,让它始终是个残缺的月亮。那年冬天,雪花飘飘,先到达太平山,再拐弯到小鱼山,然后飘进汇泉海滩。隆冬里,海滩像枚新月,残缺的新月。雪花落到仰躺在残缺月亮中的梁实秋先生身上,月牙上仿佛多了只毛毛虫。整个海滩,只他自己,沙子冰凉,海浪有声,刺啦刺啦在他脚前划着弧线,梁先生浑然不觉,只觉得整个海滩都属于他了,或全世界只剩这枚新月,却无残缺。寂寞是残缺的填充物。
风景美妙,却也寂寞,并非人来人往能冲淡它们孤寂的情怀。但丁《神曲》中写道:“四周一片岑寂,只有一缕清风飘忽不定,来也无名,去也无形。”寂寞发展到了极点,无从把握,犹如生命孤独地航行在漆黑的海上。极少完美的人生,光鲜照人是其表面,光彩熠熠是其装扮,迷失才是道路,残缺才是本质。人们不厌其烦地往风景地钻,用名胜古迹的寂寞填补人生的残缺,用风景之美换取生命的乐趣,旅游的魅力即在于此,在陌生的风景地,因为初来乍到,因为第一次,自己犹如回归最初,观摩生命路上早已远离的破碎但熟悉的自己。那是个可怜的背影,在他乡依然寂寞的背影。转身,向右移,目视南方辽阔的海域,一条驳船托拉白色水线驶离,波光淋漓有致,乃海洋之梦的碎片。那个隐隐的所在是小青岛,那个依然隐隐的所在是栈桥,逆光中,它们换了件衣裳,灰白但素雅。我知道在小青岛,有座灯塔,高十五米半,白色的塔身,八角形状,立在岛的最高处,像小鱼山的“览潮阁”一样,不同的是它的四面都是海,被海水包围,白天望海景,入夜为往来船只导航。它的体内装有航标灯,射程十五海里,因此,在幽暗的深夜,“览潮阁”成为“听潮阁”时,它也在看风景,用自己发射的光亮探视,也让船舶进出胶州湾时辨明航道。我想,人类的思想家们也像这座灯塔吧,他们脑袋里装载水晶的反射镜,旋转着发出亮光,那怕只能照射十五海里,却足以让众多的人生不致迷失,找到出发和回归的路,虽然这些思想家们不能保证自己不迷失。然而,即便“无物常存”,思想仍存在,或存在的存在,来无名也好,去无形也罢,在通往真理的途中,他们为我们照亮一截航道,只要我们渴望走过去,这就够了。至于栈桥,它让我们找到迈动双足走向大海的感觉,但只能浅尝辄止,步行一小段。所以,它像根伸往大海的四百余米的火柴杆,当走到回澜阁,走到火柴杆的头部,眺望小青岛和海洋时,我们将想到点燃和燃烧,也许它正在竭尽全力伸出去,试图引燃小青岛的灯塔甚至海洋吧。这是个无限接近的目标,一个美好可见的愿望,但它们始终保持那段不能再接近的距离。所以,远观之下,栈桥又似一支折戟沉沙的响箭,挣扎地抬着头,倔强地凝视未竟的目标。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可是现在,它们是众多人理想的观光地。
感受瞬间需要转到小鱼山“览潮阁”北面,俯瞰眺望青岛老城,或称之为旧城,即凸起在大片丛林中的红瓦屋顶,它们既不老,也不旧,却如崭新的,阳光下光彩夺目,摄人心魄,荡人胸怀。可视线无论怎么游移,左摇右晃,总无法摆脱信号山南麓上的建筑,它像是时间和空间的聚集点,有足够的能力把你飘移的眼球吸引过去,但仔细扫描,其中似乎并未包含瞬间的东西,永久之物貌似更多,所以,感受瞬间并非易事,不是睁眼闭眼能解决的问题,倒不妨称之为寻找瞬间。也许寻找的过程就是感受的过程呢。即便瞬间,或瞬间的百万分之一,也有个亚里士多德称为的不可缺乏的“整一性”,因此,这必然是个完整的行动,而行动的目标,我终于明了,就是那栋总督府。让我简要叙述这个过程。
到达小鱼山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内,在下沉的校内体育场东南侧,被信号山半山腰的总督府吸引,驻足观望良久,那时候德国总督特鲁泊上将从总督府二楼正观察俾斯麦兵营的动静,当时没动静,普鲁士士兵正在午休,海大的学生们也在午休,闻一多先生躲在故居二楼,抱书仰躺分析《诗经》的一句话,脚趾头露在老布鞋外头,而我在一棵树干比我粗两倍的法桐下一声没吭,树荫覆盖着我,我躲进将来之中,特鲁泊上将也没发声音,吐了两口烟圈,隐去窗后,甚至拉上了窗帘,好像阳光有点刺眼,之后竖窗前没再见他的身影,也许他去了院子,在斜坡的石阶翘首欣赏总督府的恢弘呢。他特别欣赏蘑菇石垒砌的墙垛和窗角,那些花岗岩,让他感受到持久不变,像一整盒雪茄烟升腾的香味。牛舌瓦让他想到征服者的血,凝结在屋顶,固化为绚丽的史诗。最后他和我得出相同的结论:总督府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不仅是一道风景,还是个可供怀念的伤疤。
于是我希望接近总督府,像栈桥试图接近小青岛,可能进化的缘故,我比栈桥略微聪明,晓得接近的方式,有效的方法一是俯视,一是近观,不能用第三种:躺着不动。最好能有一种方法取代前两种,这样省事,前提得借来特鲁泊上将的望远镜,用瞰的形式,能俯视又能近观。我借来了独眼望远镜,古老又破旧,不过挺好使,用力一拉长达半米,像根火柴杆。我想到小鱼山,那儿高,离总督府近,我走出海大只进不出的四号门,顺着鱼山路往前,从海大五号门左柺,上坡至顶到了福山路,福山路上文化名人多,大家都知道。沈从文先生一早散步未归,不知去了海边还是别的地方,照习惯早该回来了。山体夹道的石阶上,张兆和女士撑开油纸伞,如画入石墙一般,亭亭玉立,嘴半张开,那句“我欢喜你”尚未出口。220路公交巴士再驶来一辆,打大花阳伞的中年女士收伞上车,未来得及看清长相,一条腿在车门外,脚穿软羊皮面的棕色轻便鞋。苏雪林女士的马车刚好在山道上拐弯,只见一个背影,短发被山风吹成了直线,转眼她和车就都消失了。我继续往前,似是冲南的方向,回头看总督府,视线被粗而歪斜的法桐树杈挡住了,也可能是肥大的树叶或被八关山挡住了,八关山上红屋顶的建筑多,据说洪深、吴伯箫、成仿吾等先生都住这儿,顾不上细看,我心里着急,因为不见了总督府。我加快了脚步。不多会儿左拐上了福山支路,不多会儿福山支路有个分岔,一条波螺油子路弯曲倾斜下行,一条柏油路也倾斜着,是个爬坡。走波螺油子路能到康有为故居,康先生一般在故居二楼的风雨廊望汇泉湾的风景,望累了便搬把藤椅躺下,他记起曾经有人问他:“子历览万国殆尽矣,何国为善也?”康先生捋着花白的大辫子说:“夫固各有所长也。”老油条的辞令,如同说女人。他仰躺藤椅,脸部肌肉松弛,像在微笑,其实他想说苏格拉底说“人类不得不学习的是如何趋善避恶”,但他忍住了,一有拾人牙慧之嫌,二者说了也没用,人非善类,不如不说。这时候康先生躺在故居的风雨廊,躺在青岛的红瓦绿树中,蜷缩着,像件满清的小棉袄。我不便打扰,再者心里惦记总督府,我得尽快找到它。我走上柏油路,爬坡中在12号熊希龄总理故居耽误了点时间。熊希龄总理故居院内2号楼下,一个青花瓷缸种了荷花,花已开过,除了一片荷叶还绿,其他包括荷梗,都枯萎了,成了残荷,我觉得应该凭吊一番这缸残荷,就围绕它转了几圈,周围的植物都还绿着,这残荷就生出些特别,可来不及细想,我兜转几圈便走开了,继续往上,随后到了小鱼山穹形门入口,我面对马路,摆“V”字形,酷成青蛙,两腿叉开是倒“V”字,双手高举成正“V”字,两个“V”扎煞着,似两个响亮的口号,但我实在不清楚自己战胜过什么,就那么摆了会儿,然后买票进了山门。
眼含苍翠,顺山道缓行,右扭脸,从榉树、枳树、藤葛缝隙,见信号山南麓的总督府,如同彩色的鱼,举张红帆,在绿树丛游泳。还是太矮了,我得寻个高点,这样才能发挥独眼望远镜的作用。我望见了“览潮阁”,在此地它有惊人的高度,可一览大海和城市。我找到入阁的门,是拾了几级台阶之后找到的,我走了进去,内里似圆筒,如我手里放大几倍的圆筒,开阔空洞,假如去掉顶盖,便是望天的望远镜,也是坐井观天的枯井,适合和尚或道士静坐,不适合闻一多先生睡觉养生。圆筒两侧为旋转向上的楼梯,一边写上,一边写下,互为不相扰的道路,我从上的一边向上,在去二层的平台,看了会儿贴在墙上的一张黑白照,照片中两个男人,也是黑白的,从一个远去的年代拐过一道石墙出来,路是泥土路,背后是层层叠叠的石墙垒出的台地,旁边一副木架子支撑的石板桥。两个男人没走石板桥,看样子是沿泥土路去海边,我在“览潮阁”顶眺望的海边,左边的男人除了穿件白上衣只一枚扣子之外没别的特色,右边的男人带顶六角麦秸秆围笠,抬起右手扶着,估计怕海风吹走,围笠把脸遮成黑色,大辫子,和康有为先生的一样,垂在胸前,右手还抱着什么,因为我在拍照,这个男人就收住脚步,礼貌地等我拍完,两个男人背后的小男孩和一头牛,都静静地望着镜头。我收了相机,不耽搁他们往海边去,然后读照片右下角的文字:“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即墨县东海边筑城设防建鳌山卫,下辖浮山所浮山备御千户所雄崖所。部分内地人迁移到胶州湾东畔定居。从明朝永乐年间之后,陆续建立上青岛村、下青岛村、会前村、小泥洼村、小湛山村、大湛山村……”我从这些村庄的尸骨往上爬,很快到了“览潮阁”三层回廊,在回廊北侧望总督府,这下好了,青岛旧城一览无余,总督府尽收眼底。
我拉开独眼望远镜,不仅看清了整个总督府,还能看清它的局部,红瓦屋顶、青灰色蘑菇石、凹廊、滚圆立柱、明朗的墙基和暴筋的墙角历历在目,就连辉煌、华贵、荣耀、统治……之类也能看清,但我主要想找到特鲁泊上将,想知道他走出办公室之后去了何处,透过树丛我一点点搜寻,不放过任何角落,在总督府前左侧方,我望见几根巨大的松柏木,那是从欧洲运来的,还没来得及派用场,不知为什么就那么一直撂那儿了,往右移,府前一个摊平的院子,中间喷水池一座假山,假山不高,幼儿也能攀上去,但禁止攀爬。假山前一把石椅,有高高的靠背和扶手,和木头椅子一样,据说是世上仅存的三把石椅之一,特鲁泊上将就坐在上面,我以为他在看风景或山下的俾斯麦兵营,他平时坐在上面让旗手用旗语发布命令,稍后兵营传来响亮的口号,震撼天地,特鲁泊上将点燃一支雪茄,吸得津津有味,雪茄的烟雾在小鱼山就能看见。但是现在他没看风景,没吸烟,也没发号施令,而是两腿叉开,双手耷拉扶手上,低垂着头,仿佛睡着了。也许他一直有坐在石椅中睡觉的习惯,但未经考证……一片树叶正脱离枝头,我瞬间合上望远镜,不再观看——让树叶永恒地飘吧。
写于2017年
整理于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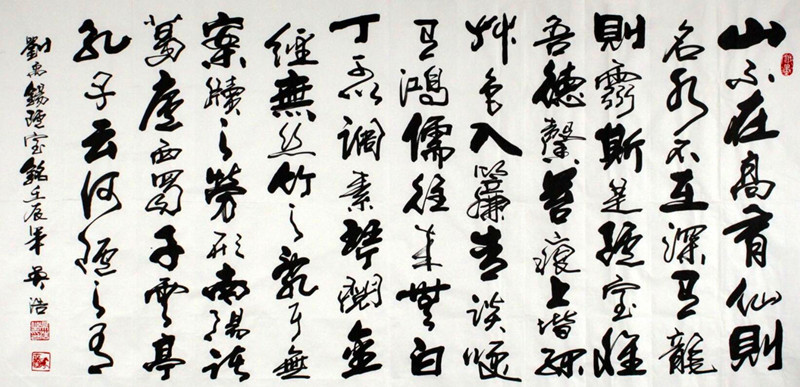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