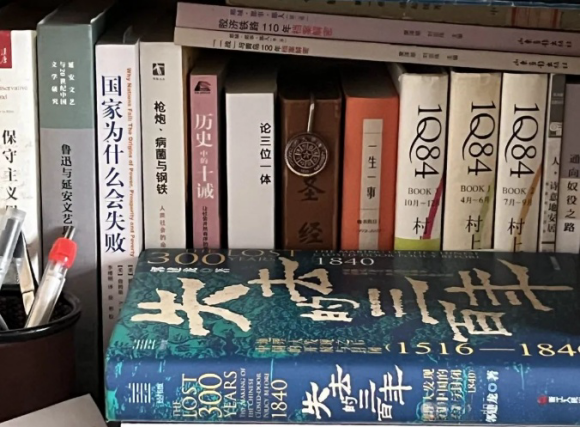电影《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导演最好的影片,也是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从电影首映到今天,时隔那么多年,每次看都有新鲜的发现和感觉。尤其是在一个特别难以确定的时代里面,看看这样的电影是很醒脑的。
关于这部电影,其艺术成就有目共睹,在此,我更想就电影桥段与京剧名伶的轶事做点说明。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没有比台上光彩照人的“戏子”更能体现这一番话语的真谛了。
《霸王别姬》的两个主角是程蝶衣和段小楼,段小楼的霸王很容易让人想到名伶杨小楼,而其身上还能隐约见到金少山的以及“文革”中境遇不佳的名净裘盛戎的影子。相对而言,程蝶衣则颇为复杂,这是一个典型,不能把他具象于哪一个人物,但从现实人物的身上可以找到戏剧人生的构件。这一悲剧人物集合了众多名伶身世、命运、际遇,在他的身上,能见到梅兰芳的影子,程砚秋的身世与性子,新艳秋、马连良的“汉奸案”隐情,尚小云、荀慧生的“文革”遭遇,言慧珠的悲惨结局。
“蝶衣”这个角色让我想到程砚秋,而且,其角色人设明里暗里也指向程砚秋。首先其“程”姓明显与程砚秋相合。其次是小豆子(程蝶衣)学艺之初与程砚秋暗合。程砚秋出身满清世胄,幼年丧父,母亲不善生计,不得已入了梨园,这和剧中蝶衣母亲将儿子送入科班很相像。电影为了突出母亲之无奈与狠毒,设计了蝶衣是六指的桥段,其母以刀断儿枝指,这是艺术夸张,其实当时程母将小小的承麟(程砚秋幼名)送去学戏,其内心的无奈与残忍几可与电影中蒋雯丽饰演的母亲相比。关于承麟是如何走上戏路的,目前说法不一。张次溪在《城都名伶传》 中说:“时北京重声歌,器曲所人,骤可致富。乃诸干日欲学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瑛却有另外的说法:与承麟一家同住在大杂院里的一位唱花脸的,很同情托氏(程砚秋母)孤儿寡母,向托氏提议说:承麟这孩子的模样俊可以去学戏,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日后兴许也能成气候。无论是承麟自己要求的,还是唱花脸的提议的,托氏对此的态度却是一样的: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身为名臣后裔,怎么能沦为优伶戏子?尽管托氏是戏迷,但她将听戏的和唱戏的分得很清。不管听戏的是贵人还是贫民,身份终究比唱戏的要高。不是说戏子是阔佬们的“玩意儿”么,她怎么忍心将有着高贵血统的亲儿送进“火坑”!可是,托氏在拒绝了以后,却悲从中来,其实已经动摇。托氏既不情愿承麟沦为戏子,却又为生计所困,当她不得已将儿子带进荣家,写给师傅荣碟仙,她的内心大致应该与电影里的“蒋雯丽”是一样的。
剧中程蝶衣出科前艺名“小豆子”,其师兄艺名“小石头”,而现实中“小石头”是程砚秋曾经的艺名,这一艺名与一位梨园前辈颇有渊源,“石头”是梨园前辈陈德霖的小名,有“老夫子”之美称的陈德霖(1862-1930),清末京剧青衣演员,原名陈鋆璋,字麓耕,号瘦云,又号漱云,艺名金翠,小名石头。陈德霖以唱工著名,表演上沿用老派青衣传统规范,世称“陈(德霖)派”。当时的名旦王瑶卿、尚小云、程砚秋、王琴侬、王蕙芳、姜妙香、梅兰芳、韩世昌等均拜其为师。程砚秋甫一出道,即有名角风范,被誉为“小石头”是对其天赋条件的极高赞誉。电影中的“小石头”尽管不是蝶衣,但稍具戏剧常识的人一定会想到程砚秋的。
巧合的是,程砚秋师傅荣碟仙之“狠”绝对可以媲美电影里面的“狠师傅”,荣蝶仙是唱花旦、刀马旦的,在清末入长春科班坐科学艺。程砚秋拜师的时候,荣蝶仙二十多岁,正搭班唱戏,同时也带几个徒弟。程砚秋的第一个艺名程菊侬就是他给起的。早年培养戏曲演员,不外三种方法:一种是出钱请教师教戏,先投资后收益,多是家道殷实的梨园子弟。因为出了钱,教师比较客气,学生不太受罪。梅兰芳就属于这种,他靠祖父梅巧玲的余荫,家道也还不错,才请得起老师。采用这种方法的是少数。另两种方法是进科班学艺和“写给老师”当“手把徒弟”,这是多数,大部分是贫寒子弟,既谋衣食,又求技艺。这后种方法对学生很残酷,等于是卖身奴隶。尚小云是三乐科班出身,程砚秋是“手把徒弟”,荀慧生则先是“手把徒弟”后又入了科班。“手把徒弟”是由师父个别传艺。这比科班更黑暗。拜师时要立文书字据,规定年限任打任骂,生老病死、觅井逃亡,师门概不负责;学徒期间,演出收入全归老师。学生学艺之余,还要兼做师门中各种杂务,伺候师父师娘,抱孩子、打洗脚水、倒夜壶等等。学戏有个不成文的说法,讲究不打不成材,师父对徒弟很少有不粗暴的。程砚秋入师门时还是个孩子。偏偏遇上了荣蝶仙——一个极为残暴师傅,荣对徒弟十分凶狠,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小小的菊侬学艺中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一次,刚练完早功,荣蝶仙马上让他吊《宇宙锋》的唱腔。琴师是按老方法拉的,他开始有点发蒙,一时张不开嘴,荣蝶仙大怒,立时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由于刚练完撕腿,血还未缓过来,一顿毒打,血凝聚在腿腕子上,留下一个淤血疙瘩。直到二十年后,才在德国动了手术,去掉了血瘤,可心灵上的创伤怎样才能平复呢?电影里,科班里童子们练功的苦与难程砚秋都经历过,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电影里葛优饰演的袁四爷,让人不由自主想到袁克文、张伯驹、齐如山、罗瘿公一干人等。袁克文是袁世凯二公子,他唱昆曲,玩古钱,结文人,风流儒雅,名士风范,电影中袁世卿之名颇合其身份。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算起来和袁克文是表兄弟,他一生酷爱京剧,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成为技艺精湛、内行艺人均极倾慕的名票,电影袁四爷的身上也有他的影子。袁四爷身上无疑还有着齐如山和罗瘿公的影子。齐如山生于清朝光绪三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日(1877年12月12日)。齐如山家为书香门第,世居北京。19岁时,齐如山入同文馆学习德文、法文、俄文。庚子事变爆发后,齐如山辍学经商,几年时间便已积累了一定家业,设商号“义兴局”于京师。他曾三度赴欧洲,在欧洲期间,闲暇之时曾观赏欧洲戏剧,十分喜爱其写实风格。归国之后,齐如山在京剧业者的公会正乐育化会讲演,并撰写《说戏》一书,内容均为“介绍西方戏剧的长处,贬抑我国戏剧之不进步”。1913年,齐如山在北京天乐茶园观看梅兰芳主演的京剧《汾河湾》,结识了梅兰芳。齐如山认为梅兰芳在这出戏中的表演有改进余地,便随即致信梅兰芳,其意见很快便获得梅兰芳的采纳。1914年,他成为梅兰芳的“缀玉轩”书房中的常客,被视为“梅党”领袖,甚至有说法:“没有齐如山就没有梅兰芳”。1916年、1917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间,齐如山与李释戡等人为梅兰芳编排了大量的新剧,其中《霸王别姬》便是一个代表,最初这出戏是由清逸居士根据昆曲《千金记》和《史记·项羽本纪》编写为京剧《楚汉争》(共四本),1918年由杨小楼、尚小云在北京首演。几年后,齐如山、吴震修参照《楚汉争》的故事,重新撰写了《霸王别姬》剧本,由杨小楼、梅兰芳于1922年2月在北京公演。此后,初始的两本精简为一本,遂成为梅派青衣的代表作。齐如山爱戏如命,这与电影中的袁四爷有一比,可不同的是,日军攻占北平后, 让他给电台主持戏曲节目,被其谢绝,从1937年至1945年,为了不同日本人接触,齐如山躲在家中著书,足不出户,写出了不少民俗书籍,其士人气节颇可称道。罗瘿公原与齐如山一样捧梅,也是“梅党”中人,罗瘿公于同治十年(1872年),生于顺德大良一个仕宦世家。其父为清朝翰林院编修。幼承家学,早年就读于广州万木草堂,与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同为康有为弟子。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的总统府秘书、国务院参议、礼制馆编纂等职。后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弃政从文,久居北京,以卖文卖字为生。罗是程砚秋的恩人和伯乐,他对程砚秋恩同再造。相比齐如山与梅兰芳的良朋益友之关系,罗对程犹如父子。袁四爷的身世及其对戏曲的热爱有罗瘿公的影子,但与电影中袁四爷不同的是,罗在程刚成名时即去世了。电影中,程蝶衣之于袁四爷绝非单纯的欣赏或者玩弄,袁四爷也非单纯的知音或者捧角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原本就不单纯,梨园中人在戏和现实之间游走,就更难以说清了!
电影里有这样一幕:1945年,日本投降。蝶衣在台上唱,一群当兵的在下面起哄,拿手电筒乱照。小楼上台来:“各位老总,这戏园子里没有拿手电筒晃人的规矩,就连日本人也没这么闹过。大伙都是来听戏的。都请回座,听戏吧!”句句在理,不想台下又传来:“好是好,可就有一样,替日本人说话就是不行。大伙打啊……”混乱中,菊仙肚子里的孩子没了,蝶衣也被带走。因为给日本人唱过戏,因此获了“汉奸罪”!庭审中作为证人的袁世卿出庭作证蝶衣是被逼被打才为日本人演戏,而程蝶衣在自我陈述中矢口否认日本打自己。?碍于袁四爷的面子和社会地位,法官暗示程蝶衣:“你有义务和权利用事实来证明你清白的人格。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再做一次陈述。”程蝶衣竟然这样回答:“青木(逼他唱堂会的日军军官)要是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国去了。你们杀了我吧!”程蝶衣活脱脱就是一个视戏如命,视死如归的艺人。而在现实中,京剧艺人涉汉奸案的颇有几位名角儿,像马连良先生就因为去给溥仪唱过堂会,抗战胜利后被逼出走香港。另有一位为“汉奸案”所困,像极了程蝶衣的艺人,那就是程砚秋的私淑弟子新艳秋,这一幕戏中,程蝶衣几乎就是新艳秋的化身。新艳秋曾两次身陷囹圄,且都与汉奸有关。1930年代,从程砚秋那里成功偷艺“挖墙角”之后,新艳秋跻身四大坤旦,被称为“坤伶主席”,红极一时的新老板自然也被很多政客高官所惦记,后来汪伪政权大汉奸曾仲鸣便是其中之一。1930年,汪精卫前往北京,与阎锡山等人讨论所谓的“扩大会议”,曾仲鸣作为汪精卫秘书陪同前往。新艳秋作为北京戏曲界当红人物,有机会参与接待汪精卫一行,曾仲鸣第一次见新艳秋,便被她深深迷住了。曾仲鸣年轻时曾旅居法国,受到法国艺术文化熏陶,对艺术鉴赏自视甚高,年轻靓丽且艺术造诣匪浅的新艳秋,在他眼中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艺术品。二人见面当天晚上,北京方面就有人撮合曾仲鸣前去造访新艳秋,两人的关系正式确立。曾仲鸣为了捧自己这位新欢,每天去戏院捧场,豪掷千金而不惜。在一次堂会中有一个环节是每人点一出戏,曾仲鸣点了一出《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是梅兰芳的拿手戏,并非程派擅长,这出戏霸王的表演者是杨小楼,在当时被称为“武生宗师”,他的霸王只陪过梅兰芳这位虞姬。曾仲鸣这个行为意味着在向其他人宣告,新砚秋和四大名旦有着同等地位。一年后,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长,曾仲鸣成为行政院副秘书长,他派人将新艳秋从北京接到了南京,几乎成了曾仲鸣的笼中雀。后来新艳秋返回北京,不久就得知曾仲鸣另寻新欢,正伤心时,被刚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缪斌瞄上了,缪斌逢新艳秋演出必然到场,甚至每日都包很多好票送人,请大家一起去捧新艳秋的场。这让他老婆醋意大发,一天在剧场正看的津津有味,突然发现其妻出现在戏院里,害怕河东狮吼的缪斌匆匆溜走,恰好有位关医生与新娶的姨太太见有个很好的座位空着,高兴地坐了下去。这位医生也戴眼镜,跟缪斌轮廓很相似。舞台上,新艳秋刚唱一句“来至在都察院举目向上观……”“乓”的一声枪响,这位关医生倒地身亡当了缪斌的替死鬼,原来缪斌勾结土肥圆,早就成了爱国志士暗杀对象。枪击案之后,新艳秋被逮捕入狱,后经川岛芳子搭救才得出狱。后嫁烟台市长邰中枢,抗战胜利,邰以汉奸关系,身入囹圄,新艳秋也因与川岛芳子关系过密而收押。她二次如何出狱,已有资料甚少提及,无从考究。民国报人喻血轮在其《绮情楼杂记》中哀叹:“回思畴昔红氍毹上,万人倾倒,王孙少年,求一亲芗泽而不可得,今则门前冷落,不复为人眷顾,美人摇落,徒自嗟命薄!”新艳秋前半生大红大紫,后半生落寞孤寂,其命运起伏着实令人唏嘘。电影中,程蝶衣抗战前后一段经历庶几类似新艳秋,文学源于生活大致不差。
电影里程蝶衣是一个十足的悲剧,现实中,多少艺人也曾经历过他的悲催,四大名旦梅、程死得早,没赶上“文革”,逃过一劫,尤其是程砚秋先生,以他的个性,活到“文革”其命运不敢想象,尚小云先生、荀慧生先生在“文革”中均遭劫难,可做旁证。更有一人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程蝶衣,那就是曾经的“平剧皇后”言慧珠。言慧珠生于1919年的言慧珠,是京剧言派创始人言菊朋的女儿,她先学程派,后拜梅兰芳为师,是梅派弟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曾经三次自杀,前两次均获救,而第三次却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关于言慧珠的自杀,其子言青卿在书中写道:“1966年9月初的一天,一大帮人又进入了华园11号的小楼(言慧珠家),抄家持续了几乎一天一夜,他们把言慧珠藏在花盆底下、日光灯管里的金条,都抄了出来。藏在瓷砖后面的美钞也没逃得了,连镶嵌在床架上白金也被挖走……言慧珠看到如此惨状,顿时瘫倒在地——没有感情了,钱还可以让人活下去,但这次,钱都没有了,她彻底绝望了……那天晚上,她在二楼的浴室里悬梁自尽。第二天早上,遗体被抬走的时候,俞振飞只来得及给她穿上一双玻璃丝袜。”
行文至此,电影里一些画面不由自主在眼前交替出现段小楼在红卫兵的拷押下亢奋地喊着:“他是个戏痴戏迷,戏疯子!他是只管唱戏,他不管台下坐着什么人,什么阶级,他都卖命地唱,玩命地唱。”
而面对疯狂的人们,蝶衣几乎语无伦次了:“你们都骗我,骗我!”“我也揭发,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井颓垣。”悲愤地指着小楼控拆着“段小楼,你天良丧尽,狼心狗肺,空剩一张人皮了……报应啊报应!我早就不是东西了。可你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能不亡吗?”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啊,在这样的批斗会上竟然还惦记着京戏!
完了,疯了,全疯了!
血和着泪,分不清真假,辨不明黑白。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