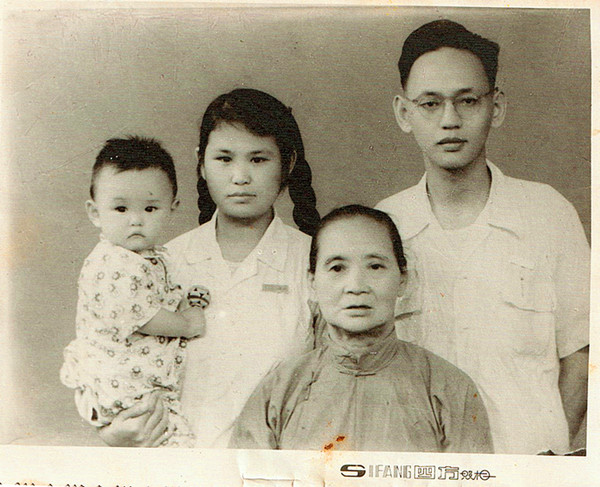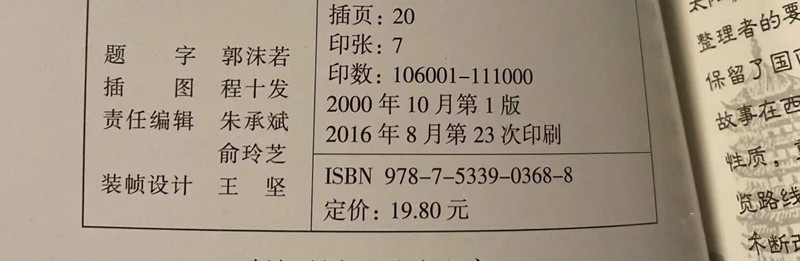过去的几十年,随着国家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产生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资源型城市,而且这类城市大多聚集在西部地区。
其实,没有人不知道,任何地方的地下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的,也没有一个矿区是可以无限期开采下去的。那么,当资源真的枯竭的时候,这些城市还能活得下去吗?
阜新:绝望中的突围
从1897年挖出第一锹煤开始,到1997年,辽宁煤炭重镇阜新市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开采历史。所有资源型城市应有的惊喜与辉煌、繁荣与景气,它都曾有过。
然而,到1998年,因为资源接近枯竭、煤矿从十多年前就开始接连报废,阜新矿务局已经被亏损拖到了绝望的边缘,开始动员局内职工提前退休,退休后可领取300元退休金。
仅仅两年之后,整个矿务局只有阜新最大的海州煤矿在做寿终之前的最后清理,大量矿区职工没班可上,没钱可领,连下岗通知和待遇也没有,只有彻底失业。
“九五”以来,阜新市GDP年增长率仪有2.7%,比全国GDP平均年增长率9%低将近7个百分点,去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比全省倒数第二名朝阳市少了60个亿,全市有19.98万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全市人口的1/4还要多。难怪阜新劳动培训服务就业公司总经理冯广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全省1.4%的GDP养活全省4.6%的人口,你说阜新怎么过?”
对于一座几乎不再有任何经济增长能力的城市来说,负担着1/4处于生活“警戒线”以下的失业人口,真的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经济转型,缓解压力,迫在眉睫。在阜新市的多方呼吁下,去年年底,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落实转型方案。
今年3月正式实施转型方案的阜新市委,向全市下岗失业人员发出动员令∶向周边12个乡镇的农业示范园区疏散和发展。随后三年内,将有四万多工人身份的农民,也就是说,这座工业城市将成为一座农业城市。
然而,转型能否成功?现代化农业经济是否就是阜新的出路?还很难说。
大同:不敢想像的未来
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会有所设计,对自己的家园都会寄予希望和憧憬,然而,山西省大同市的居民没有,他们有的只是悲观与茫然、落寞与脆弱……因为,他们在自己居住和生活着的这座城市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严格意义上讲,这座拥有280万人口,全球产煤量最大,年产量最高时达到8606万吨,真正堪称煤都的城市,并不像阜新那样到了彻底无矿可采的程度。目前,煤炭工业仍然是支撑大同经济的顶梁柱。只是已经摇摇欲坠、穷途末路。“调整产业结构”和“没有钱”是近年来这座城市各级领导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这座城市陷入尴尬和两难的关键所在。
去年,大同市民之间到处传播着一个消息:为了开采城市地下的优质动力煤,整座城市将迁址新疆。一时,笼罩在传闻中的这座城市,到处弥漫着疏离的气息、末日般的放纵和莫名的兴奋,人们的日常生活得过且过,不再对未来做任何打算与设计。
山西籍“第六代领衔导演”贾樟柯,去年在大同拍了两部纪录片《公共场所》和《任逍遥》,前者记录的正是一群面临迁徙者的状态,后者讲述的是一群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而贾正是凭《任逍遥》惟一入围去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华人导演。
尽管大同市政府被迫公开辟谣,市政府副秘书长说“没有听说过大同要搬迁的事”。其他官员也说传闻纯属空穴来风,但谈到大同未来的发展,却仍无定论与良方。
早在1985年,时任大同市市长的王玉军就曾向市委常委提出过:“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大同煤炭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党委和政府,应充分考虑将来的替补产业。”如果当时调整产业结构或许正是良机,但是,当时大同煤炭正炙手可热,王玉军的提示没有引起重视,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考虑那么长远的事情,而且,没有人会想到能源产业也有衰落的时候。
然而,今天,尽管煤炭储量尚有几十年的可开采期限,但末日般的生存危机已提前降临大同市的头顶。在新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曾经紧俏的动力资源——煤炭已经沦为一般商品,而且随着西部地区更多矿产资源的开发,煤炭市场早已由当初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的格局。在日渐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携带着多年来强力开发遗留下来的无法卸却的重负与后遗症,缺乏竞争力和不断丧失生存空间的大同市煤炭工业,已经无法支撑和维持这座城市的生存。
直至今天,大同市高层之间,仍然存在着“调产”和“固守煤炭”两种思路和意见。
调产,已错过了最佳的历史机遇,先不说转向何处,仅仅大笔大笔的转型投入,对于财政吃紧、银行惜贷的大同市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拦路虎。
转型无望的大同市只好继续向煤炭要饭吃。面对市场对燃料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传统的洗选煤工艺已经落后和濒临淘汰,今年,大同市投入8844万元的技改资金,完成了1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水煤浆项目,因为这一洁净燃料已有可靠输出渠道,大同市将最后的赌注押到了这里,正在努力实现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目标。
然而,水煤浆能救大同吗?它果真是大同的“新生之路”吗?或者,根本就是在做最后的疯狂透支?
如此没有办法和看不到明朗前景的城市,老百姓怎能不悲观和茫然无措?
铜川:在焦虑中寻梦
铜川,这座曾被誉为渭北“黑腰带”上一颗明珠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与上面两个城市相比较,可谓动手较早,距老城25公里处、累计投入达十多亿元的新区建设,动工六年来,虽进展缓慢,但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市政府也已迁入新址。人们梦想着、希望着弃掉那个没有了资源的破落无望的老城之后,能够在这里再创辉煌,形成一座新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然而,美梦能否成真?仍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陕西经济来说,铜川功不可没。
铜川是陕西于1958年最早设立的地级市,面积3882平方公里,人口82.28万,煤炭储量30多亿吨。据考证,铜川产煤历史可上溯到汉代,距今2000多年,近代大规模开发也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探明或正在开采的矿产资源有煤、油页岩、水泥灰岩、耐火黏土、陶瓷黏土等四大类
20余种。
建国后,国家对铜川的煤炭开发和建材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起了西北最大的煤炭矿区和当时亚洲最大的水泥厂,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建材工业基地。
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铜川原煤产量占到陕西煤炭产量的70%以上,整个陕西省的工业发电主要依靠铜川矿区供煤。70年代开始,煤炭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原煤产量占全省的85%,最高年产量达770万吨。除了煤炭之外,建材和铝业也是铜川市的支柱产业,当时铜川的水泥产量占全省的83.8%,电解铝占100%,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40多年来,铜川累计为国家生产原煤3亿多吨,水泥5000多万吨,电解铝30多万吨,不仅为陕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这些产品还远销东部沿海,并为著名的三峡工程、京九铁路、亚运会工程等做过直接贡献。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座城市由于资源枯竭、优势弱化,而渐趋式微,经济迅速下滑。到199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2.6%,地方财政收入只有全省总额的1.68%,在全省10个地市中,综合经济实力排到了最末位。
1999年底,铜川矿务局于1957年最早建成投产的、西北五省第一座现代化矿井三里洞煤矿停止生产,2000年按照国家政策正式破产。同时破产的还有史家河和李家塔两个煤矿。这一年,还关闭小煤窑273个,压缩煤产量287万吨,财政收入减少60%以上,全市有4.8万下岗工人,陷入了再就业无门、生活无着的困境中。
而到今年年底以前,桃园和焦坪煤矿两个主力矿井也将因资源枯竭马上关闭,几万名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又将加入贫困和失业者的行列。目前,铜川市有人口87万,市区37万人口中,就有近26万人是煤矿职工及其亲属。
铜川这座曾为陕西经济立下汗马功劳的城市,已经矿竭城衰。
早在十年以前,铜川市就为今天的结局忧心忡忡,不断从农业、旅游业等各条途径上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探讨铜川问题时,省内外经济专家们曾提出过许多观点和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全面提高铜川的战略地位,使其由一个矿业城市转变和提升为中心城市。
1993年11月,陕西省政府批准铜川市在远离老城的地方建设新区,并享受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切优惠政策,一座梦幻般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在向铜川市民招手的时候,一般市民心中尚无概念。但是,随着铜川矿务局在黄陵县的建矿投产,90年代中期,一度关于黄陵将划归铜川,铜川将迁市黄陵的传闻很盛,人们以为那个梦幻城市将在黄陵。
不管怎样,铜川的败落景象已是大势所趋。
1997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将铜川市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八个试点城市之一,这是西部地区惟一列入试点的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大大增加。
1998年4月,铜川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入支持“中国21世纪议程”能力建设的试点城市之一,该项试点在国内只选了三个城市。
那么,已初具规模的铜川新区,是否可以使这座城市“焕发青春,重新振作”?
就目前人迹寥落、入住人口非常有限、投资企业更是寥若晨星的境况,还看不到人们期望中的景象。有城无市,同样是一件让人焦虑的事情。
有人对铜川能否担当起渭北中心城市的重任提出疑问,理由是,其辖区内只有耀县、宜君两县以及王益区、印台区两区,总人口不足百万,“充其量是一个大县城”,而且经济实力太弱,在陕西经济发展中处于“南遗北忘”的尴尬境地,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西安的服务半径看,其城市定位只能是西安的卫星城市,很难自成“中心”;
还有人认为,花十多个亿,起一座命运难测的新城,有些冒险和划不来,不如将这些钱投入到老城改造和经济结构调整中。
而事实上,那些依旧窝居在被废弃的老城中的人们,他们并非不想住进新区,而是不能。多达26万的下岗失业工人及其家属,连生活都成问题,怎敢梦想迁居?何况冷清的新区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梦,近在咫尺,又何异于远在天涯?
让历史告诉未来
目前,在全国400多个单一结构的资源型城市中,跟阜新、大同、铜川情形相同或接近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多达近百家,都在焦虑不安地探索转型和救市的新路子,但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例可资借鉴的成功典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跟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开发的统一管控、环境保护、利益分配以及城市规划考虑不周都有关系,但是,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探测开采的新矿区,就一定能避免相同的命运吗?
历史,从来就是未来的老师。如果这些曾经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无比辉煌过、今天又因为资源的穷尽而无限凄凉的城市,仍然不能惊醒同样因为资源而正在辉煌或者即将走向辉煌的新城市,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废城”在明天出现的时候,谁还有资格怪谁吗?
原载《新西部》2002年第七期
胡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