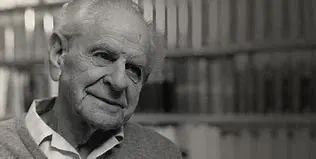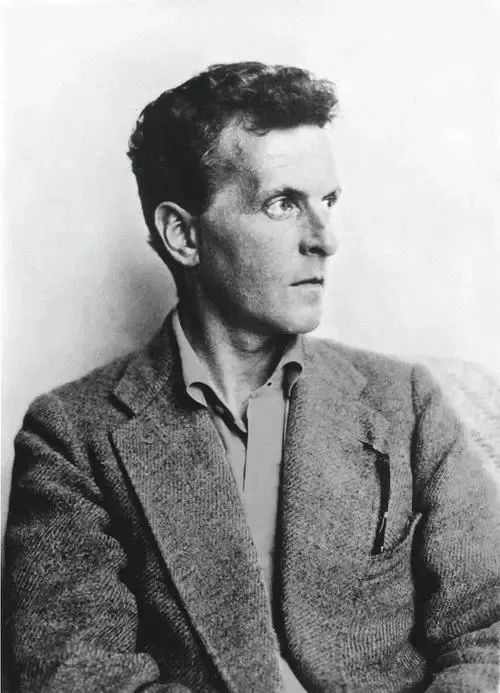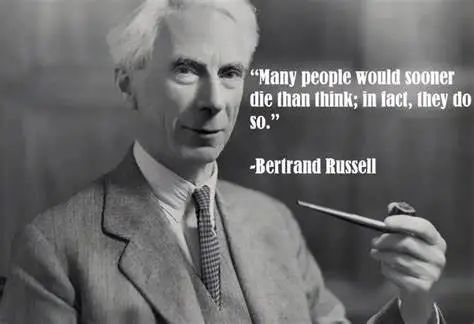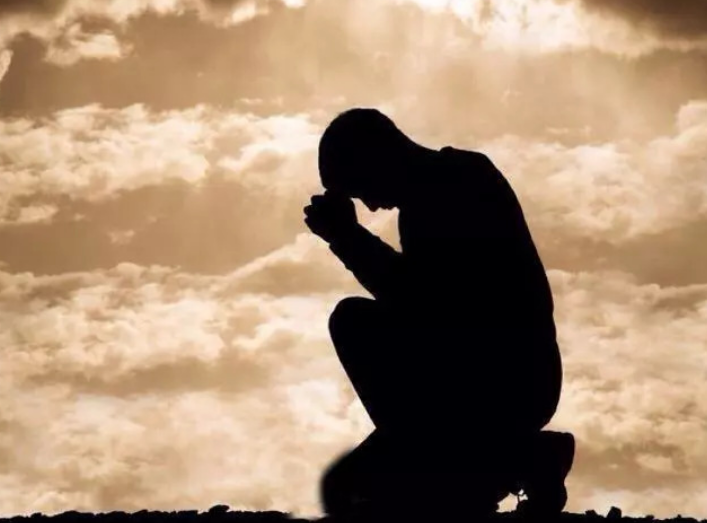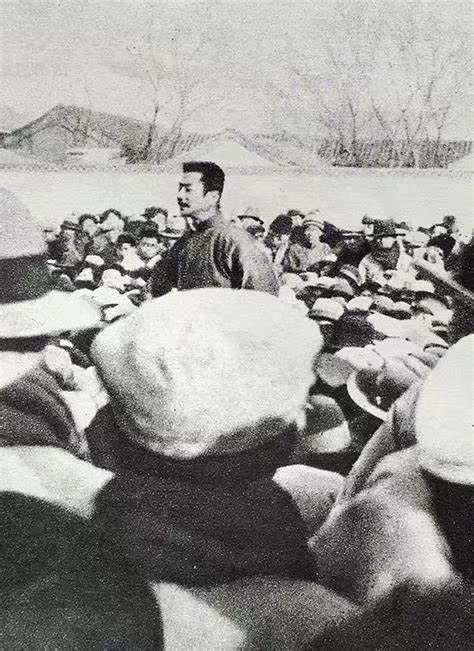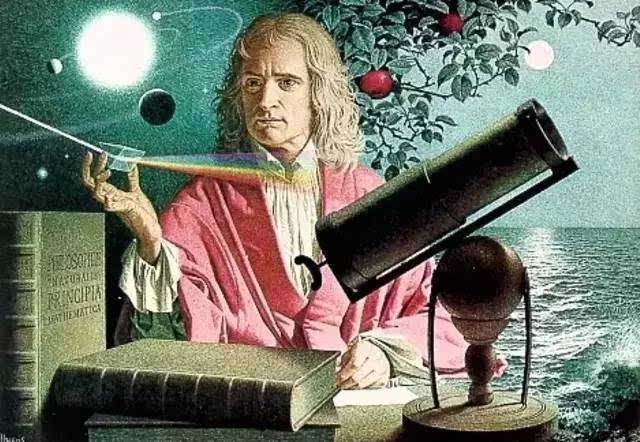不过,那次访问,波普尔差点接受了剑桥大学道德科学系的学术资助,仿若如此,波普尔就会更早地与维特根斯坦短兵相接。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1946年那次著名的“吵架”事件,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叙述这一事件,标题是“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副标题为“两位大哲学家十分钟争吵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当然是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次级主人公是伯特兰·罗素,这也是三位大哲学家第一次聚在一起。书中还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了将近30位见证者,他们大多是维特根斯坦的门徒和追随者。
卡尔·波普尔
其实他们是老乡,都是维也纳人,甚至他们的住址都相距不远,生活半径也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维特根斯坦和他的“维也纳小组”如日中天的时代。在大学,在咖啡馆,甚至在家庭客厅里,人们热烈地讨论,什么是哲学的真正命题,以及有无哲学,或者根本就一场语言的游戏。
这一切,波普尔不可能不知道。
但波普尔可能是那个年代自始至终清晰的反对者。他早年读过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在寻求一个界限,就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线,波普尔认为这个界限不难界定,他认为他找到了一种方法,他的分界标准胜过他们。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一切的科学理论都具备假说和猜想的性质,界定他们的标准就是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
1946年10月25日,波普尔与维也纳哲学小组终于迎来了短兵相接的时刻。他接到剑桥道德科学社秘书的邀请,去宣读一篇关于“哲学疑难”的论文。地点在国王学院吉布斯楼R·B布雷斯韦特的房间里,布雷斯韦特是这个房间租户的名字,他是一位教师,这个房间正确的名称应该是H楼的3号房间。
国王学院的吉布斯楼是一座庞大而庄严的古典式建筑。从街道、国王广场方向看,H3在楼的右边,一层。走向一段没铺地毯的木制楼梯,通过没有装饰的墙面,那个冬天,来客的脚步声显得凄凉而惊心动魄。
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H3房间的壁炉旁,所以在数十年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中,壁炉是个主要论题。壁炉四周由大理石包围着,上面是木雕的壁炉架,长期的烟熏火燎使得铁制的壁炉显得又小又黑。当时的取暖方式依然依靠外面生火,中央取暖和洗浴设备直到1947年才安装。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有人观察到,聚集在煤气管道中的水结了冰,堵塞了管道。
正常情况下,尽管有许多杰出的演讲者,道德科学俱乐部的听众大约只有15人。但是就波普尔演讲来说,听众明显要多些,大约30人。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涌进来,找到他们可以找到的位置,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维特根斯坦研讨班上的成员。尽管那时候他们还是大学生、研究生,据《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的作者考证,他们后来大多数都成为有名的哲学家或科学家。
很明显,“哲学疑难”问题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这一观点背后是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语言的疑难。这一命题恰好是波普尔最讨厌的东西,所以他决定讲一讲到底“有没有哲学问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946年十分钟的“吵架”事件几乎成了一个罗生门,数十年来众说纷纭,波普尔在自传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波普尔一开始就用诙谐的口吻说,在接到秘书关于“哲学的疑难”的邀请中,他感到惊异,因为写请柬的人已经隐含地否认了哲学的问题,这已经在由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的争端中偏袒一方了。
这一开场白显然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不快,也许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大声地有点愤然地说:“秘书完全是照吩咐做的,他根据我本人的指示行事。”波普尔并没有在意,继续讲了下去。但听众中至少一部分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很当真,把波普尔的玩笑当作对于秘书的正式抱怨,后来的会议记录显示,就连秘书本人也这样认为,他还在记录中加了一个脚注:“这是写请柬的固定格式。”
波普尔继续说道,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所有人不假思索地采纳对许多或许是所有哲学问题的靠不住的解答,而这恰恰提供了当哲学家的唯一理由。
维特根斯坦又跳了起来,大谈特谈疑难和哲学问题之不存在。波普尔选一个时机打断了他的话,拿出一张准备好的有关哲学问题的单子。“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的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吗?”维特根斯坦驳斥说,这些问题是逻辑而不是哲学。波普尔又提出了无限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反驳说,这个问题是数学的。波普尔又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
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边,烦躁地摆弄着拨火棍,他发言的时候,举起的拨火棍就像指挥棒一样加强着他的论点,他挑战似地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波普尔回答:“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伯兰特·罗素
目击证人之一彼特·凯奇教授看到维特根斯坦走回椅子坐下来,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情,拨火棍落在炉床的砖瓦上,发出“啪”的一声,凯奇注意到房间的主人布雷斯韦特猫腰穿过听众,捡起拨火棍,似乎要处理它。不久,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带着愤怒,静静地离开了会场。
另一位目击者迈克尔·沃尔夫教授看到维特根斯坦摆弄着拨火棍,罗素介入了进来。维特根斯坦说:“你误会了我,罗素,你总是误解我。”他强调误解时,把“罗素”发音变成了“胡素”。罗素说:“你混淆了一些事情,维特根斯坦,你总是混淆一些事情。”
波普尔的学生兼好友彼特·蒙兹看到维特根斯坦突然从火中取出拨火棍,在波普尔面前愤怒地挥舞着,接着,罗素拿开烟斗坚决地说:“维特根斯坦,立即放下拨火棍!”声音非常严厉。维特根斯坦听从了,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走出去,门在后面砰地一声关上了。
发明了“图尔敏论证模式”的斯蒂芬·图尔敏当时正坐在离维特根斯坦仅6英尺的地方,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件发生,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关于波普尔对哲学无意义的反击和举出的各种例子上。不过他说,实际是在维特根斯坦离开后,他听到波普尔讲了拨火棍的原理:“一个人不该用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
还有一位叫沃特金斯的教授在收到时代文学副刊的挑战后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在听到拨火棍原理之后离开的,显然,他是被波普尔的玩笑激怒的,如果说他在玩笑前离开,在逻辑上说不通。
波普尔在自传中说,“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是一句玩笑话,意在激起维特根斯坦关于真正哲学问题的讨论,根据波普尔宣讲论文就是“挑战”的一贯观点,笔者相信这一点。不过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波普尔显得相当惊讶,维特根斯坦居然看不出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事后波普尔也进行了反思,他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可能觉察出他在开玩笑,正是这一点使他大为恼火。房间的主人布雷斯韦特后来称赞说,波普尔是唯一敢用维特根斯坦打断别人的方式打断他自己的人。我怀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原发《书屋》2022年第5期)
原载 葛陂小记 2022-05-21 06:30
张祚臣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