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八月十八,刚到湖州任的苏轼被捕,押解御史台监狱审理。“乌台诗案”让汴梁城热闹了一阵子。至十二月二十九定谳,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苏轼走出大牢,一身倦容,精神劲尚可,笑眯眯顶着四十多岁的人不该有的花白头发,回望御史台周围森严高大的柏树林,冲黑压压的乌鸦窝和无精打采啄翅尾的寒鸟挤挤眼:死劫躲过,重见天日,却难言吉凶,但赖活总比死了好。正值年尽岁除,按规矩,谪官不可滞留皇城,解差一老一少,一前一后,像护卫,押苏轼往流放地黄州打马飞驰,苏轼长子苏迈紧跟三人后面。出开封城时,朔风吹来元丰三年大年初一的早晨。
正月十八过河南蔡州,路遇大雪。白花儿从压低的云层扑簌簌飘落。个头大的挂上眼睫毛,手臂扫才会掉到泥地。马鼻喷洒热气,不停咀嚼,看似恨得牙痒,又像诅咒。白茫茫的旷野一行人如黑菇,缓慢移动,黯然耸立的树梢由灰黑变雪白。不一会儿,北风啼嚎,像有人在阴寒处吹唢呐,声音破裂,不成曲儿,单冲他们。铺地雪花起了扬尘,旋转呼啸,不离四人左右,白生生的地面踩上去更泥泞,举步维艰。
“老苏啊,俺们跟你遭罪。”老差役梗直脖子,似乌鸦扭头,眼神却如猫头鹰,一望而知是练家子。苏轼听到抱怨,并不在意,雪天的动静比牢狱的死寂强多了。他闻到自由的滋味,空气凉了点儿,却很畅快:“新开年如此暴雪,着实不多啊。”他自语,也是回老差役的话。话一离口即冻成冰片,被狂风吹走。不知多少已死的会在苦寒中复活。
过新息县城,雪自然小了,等到分界豫鄂边境的淮水,雪停了,天空如冻裂的壶底,漏下阴沉和水珠,渗入肌肤,比雪还冷。摆渡口一间茅屋,像个雪人蹲着。舢板船拴在岸边,一艘孤舟。过河费加倍。老差役亮出御史台的牌子,船家不再说什么,载人马横渡。淮水宽阔,水流不急,却很硬朗,木船颠簸如撞石壁,砰砰作响。老少差役缩于船尾,手抱船家的水烟袋,你一口我一口分享温暖。苏迈坐船舷一侧,神情坚定,很让苏轼心安。苏轼坐另侧,盯望一带黑水滚滚而去,诗句涌到嘴边,却不成行。他想学古人端立船头,后背双手,宽袍大袖随风飞舞,目视对岸馒头般的山峦,思绪飞越古今,呈潇洒状,无奈木船起伏得厉害,他没站直的功夫。轻叹一声,这声音落去心里,只他自己听得见。苏轼心乱如麻,尤其坐凛冽的河水上,有惊弓之鸟的乱,有千里投荒的乱,有前程未卜的乱,有柴垛焚烧的乱,都似眼前翻滚的淮水。上下左右灰蒙蒙的天气,像只倒扣的铁锅,把他完全罩住了,前不久呼吸到的自由空气稀薄起来,逼得他用力鼓荡胸脯。就在他沉入黑暗即将崩溃想呐喊时,眼前出现一条山谷,峡谷弯曲悠长,存太古之静。谷地多巨石,岌嶪相依,石间人高的灌木不因微寒而不绿。一支队伍进了富春江边的这条山谷,骑马行于中间的是苏轼。熙宁六年,也就是七年前,王安石新政中,苏轼任杭州通判,反对新政却不得不执行新政。正月下旬一天,微风细雨,苏轼巡按属邑富阳时被身旁峡谷清绝的景色吸引,越往深处走景致越与尘世不同,不觉半日已过。又行数步,几块圆石后,一棵樛曲之树斜伸几根枝子,开数朵白花,朝山径招手。苏轼闻到梅花香,跳下马来,直奔白梅。石后的梅树,主干竟有大腿粗,像个人半蹲着,露半个脑袋,只有如手臂的大枝搭靠石头凸棱上,举着几朵开放的白花,更多含苞在枝杈间,点着唇红的萼。苏轼喜上眉梢,大袖子轻拂过花朵,花瓣新沾的雨滴,惊慌之下垂落石槽,花香却被衣袂卷走。苏轼擒高衣袖,距鼻尖尺余,耸鼻闻香气。香气如丘,将他掩埋,顿时身轻脑明,仿佛重生一次。沉醉中,身后传来钝器撞击石块的响声,回身见不远一位老者,甩举镐头,一下一下开垦山坡上的荒地。身旁开垦过的,不到半亩,种了麦子。麦芽噙含雨水,正在返青。苏轼好奇,斜身下坡。老人头发全白,像惨败的白梅花,蔽身的衣服不完整,一条一片的,满是千疮百孔的破洞,光着脚,趿拉一双草鞋,脸上却不少汗珠子,重重地滚落地面。这一幕,苏轼瞧着脊梁骨发冷。他四处望望,只见雾障,不见村落。
闲聊得知,老人八十六岁,山下村子的,种了两亩地,收的粮食不够每年强派的青苗钱,于是上山开点荒地,好有口饭吃。苏轼无语半天,抓起老人磨出水泡的手,眼泪差点下来,心道:“安石误国害民。”他眺望绵延的山峦,说不出的愤懑。为什么不轻点对百姓下手?所谓新政,左右不过变着花样折腾百姓,盘剥生民,富裕了国家,贫穷了百姓,于江山何益?他招呼随从下马帮老人垦荒,搬走一块石头也是好的,至少让老人少弯一次腰。日已西沉,开出一片新田,嫩土散发梅花的清香。告别时,老人拉过苏轼的手,一再嘱咐:“别往前走了,回吧。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
透过七年光景,梅香在苏轼记忆中隐隐约约。他撩起衣袖,嗅了嗅,香气全无。“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豁然开朗。舢板破浪的速度明显快了。登上淮水南岸便是楚地,中原已远,无法相望汴梁。苏轼意识到,河北的一切人和事都被这一指流水阻挡了,与他是永别也未可知。
“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
鄂北关山层叠,云遮雾绕,细雨中瞭望恍如无路,近前才见一崎岖古道壁嶂间盘旋。老少四人至麻城黄土关,天色已晚,驿站打尖一宿。正月二十日晨,乌云翻滚,小雨飘飞,寒气却不似淮水之北那般逼人了,山风掠脸,频送春暖,四人有了说笑的惬意,不多会儿过仄狭关口,需下马牵行,边走边惊呼其险,仰视一线天慨叹,真个是行路难,恰似上青天。难字尚未落地,便闯入一片洞天。原来黄土关不过百十来米,连接一处开阔的峡谷,名春风岭,意指此处只一种风,一个季节,蕴含美好的心意。苏轼在谷口闭上眼,驻足挺胸,长吸一口甘醇的空气,四肢百脉一瞬间运转正常了。
谷地一溪,从山外折来,坠落中跌宕为瀑,弄出百鸟齐鸣的响声,在低处汇为大潭,鹅蛋状,因映照青山翠岭的颜色,反失了自身的清白,望去一团碧绿,很粘稠,流出峡谷时,才找回浅潺和透明。一溜梅树,或高或矮,或三五一簇,或单棵独立,排着队,斜生溪水对面,怒放白花,春风过时,晚开的送出香味,早开的花瓣陨落,飘荡着悠长,入了溪水,不知想被载去哪里。白梅在一谷青翠中,特别耀眼,像些碎了的镜片,闪烁隐秘的智慧。说来奇怪,梅树身下周边,除卵石和细沙,竟无杂木和荒草,如被净化,画上去的一般。执画笔的是春风岭自己。它还画了百年的榉树,千年的香樟,万年的藤萝……但苏轼视而不见,眼里只有梅花。
缰绳递给苏迈,山道旁取截枯枝,点着石阶,苏轼快步入谷,朝那些梅树去。苏迈从未见父亲如此慌张,心里着急又担心。老差役搞不清苏轼要干么,缰绳塞给年轻的差役,随苏轼下坡,踉踉跄跄,嘴里嘟囔着什么。梅树看似不远,其实有点儿距离。首先下个长坡,得离开石阶的路。随后绕过潭水,过片草甸,水草中隐约水洼。最后涉步溪水,看上去窄窄的溪流,足二十多米宽,粼粼湍急,深及膝盖。苏轼对老差役喊了什么充耳不闻,更不回头,一袋烟工夫趋至溪边,既不停步,也不脱鞋,下到水中,右手的枯枝探去身前,水下迈步,身子扭得像大鹅,难免趔趄歪斜。老差役追至水渚,不想去试刺骨的冰凉,干脆坐块石头上,大口喘气,目送苏轼过溪。
报春的白梅等在岸上,静默环视,像冷漠的美人。苏轼身后留下一串水渍的脚印,径奔单立的梅树而去。那是棵直脚梅,野生于此长达三百年之久,植株并无年龄所示的庞大,斜立向水,茎干弯曲,疤痕累累,通身亮黑,荒寒中依然疏瘦,近看不是美人,更似风霜尝遍的耄耋老人。苏轼停步仰视,缓缓闭上眼睛,张大鼻翼,一股凛冽的清香直入肺腑,淡而坚的香味从未闻过,让他感觉头晕。等他睁开眼,一片晶莹的花瓣飘落,花瓣小的可怜,无声无息,落在他脚下。他想俯身捡起,嗅那陨失之香,一低头的刹那,不觉清泪盈眶。他看见了自己。
苏轼整整衣衫,拂去风尘,仰面平躺直脚梅下,再次闭上眼,像具尸体,任梅香、雨滴、花瓣落到脸上身上。时光安静地扫过春风岭。
写于2019年
整理于2020年
作者简介:阿龙,高密人,生于1965年,大学新闻系毕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高密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散文专著《老家三部曲》:包括短篇散文集《发现高密》、中短篇散文集《夷地良人》和长篇散文《五龙河》。单篇(组)散文、诗歌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获第四届风筝都文化奖,第二届齐鲁散文奖。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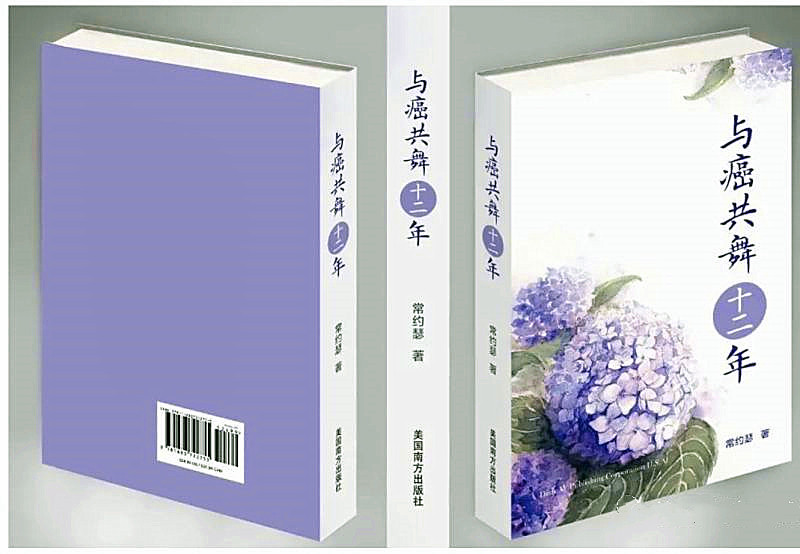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