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板弄
江南。三月。雨巷。
油纸伞。青石板。金缕梅。
走着的模糊的永远的时远时近不善言辞的回声。
谁在我身上,播种宿命?
窄一点的世界,多好。
光是采摘来的,经过筛选,因此稀疏。
而缘分,如果相遇,便不会绕行。
高高的砖墙,仅供月亮攀援,
石板弄的睡梦,只允许一颗星星读懂。
我站那儿,像风停歇。
可以学藤萝,不由自主地向上,
可以自己覆盖自己,可以重复。
可以抬起头看看流云,漫不经心地叹息,
可以不开花,可以落叶,可以折返。
可以回到二三十年代。可以再远一些。
悠长的石板弄,
像一缕线,像时间,
找不到头尾,扯不断。
像人生,像活在人生的人说人生,
断断续续,有清晰的兴衰和血肉模糊。
但石板弄是完整的,即使偶尔潮湿,偶尔忧伤,
每个段落是完整的,从古及今,头尾贯通,
你可以一直走,一直走,追赶自己和别人的背影。
即便石板弄始终一动不动。
青石,我相信它来自天堂,
用神秘炼制。我相信它来自天堂的某座花园
或天街,并在我无法参与的朝代,
到达江南,到达心海。
我尝试爱上这些石头,
或者已经爱上。
我爱石板弄的石头,
如果星星也是石头,
我爱不发光的石头。
因为石板弄的青石自天堂来,
躺在地上,没有光,很安静,
连神明也情愿站一站,
它们性格一致,
无光自幽,无声无息。
并非所有石头可以吞进胃里,
我倾情吞下的只有江南的石头。
石板弄的石头到达我胃部,
它不打扰我,只把弄巷的水珠擦拭。
它在明亮的喘息中种植苔藓,
穿上青翠的彩衣。
俯下身便可爱抚和亲吻,
很多年了,我因此固执且坚硬。
我总是赤脚走进石板弄,
就是这样,贴紧石头的魂魄,
清凉、平滑、柔软地上升,像洁白的云朵。
倚墙而立,窄的天高而悠扬,
仿佛回归了母体,
尚未萌芽的我的躯壳,
被呵护在光阴之中。
雨落的黄昏你们不要来,
只让我亲近。
我要霸占石板弄尽头斜进来发光的灯,
那是大片夜色为我撑开的伞。
伞下面飞来飞去的晶体,
我仰首展开的双臂,
谁说这不是一次际遇?
那束耳鬓厮磨的明亮,
分明照见难舍难分,
看吧,不计其数的水珠聚过来舞蹈。
并用潮湿,洗净自己。
假如,我是一本书,
假如我是从天堂的书架上掉落的书,
从时间的缝隙掉落在石板弄的书,
一定写满文字,
并刻就读不完的音符。
比如,下雨了。
巷尾的门洞,
我坐在那里看梅花。
很久以前,我坐在那里,
守着自己看梅花。
昨天的从前,
我看到,巷尾坐在我体内,
看石板弄门洞里的梅花看梅花。
并且望见石板弄和门洞
在梅花里,看梅花。
拙政园
一直不敢
在它面前舞文弄墨,
生怕念头一闪,
五百年的山水就要苏醒。
它们醒来,
江南的愁烟怨雨也会醒来。
像梅子黄时雨,
只要下,便不能停。
这里山水,
神明给蜻蜓
比给任何人的多。
它轻悠于荷叶之上,
伸展古典的长腿抒怀,
消解园林奥义。
我从它的复眼里,
看到流水及湖底的世界,
不只一个;
混沌与空寂中,
一尾游历的鱼睁大眼睛,
翻阅蜻蜓异变的思维和
荷风四面亭起伏不定的球状阴影。
而四方游众肩头,
端坐到此探幽的表情,
笃信的目光试图从拙政园的蜂巢,
分享蜜与痛。
那些俯身于蜻蜓翅膀的昨天,
在唇与齿的关联上飞行。
在拙政园的黄昏,
我遭遇叙述的艰难。
不是多少往事无法显现,
不是木芙蓉收藏一群花蝴蝶,
不是下垂的日照在花格窗的枝叶凋零。
难以叙述的将是蜻蜓、游鱼和我
注目的傍晚不会来临于同一时刻或
这个黄昏本不是我们共见的哪一个——
它至少有三幅面孔——
我们找不到协调歧义的语言。
绿树如烟,目光迷乱。
四季骨瘦如柴,却需要风水丰腴。
我坐在丑石之上,被反复修改,
满意的结果,在陌生人手中传递。
一个说典雅,一个说沧桑,
我手指景深处虚化的天泉亭芙蓉榭:
可曾留意一口古井是否枯竭?
在这里,我不会分得更多山水,
月光被山茶和杜鹃分食,
星星只会眷顾梅亭,
雨水和它跳跃的歌唱专情于芭蕉肥硕的身形,
玉兰向雪开,桃花独享泛红轩,
我抱紧一丛青竹,只晃落瘦削的影子。
听松风处的松,
已不是我能理解的松,
它们沉默在真实与虚幻之间。
“风入寒松声自古”,
当风铺天盖地卷起雪花,
天空下沉如冰封的湖面,
山水逶迤用僵硬呼吸,
它们却挂满柔软、明亮、沉静,
——在我出入的冬季,
悲伤守望古老的云朵。
风尘的脸在时光里苍老,
驱赶不走皱纹。
星辰睡在黑暗中。
灵魂沉疴,结为淤泥,
俗世喧嚣,驻留无望之上。
命运赐我机缘,我在其中衍生,
像红莲,恋淤泥,念流水。
一定有只手,
拧紧过时间的发条,
让尘土、愁绪、心灵、痛苦,
交织并穿越了密林和深渊。
成为暮光中麻木的
相似物。
成为意义偏狭的词语,
我无法触及。
历朝历代的隐士们,
是不是错了?
他们栽山种水,修竹剪梅,
莫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吟罢风霜,打马再来?
如若不然,这松风水阁,
怎会在我体内,涛起云涌,日起月落?
山不在高,一拳千仞,
心的高山在千里之外,还是近在眼前?
是了,阿猫阿狗尚可豢养,
山山水水树木花草怎可例外?
被豢养的文墨一旦遭了遗弃,就只有逃,
逃无可逃便圈块田地,弄些山水,
豢养自己——更信了南山不远,悠然可见。
藏志于物,纳美于丑,多么讽刺!
我看那蜻蜓忽然恼了,要斩青荷,却折断翅膀。
鱼也看得累了,闭上眼,沉入更深的黑处,送上一串气泡。
梦境停靠在昨夜的船头,
船头带走雾和一贫如洗的星斗。
安静的晨光里我过来告别,
拙政园又披上鲜艳的彩色,
宛如展开另一个梦。
一行又一行头颅,在地平线塌陷
缀云峰上,我在光明中消溶。
试着假设,时间耗尽,
最后一个人低头走出拙政园,
这唯一的人在离开拙政园的路上转弯。
它有没有关闭拙政园的门?
假设,它走到时间尽头,那一刻,
世界的大门会不会对它关闭?
如果假设成立,在两扇关闭的门之间,
它如何行走?能否返回拙政园?
这个人,不是王献臣,
就是陆龟蒙。
石湖
在石湖,我信任奇迹。
吴越两国都信任,
范蠡西施相爱的故事。
我相信爱情本就是奇迹。
我相信范蠡因偶然流落越国,
去苎萝山村却因必然。
在浣纱溪,遭遇西施属于偶然,
埋下爱的种子出自必然。
我信任一见钟情,耳鬓厮磨。
像历史中众多的偶然,
越王勾践击败吴王夫差纯属偶然。
也如许多必然,
必然地,范蠡携走西施,终老碧水青山。
换成你,也会这么做。
由于总有大的不善无法躲避,
比如战争,洪水,瘟疫,
比如难以改变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欺凌,
因此,人心积攒小小的善,
用于弱小和无助。针对范蠡和西施,
人们情愿让爱情击溃历史学考证。
范成大选择石湖,
而不选择其它的湖建造房舍,
因为他信任石头。
他用余生挖石采石,
用手用嘴清除淤泥,打磨棱角和凹坑,
让它们重现光阴的本质。
他匍匐于每一块石头,
尽全身之力雕刻,
他把用月光写成的诗,用阳光刻进石碑,
石碑一块一块立在湖边,
成了诗的碑林。
他刻完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
揉揉老花眼,看到的每个字都清清白白。
天蓝地绿,黑底白字,
我读他的我所见的全部,
手指碰触的每个字,
一枚枚一下下地盖着图章。
这时候,肩膀上多了件蓝紫色雨披,
下雨啦——
笑眯眯的老妇人,站在我旁边,
新摘的绿叶菜在她挎着的竹篮里跳跃。
行春桥下,
你一眼看到九个月亮不算奇迹。
但你如果连续三个
阴历八月十七子时至寅时
只有一个月亮才是奇迹。
曾经我每天经过行春桥,
每天不只一次。如此这般三年有余。
一直并非一般地相信我会看到石湖串月。
第一年,我手捧菊花,
守在子夜。月亮藏在云层背后,
天微明,菊花落入九个桥洞。
第二年,我折桂而来,信心满满,
眼见月亮偏向西方,串月时刻已近,
却见上方山顶飘来大片雨云,
一夜细雨打湿衣襟。
第三年,一桶桂花酿置于桥头,
对月饮酒,好不自在;明月如盘,清辉满湖。
环顾四周,竟无一人陪我共赏天赐奇景。
屏息至寅时,眼见一轮明月沉入湖底,
竟不见串月,莫非我曾醉酒睡去?
第四年……已别行春桥十余载矣。
想那串月也许串了十几回。
来这里的人相信这里有间屋子,
屋子足够大超出想象,
有很多门,每个人可以拥有一扇,
门上捏锁,每人一把钥匙,
可以打开任意一扇门。
属于每个人的门一旦打开,
满屋子都是黄金,取之不尽,
能拿多少取决于你拿走的本事,
还取决于八月十七这一天。
这一天,四方信众排队挤往楞伽山,
焚香烧纸伺候五通神,能不能拿到钥匙
视乎这位财神看中了谁,人们磕头祭拜,
渴望借到心里想还其实不用还的阴债。
目睹心满意足的人群下山,我替他们高兴,
由山下餐馆点吃的山珍海味推知,
他们找到了金山。
山青了,水绿了。
那条熟悉的路还奇迹般通往石湖,
没有名字的流水永远没有命名。
一支荷站在凝视我的阴影里继续呼吸,
蜻蜓又长出透明的羽翼,
路旁樟树依然环抱巨大的静寂。
在石湖,我终于学会并习惯了
漫长的循环和重复,
习惯了一面之缘的飞鸟,
湖边日渐衰老的水草,
天天相见最终成为陌路的石坊,
习惯了偶然的惊喜和爱情,
桥头沉默却永不疲倦的石狮,
终于习惯了别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
远离了石湖,
依然相信那里还有奇迹。
范成大继续写田园诗,
孩子们早学会了种瓜,
孩子们的父母们还学会了种豆。
范蠡又穿上他喜欢的白衣,
只是勿需再偷偷摸摸挽住西施,
他们的画舫终于来去自如。
我多年没找到的西施登舟石,
终于被远道而来的旅人捡起,
通报西施脚掌的尺寸和一米七五的女子无异。
陌生朋友发来“酒焖茭白”图片,
说这盘葑水清味产自石湖,
由此得知我走后石湖的葑草未停止生长。
只是不知给我披上雨披的老妇人是否健在,
据说她用苏绣绣好范成大的全部田园诗,
而我只记得她精致的绣花鞋
刚从田间走来沾染的新泥。
山癯水瘦,悠悠万事,
天镜阁在湖边望见它自己,
薄雾遮掩了渔庄,
睡梦中,炊烟轻缓,已翻过越城桥。
月亮再次偏去上方山,
拜郊台伫立的姑苏女子,如梦似幻,
弱风细柳,一黛远山,
谁在唱散曲评弹:
忆江南,风景旧曾谙。(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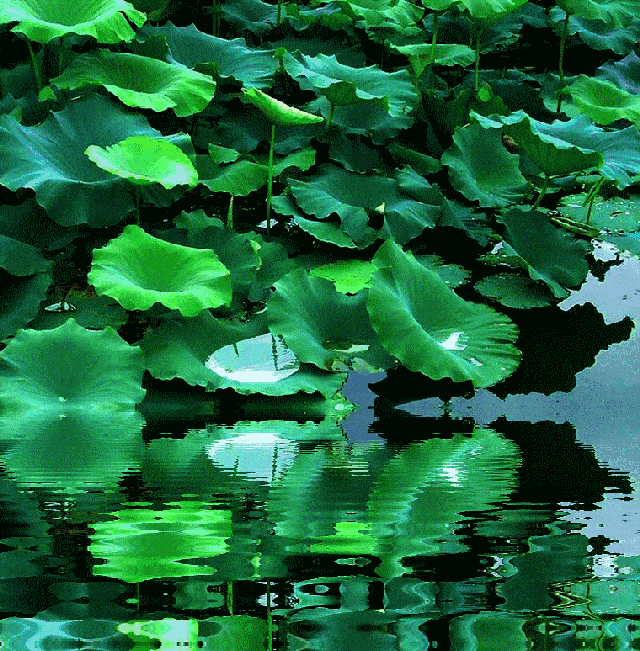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