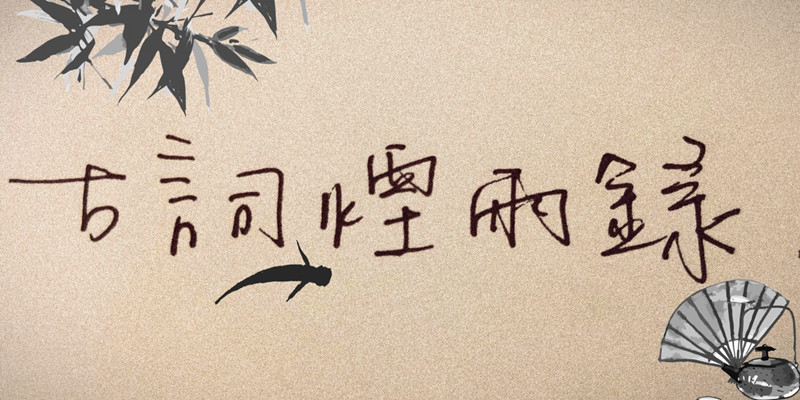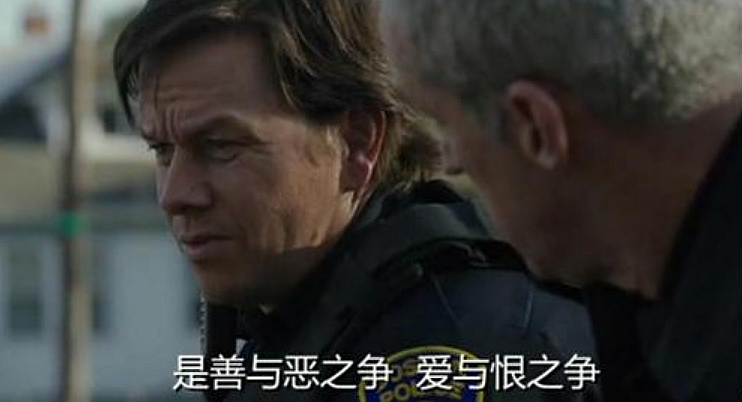这篇关于顾正秋与戴绮霞打对台的小稿,大多资料来自高美瑜女士的文章,特此说明,不敢掠美。
台湾京剧艺人淘金地
就单一剧种而言,台湾京剧观演风尚的基础奠定于日治时期,是由上海及福州传去的,营业演出清一色是海派京剧,并无任何京朝派剧团,海风俨然一股时尚潮流席卷台湾,不仅在绅商、文人阶层流行,亦以商业剧场公开售票方式受到群众喜爱,从1895年至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止,来自上海以演出海派京戏为主的京班超过40团,占日治时期来台演出戏班总数的三分之二。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战争期间一度消匿的京戏演出活动迅速复苏。从1946年元月报刊出现战后第一个复出的本土京班“京音宜人园”在台北中山堂演出,及至最后一个外省京班周麟崑“麟祥社”于1949年8月在台中国际戏院演出,战后初期四年内全省进行商业售票的演出团队,保守估计至少有23团。其中内地职业京班重启航程来台献艺,尤以1948年为多,如李少奎“新生平剧团”、曹畹秋“正气平剧社”、上海美猴王“张翼鹏剧团”、徐鸿培、海慧苓“海升京剧团”“张家童伶班”,本文主角顾正秋与戴绮霞亦在这年年底先后带团抵台,台湾商业演剧渐盛,被戏班视为是淘金的热门地点。
顾、戴青岛初“对台”
事实上,顾、戴二人曾不只一次对台争胜,第一回发生在青岛,第二次才是在台湾。有趣的是,从顾正秋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两次与戴绮霞对阵,一次轻描淡写地带过,一次是只字未提,其中意涵令人玩味。
1947年,戴绮霞在上海共舞台唱红,当时承包了青岛四个剧院经营权的麒派老生周麟崑,即邀请她到青岛华乐戏院担任头牌旦角,班底为周麟崑的“麟祥社”。戴绮霞,早年拜师“南方四大名旦”小杨月楼,后师从“花王”筱翠花(于莲泉)、工花旦兼刀马旦,擅演《大英杰烈》《小上坟》《红娘》《大劈棺》《红楼二尤》等,她扮相妩媚娇艳,身段轻盈飘洒,演技动人心魄,她演《大溪皇庄》《盘丝洞》还将流行歌曲融进去,她的戏一出场就能赢得捧头彩,尤其是《马寡妇开店》一亮相,赢得满堂好,很受青岛观众的喜受,当时青岛的戏迷有个口头禅“三天不喝茶,也得去看戴绮霞”,借着这个势头,1947年,30岁的戴绮霞在青岛当选为“平剧皇后”。
正巧,那年秋末,18岁的顾正秋率领“顾剧团”在徐州演出,青岛永安大舞台派人去邀她前往青岛献演。顾正秋在她的舞台回忆录中回忆:“(当时)麒派老生高百岁和戴绮霞大姐也在华乐戏院上演,因为他们是常驻青岛,我们两方面是相安无事。到了第二期,大会堂就邀了京角陈永玲来和我打对台了。”当时,青岛剧院林立,戴绮霞在华乐戏院、顾正秋在永安大舞台、陈永玲则在大会堂,另外还有光陆戏院、同乐戏院等。数家戏院同时上演,本来就具有竞争意味,对于戴绮霞,顾正秋认为双方“相安无事”,而据戴绮霞回忆,两人在青岛同时以自己的拿手剧目参与“剧后”选拔,戴绮霞以《马寡妇开店》夺得荣衔,当时竞争意味不可说不浓厚。顾与陈永玲则称“和我打对台”,顾氏真实想法虽无法得知,但可以作如下推测:其一,从年龄上相比,顾正秋相差戴绮霞整整十二岁,出版回忆录时,顾正秋定然会虑及戴绮霞同在台湾,不欲以陈年往事引起争端,而陈永玲则在大陆,可以不考虑这层;其二,顾氏或许会认为自己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校”,然所演剧码均遵循各京朝派名家指点的传统路数,因此与海派旦角并无直接比拼之处。而京角陈永玲则不同,尽管陈氏与戴绮霞同样以花旦见长,顾正秋专擅青衣唱工戏,可两人都具有名家嫡传之身分,他们之间才算是真正打对台。
顾正秋、戴绮霞其人
顾正秋(1929年10月5日-2016年8月21日)原名丁祚华,又名丁兰葆,生于南京,长于上海,干妈顾剑秋将她改名顾小秋,上海戏曲学校学戏,是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正字科学员,因此改艺名顾正秋,她入学考第一名,坐科六年期间得到学校重点栽培,各流派名家如张君秋、宋德珠、黄桂秋、魏莲芳、朱琴心,以及昆班“传”字辈艺人朱传茗先生,均曾受聘至戏校亲授其拿手剧目,而后更在校方安排下得拜梅兰芳为师,成为梅门入室弟子、梅派正宗传人。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顾正秋成名很早,1945年戏校甫毕业,即三度在上海“皇后戏院”与“黄金大戏院”演出营业戏,合作者纪玉良、李宗义和谭富英均为名家,而后自组“顾剧团”到南京、徐州、蚌埠及青岛演出,主次要配角多为上海戏校“正”字辈同学,蚌埠演出之后开始固定与胡少安搭档。在台湾被推崇为“一代青衣祭酒”,有“宝岛梅兰芳”之称。
戴绮霞(1918年-)出生于新加坡,其母艺名筱凤鸣,为髦儿戏班出身的河北梆子演员,外婆在新加坡经营梆子、京戏“两下锅”的戏班,自幼受家庭熏陶影响,7岁开始学戏便经常登台献演。初以武生、老生开蒙,向海派武生刘长松和文武老生张鹤楼习艺,奠定深厚的武功基础,尤擅各项翻滚扑跌功夫。使得她得以在三本《铁公鸡》中反串张嘉祥,使用真刀真枪对打、翻跟斗过城墙;在《三国志》中反串周瑜,最后“周瑜归天”时踩厚底从二或三张桌翻下,毫无所惧。戴氏13岁正式改唱旦角,师承京剧花旦小杨月楼(杨慧侬),由母亲亲自监督习练蹻功。1937年回国,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头二本《虹霓关》,通过上海闻人黄金荣考核,顺利进入黄金大戏院搭班,期间曾三度傍海派京剧代表人物麒麟童周信芳,分别演出全本《韩信》《投军别窑》和《斩经堂》。恰在此时,适逢荀慧生带着上一年新编的《红娘》来黄金大戏院献演,他亲口应允让戴绮霞在台下观摩其演出,并由饰莺莺的二旦何佩华授其全剧总纲,算是正式进入荀门。戴绮霞赴台第一晚所演出的《红娘》,即是正宗荀派秘本。直到她九十多岁登台,所唱“小姐呀你多风采”一段,还是“戏改”前的老词,词即隐晦加上又媚又嗲的深情,在台上确实勾人心魂。二战期间,戴绮霞携母亲及幼妹戴根兰(来台从艺后艺名戴婉霞)从新加坡至江南避乱,经历过杭嘉湖水路班子、1942年,汉口“戏窝子”挑班收徒关肃霜、上海共舞台连台本戏、青岛华乐戏院与麒派老生高百岁共挑大梁的舞台经验,1948年,她率剧团赴台湾时,海派京剧历练丰富而完整。1974年起,她于国光剧艺实验学校等学校执教,她是梨园常青树,年过九十仍不定期公演,在台湾有“京剧皇后”美称。
顾、戴宝岛再“对台”
顾正秋与戴绮霞在大稻埕打对台的确切时间为1949年1月6日起至2月8日。青岛与台北,都是京朝派与海派京剧交汇的码头,观众对于两人的表现,也都给予高度肯定。
1949年在台湾打对台的情况与青岛时期雷同,但顾正秋在传记中只字未提,戴绮霞在接受访谈时,也以“不是对打,她在那边唱我在这边唱,只是刚好在同一个时候,我们谁也不输谁”的说辞暧昧回应。
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1948年底“张翼鹏与筱刘玉琴剧团”已先后在台湾新世界戏院和永乐戏院演出将近半年,张翼鹏决定返沪过年。永乐戏院在日治时期是电影与传统戏曲混杂演出的戏院,战后处于半歇业状态,因“上海美猴王”张翼鹏的演出为剧院票房带来起色,经理刘正明打铁趁热,觉得亲自到青岛邀请风头正劲的顾正秋来台接替因“美猴王”离开而形成的演出空档。没想到的是,这次来台,让顾正秋彻底失去回大陆的机会,从而成了宝岛京剧的播火者。
顾正秋于1948年12月20日在台湾永乐戏院登场,连演半个月,所演兼及梅尚程荀各流派名家的看家剧目,且多为唱工戏。台北观众相当捧场,天天满座,一票难求。当时台湾报纸《财神爷》有这样的报道:
“顾正秋偕老生胡少安,于廿日登台永乐戏院。营业鼎盛,卖座空前,廿日夜戏,在十八日晚去买票,已卖出十分之八,这亦难怪,初期露演,当有人捧场,可是现已出演四五天,戏票仍是无有,虽头三天预定,又是到头一天去拿票还是十五排,不然就是边上,请你饱闻厕所异味,与之交涉,是自找难堪,大有‘要就拿走,不要就算’的态度,毫不客气。”
同一时间,台湾新民戏院正好因“海升京剧团”当家花旦海慧苓欲回上海,尽管老生徐鸿培推出连台本戏《貍猫换太子》,一连演至七本,似仍孤掌难鸣,从元月2日起便告休演。“新民”为求营业,委托蔡金涂前往上海邀角,请来的就是刚从青岛载誉回上海发展的戴绮霞。当时该戏院在《新生报》上刊登预告:
郑重启事:本院为增强阵容除将观众一致欢迎之徐鸿培剧团予以恳切挽留外,并派专员驰沪邀聘南北名角文武花衫祭酒戴绮霞、文武唱工须生于占先、艷丽无双文武青衣花旦戴畹霞(按:应为“婉霞”)、青春美丽花衫缪湘娟、架子铜锤花脸张世春、滑稽小丑左伟民等外十数名,业已抵台稍事休息,不日登台献艺以谢顾客之雅望,希密切请注意公演日期!
1948年(民国37年)12月24日,戴绮霞一行人搭乘的“太平轮”缓缓驶人基隆港,负责接船的人把他们带往台北大稻埕延平北路二段的“新民戏院”后,直接让他们加入己经在此演出将近一个多月的“海升京剧团”。当时,“新民戏院”正和“永乐戏院”同样来自上海的名角顾正秋对台竞争,戴绮霞一来正好就补上了“海升”的头牌旦角演员海慧苓回上海留下的空缺,从1949年1月6日起至2月8日,戴绮霞和顾正秋足足打了一个多月的对台。
海派京剧的做工老生和女武花且有很多对手戏可演,戴绮霞不仅自己唱了不少老戏,也和徐鸿培合作了《北汉王》《楚汉相争》《盘丝洞》《越王与西施》《八宝公主》《六国封相》《天雨花》《董小宛》《潘杨恨》(全本《杨家将》)、《杀子报》《斩经堂》等戏。94岁那年,回忆起这段演出岁月,戴绮霞觉得当时跟“小秋”根本算不上什么打对台,面对采访者,她一派轻松地说道:“不过就是她在‘永乐’唱她的顾派戏,我在‘新民’唱我的戴派戏,要不就和徐鸿培陪他唱他的麒派戏。还前后没几个月,谁也不输谁呀!”
民国38年1月22日《华报》有一篇评论,戏迷“卫民”对戴绮霞与顾正秋对台的情形和她的绝活描绘甚详:
这次戴绮霞来台,助徐鸿培出演“新民”正和“永乐”的顾正秋打对台,论技艺各有千秋,如以资格经验来说,戴绮霞较顾正秋棋高一着,加之不骄不纵,前后台人缘奇佳,又肯卖力赶活,因此出演以来,卖座始终在水平以上,并不稍受影响绝对不是偶然的事。……前天她贴演三本铁公鸡中的张嘉祥,依我的预料,她这个女扮男装的张嘉祥,袒胸裸体,跌扑开打的全武行,一定很难讨好,哪里知道一出场,几个筋斗,稳健轻松就是一个满堂彩,一臂裸露,雪白粉嫩,扮相英武,及至开打,五龙绞柱,满台乱滚,扇刀更舞得出神入化,武功之佳,如非科班出身绝不会有此成绩,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压倒顾正秋了。
这段评论从技艺、经验、演出态度等方方面面比较了顾戴二人的些徽差异,从字里行间也可看出该戏迷对于戴绮霞这边卖座成绩之在意,可想而知当时二团必有一番激烈竞争,肯定不是戴绮霞后来所说的这般轻松自在、云淡风轻。
余韵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局势紧张,愈来愈多的军民涌入台湾,这其中有许多来自京津的艺人,像出身“富连成”的朱世友、马元亮、孙元彬、孙元坡、哈元章等多位正宗京朝派科班。京津各地艺人加入,使得台湾整体京剧演出热闹蓬勃、京海并呈。同时,面临同样的资金困难,顾正秋毅然选择“扛上那面艰苦的枷”(顾正秋语)挑起班子继续在永乐接着唱,藉由她在上流社交圈的交际与人脉(蒋经国曾倾心于她,而她后来给时任台湾省财政厅长、台湾银行董事长的任显群当了没有名分的“妻子”),以及顺应正统文化的流行趋势,创造出五年传奇性的演出历史。而戴绮霞和徐鸿培未采取就地承租戏院继续演出,反而决定收拾行囊往台中走,其中因素,当然不能免除戴绮霞一行冲州撞府的艺人惯于到处跑码头、找机会的习性,同时也说明,经营者可能嗅到了台北京剧观演风尚正慢慢由“海派”向“京朝派”倾斜,从此,台北与其以外的地方,显现出喜好有别的情形:台北城内由“顾剧团”稳坐龙头,台北以外,则几乎都是海派京班的天下了。从两人竞争态势的消长,显示出战后初期的台湾京剧,在延续海派京剧传统的基础上,京朝派艺术已经慢慢地开展开来,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