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红色刺槐花
年轻时,一身白,气清幽
年龄逐渐增长,变老,呈红色
住进繁华闹市区——我是说
我是我,刺槐花是刺槐花
我住乡下酿蜜,它在城市治病
小狗叫着离开
眼前六级水泥台阶
被树影筛下的阳光撑得很宽
一只小狗,站顶上,占据中间位置
我经过这里,收住脚步,它也停下
我们因面对面无法躲开
我很想记录这个场景
没事一样取相机
脑袋歪向发光的植物
用自然的动作举相机
意思是我想拍远处的房子
镜头里出现了它,小狗居高临下
仔细观察我每个动作
对焦时,小狗俯下身
石阶平台落满它的大吼
我们谁都没走六级台阶
也许本来谁都没想经过它
虽然石阶被树影筛下的阳光撑得很宽
苔菜花黄
急刹车没影响
它把黄继续往地里洒
却直接把风
按倒在低矮的河床
那床被子
天再热也不多余
鱼水之欢需要
搂抱在滚热的卷筒内
说尽软绵的情话
我走了整整一个春天
终于到达高潮
大蓟高大
小蓟边上一棵大蓟
身高是小蓟的十倍
周围几棵速生柳
带来阴凉和飞虫
速生柳高大
但不影响大蓟俯视小蓟
它们皮肤嫩滑
阴影中相互取悦
虫蛾飞舞
大蓟满足自己的身材
小蓟满足浑身的刺
比大蓟尖硬
麸子苗和田旋花
叫它麸子苗
它便是羊追赶的野草,村妇
或推车叫卖的街头小贩
当它被称为田旋花
它就是造型艺术家,中国好歌手
半个脑残诗人
或混迹于商界的著名演员
播娘蒿的回忆
这丛播娘蒿
长在莫言旧居和基督教堂之间
水泥路南边小块空地。
梧桐和刺槐树占大半部分
剩下的干硬地面才属于它们。
开出的花像苔菜
也像油菜
花瓣的黄介于两者之间。
没有一棵麦苗。
播娘蒿应该长在麦田
或靠近麦田的沟坎、畦垄才对。
它们聚集这里的原因
不因为莫言旧居
也并非由于距离教堂不远。
属于平安村的一部分
也谈不上。
播娘蒿大概是有记忆的植物。
去年也许更多年前
这里种过麦子。
播娘蒿借助回忆
返回此地树荫之下
长得和原来一模一样。
苦菜花香
取单饼
或生菜叶一张
洗净的苦菜根码放其中
卷起,双手握住撕咬
吃下它,败火
带上铲子、铁锨
条筐或小桶
躬身在春寒中
弯腰在挖开的一个个土坑
抖掉土屑
粗根、细须和幼芽
都要完整
憋了一个冬天
春天的人火气大
围餐,吃下它
不觉得苦
苦涩用嘴和味蕾
感受不到
断了腿的苦菜
少了一只或两只胳膊的苦菜
首身分离的苦菜
丧偶、失去子女的苦菜
被一阵紧似一阵的风
被一直不停飞奔的鸟鸣
被一滴寻找故土的雨
吵醒了
它们从毫无生机的碎石缝隙
爬出来
它们从自己的尸体爬出来
它们从笑声中爬出来
它们从哀嚎中
爬出来
我蹲在一棵苦菜身边
递给我黄花
用嘴衔着一朵黄花递给我
递给我一缕清香
它递给我心静目明的早晨
风景
想早点到达某处风景
就得比别人走快点
最好早起
赶在道路明亮前
赶在清晨还没醒来
如果想在某处风景逗留
并且最后一个离开
就要慢和晚
比时光慢,比夕阳晚
所有人走开了自己也不走
直到夜色隐藏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切
假如要拥有某处风景
早和晚,快和慢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找到它
做好停下不走的准备
做好把余生丢在那里的准备
直到心灵枯竭
植物茂盛
白缘蒲公英
左边的农舍
因为中午关闭着
石头的墙,把睡眠垒出
四四方方的轮廓
右边的深沟
比昨天有更长的路要走
因为梦境被进一步
生长的树木举得更高
甚至连根拔起
你目睹过葱、蒜和青菜
被无数次播种
反复长大
你蹲在墙外菜园的偏僻角落
在寻求安静的流水身边
从完整的梦的壳里
探出半个脑袋
看见了自己
称得上美丽的睫毛
大苦菜子
必要时,你得告诉我
叫什么名,正规的学名
喜欢做什么,最爱吃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夏天还没有
蝴蝶,飞到你这里
我估计蜜蜂和花雨都错过了
陪伴你的枯井
春天离开了
你应该有时间描述一下那眼枯井
你从它黝黑的里面
是否发现了水
水中的青蛙
它们是否摘走了你说过的星星
当然,除了这些重要的
那些无关紧要的
最好也能告诉我一些
比如清晨从你眼角滑落的露水
用去多少时间
为你测量了那段黑暗的距离
还有你无数次提到的黄昏
会否真的每次都为你
披上一身鹅黄
翠鸟与樱珠
那对翠鸟是第三个年头
飞到我五年前栽在院门前
果子即将熟透的樱树上
它们来自胶河边
大概刚刚吃下几尾小鱼
到这里为餐后水果
一只在吃
另一只往四周观看
之后交换角色
吃够的那只顺带整理尾羽
是不是三年前那对翠鸟
我不得而知
它们吃樱珠的方式
三年来一模一样
只是吃的过程一年比一年
随意和放松
鸟儿飞走后
我查看满树樱珠
一个不少
树梢上留下一些核
我模仿它们吞下一颗
树上便少掉一颗
米口袋绣好一朵花
喜欢直呼它米口袋
这样粗俗地喊一声
它就不是草也不再是一味药
而是墙根地边石缝
站起摇摆的风情
它擅长将一朵小花
绣在胸前左侧偏上位置
用白线做底铺边
围成黏住朝露
也反射午间强光的薄片
至于夜晚
它让这乳白羽毛躲在低处
卷起来
护住尚未完工的绣品
我和它相遇
是夕阳西下之时
它把收拾好的针线
藏于浅绿的袖筒
我靠前仔细看它一眼
怦然心动
它慌乱地转过脸去
粉红的心颤抖得
像刚刚绣好的一朵小花
蔷薇美丽
蔷薇开满铁篱
那是两只大狗的愿望
它们代表我
坐在院子摇尾巴
母的向公的示好
公的看看我,我看篱笆向上的花
是的,那些花
摆错了位置
它们居住在尖锐之间
绷紧错位的阳光
我们共同的嗜好
一首诗歌无法完成
蔷薇一会白,一会红,一会粉红
两条尾巴,往同一方向摇摆
我转身,拔掉手指的刺
难以理喻的鲜艳滴到舌尖
白茅之饮
辩证法诞生前
藏身晒雪的斜坡土层
它不知冷的概念
后来,唯物论
把春天植入风土人情
它错误地举起唯心主义的利刃
却荒谬地躺在少女的手上
像根甜的倒刺
我们吃它的时候它叫茶饮
我们吃它的时候辩证法
借夏天的手剥去了它的外衣
我们不再吃它
它变成了白茅
它举起软绵绵的枪
尝试刺穿漫山遍野的风
这时候我坐在一截唯物论的树桩
打瞌睡
忽然想到口袋
香烟和打火机里的液体
斜坡的隔壁种了上万亩黄烟
我知道应该辩证地看待
白茅和黄烟的关系
白茅说夏天它冷
一身白雪
它喝过太多雪水
我吸进太多烟
山顶蔷薇
不是很高的山
也有山顶
并非尖锐的山顶
长了草和一丛蔷薇
蔷薇从几块石头缝隙爬出来
一身尖锐的刺
刚刚打开的花是红的
有柔软的花瓣
我喜欢它柔软的部分
像喜欢低矮的山
和随意摆放的圆石
这里至少可以生长野草
生长蔷薇是意外惊喜
而寸毛不长的高山之巅
只能算是象征
并非沃土
为什么遇见蔷薇而讨厌高山
我想不出理由
其实我也不喜欢蔷薇
它的红过于鲜艳
四处攀爬
疯长丧失节制的刺
我想伸手摘一朵的时候
被路过的白云制止
我喜欢白云吗
在这孤零零低平的山顶?
太阳草
或许它有比太阳草更好的名字
但我不知道
我喊它太阳草的时候
它开了太阳花
紫白色的
紫白色的太阳花
开了几个早晨
败落了
又回到草的模样
被阳光照着
绿的萎靡不振
我叫它太阳草的时候
是个中午
你没表示反对
你蹲下在它身边
被一阵热风吹开了笑脸
亲爱的,反对也没有用
我是你认可的植物学家
而你研究人和动物
看麦娘
我观察月亮的颜色
比如现在
我从白杨树的阴影观察它
它喝了过多的酒
蹲在沟沿前后摇晃
原先不是这样的
原先它站着抽完卷烟
再学习水的起伏淌过麦田
我观察月色时你睡在村庄中部
你睡在大狗的鼾声
像牛栏一般寂静
月亮绕过半个村子
和大片麦田
我观察它时它举着镰刀
正在收割你掉落的梦
躲在白杨树的阴影不能入睡
我假设不能入睡的原因
是小麦一直醒着
而大狗只有翻身才暂停鼾声
车前草的黄昏
等我拐过屋角
黄昏便把一条胡同揉搓的不成样子了
那头栓在木桩的大眼花牛
哞一声不情愿着往灰暗里退
蝴蝶本来站立挑水桶的老汉扁担
这时候飞去了高过屋顶的刺槐树杈
关闭木柴门的辅首转动一圈
躲在村西白杨树林的夕阳便咽一口唾沫
所有的金辉被斜坡屋顶截流
碎末掉到矮墙的灰瓦片蹦跳两下
车前草模糊在胡同呆若木鸡
我蹲在它身旁惦记一个人直到想不起来
汉墓观景
登上三十五米高的汉墓
就看见连片麦田了
我以为能听到麦浪声响
其实不对
麦浪的声音也是用来观望的
在被收割前
两千年前的墓顶土堆
酸枣树新叶琐碎
狗娃花紫圆
三只钻木蜂飞来飞去几个来回
我是第五只挤在它们中间
第四只在塚外盘旋
采石场往下
又钻出几个巨大的窟窿
下午两点,阳光炙热
柏油路,像僵硬的蚯蚓
汽车停在上面,如焦糊的甲壳虫
采石场工人,东倒西歪
睡在公路两边
一个工头模样的人
走去蚂蚱模样的碎石机
踩倒一丛白茅
我见自己穿汉服
断襦敝屣,腰垂长带
打开车门走上墓顶
看原野浩荡,麦浪如海
狗娃花开,艳若佩霞
听见第四只钻木蜂飞回
哼唱乐府之音
为什么不是金银木
如果你是金银木
我会高兴一个下午
但你不是,我只好绕开湖走
绕开近似平面的事物
两条交叉在一起的公路
持续奔跑的草地
桥头讲哑语的指示牌
徒然站立的石坊
一个人握紧又伸开的手掌
紧贴水面明亮的荡漾
你不是金银木
我只能爱圆的立方体
柳枝自下往上褪尽叶子
光柱往灯杆攀爬
油罐车熄火于十字路口
杯子和它围困的汁液
一次失眠
蹲在井口打捞失落的影子
蚂蚁向草丛移动的队伍
挤开月影的围堵
如果你是金银木
我会愉快地披衣出门
用很久没用的拐杖
分开覆盖台阶的日子
分开光束和暖意
站在被堤岸隔开的早晚的缝隙
使用不规则的声音
展开一枚打了卷的落叶
让一滴水从脉络涌出
流到你的掌心
(待续)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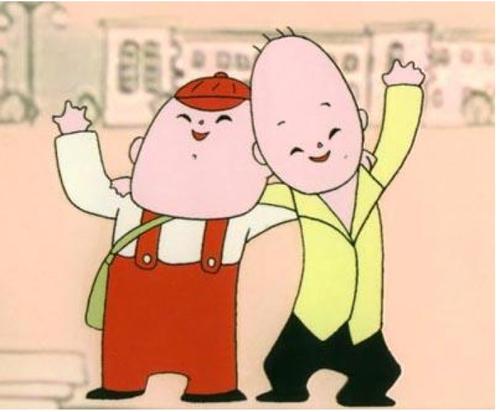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