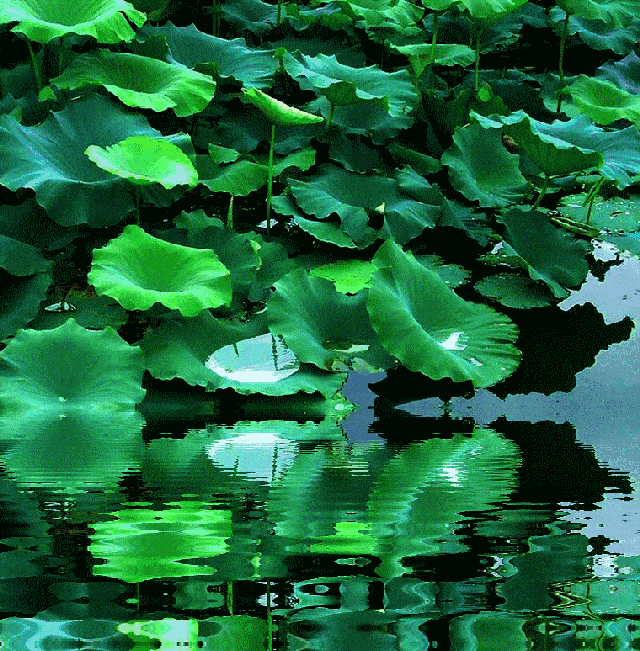根据王国斌的油画《我的前夫》改写,人物和事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作者
“不!不——!”
何嫚连踢带踹的挣扎,胳膊一抡,把睡在身边的博闻惊醒了,他朦朦胧胧地翻身把妻子搂进怀中:“醒醒,是不是又做梦了。”何嫚一下子醒了,泪流满面,她把脸贴在丈夫宽阔的胸膛上,紧紧地把头拱在在博闻的怀中。刚才是做了一场恶梦,梦见一条凶猛的黑狗把她拖了就跑,她正在挣扎的时候,被丈夫晃醒了。她被博闻紧紧地箍着,却再也睡不着,她知道,那是援朝家的狗。
乡下村里那条胡同里的狗是出了名的凶猛,知青们都绕着走。多少年了!每每一想起下乡时的经历,泪水就在何嫚的心里翻滚,究竟是嫁过一次,何嫚不愿再想起它。而年轻时的狂热和轻率、乌托邦式的理想、那些无知和愚昧、那些贫穷、那些无奈、无望和委屈,却像雾霾一样时不时地侵入她的脑海……
一
那时的年轻人是多么的天真和容易激动啊,只要国家需要,刀山火海也敢闯,何况是上山下乡呢?!再说,在城里也没有工作,哪怕是有个扫马路的活……
何嫚和她的同学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已经待了整整五年,原来宏大的理想变得虚无缥缈,广阔天地里的封闭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在把这些天真烂漫的学生变成一个个“闰土”,谁也没有想到上山下乡就是在农村把自己蜕变成一位农民,那些漂亮的口号成了画在墙上的“饼”。
初到农村的学生们连青草和麦苗也分不清,为了除掉地瓜苗旁边的一些草,知青们连地瓜苗也都一起锄掉了,惹得队长心疼地咆哮;夏日,高粱地里密不透风,草疯了似得长,雨后的地面热烘烘地蒸,天上的太阳火辣辣地烤,何嫚和乡亲们挥锄除草,汗水模糊了眼镜,昏昏沉沉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大雨滂沱的天气也要下地,地头上的大树下,知青和老乡们拥靠在一起避雨,前来检查工作的公社书记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盛赞农民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除了喜悦,还有用原始工具干不完的农活;冬天寒风凌冽,继续学大寨深翻地,一锨土扬出去被大风吹得老远老远……除了这些,还有索然无味的政治学习,这种平庸的日子绵绵无期……一年下来分了二十几元钱。这是一年的辛苦钱,除了回家的车费,剩不下几个钱。
有的知青受不了这个苦,家境富裕点的就频繁地穿梭于城市和农村,可是户口不在城里了,口粮也没有,家里也不能长待。几个男生已经准备打算去东北闯关东了,听说那里的生活比这里好过些。若在这里娶个农村婆娘过一辈子,想想都后怕,知青们都在为将来的出路焦虑着,打算着。
知青们里连咸菜都没的吃了,饭食只有地瓜,锅上面蒸着地瓜,锅下面煮着地瓜,用地瓜腌的咸菜半咸不甜地透着股怪味令人作呕……这样的日子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幸亏支书前几天在村里的喇叭上号召各家各户给知青捐点咸菜,朴实的老乡们端着碗,三三两两地来到知青组给他们送咸菜,有的送两个辣疙瘩,有的送三个咸萝卜,有的把现腌制的白菜帮也送来了,分管做饭的何嫚满怀感激地连连道谢,知青们终于有咸菜吃了。只要有咸菜吃,再粗糙的饭也能咽下去,知青们吃着百家咸菜,心中对老乡们充满了感激,农民们也很穷,他们就指望着几只鸡下蛋换钱买盐吃。
前几天县里召开知青会,一再要求他们扎根农村干革命。扎根?什么叫扎根?说白了,就是让知青们在农村一辈子,在农村成家立业。怎么成家立业?就指望着一年分的二十几元钱?怎么盖房子?怎么养老婆孩子?男知青老四和老五两人回来后,垂头丧气地从小卖铺打了半茶缸子白酒喝得酩酊大醉。
天气非常好。因为是难得的好饭,知青们的午饭比平时吃得快,老六吃了六碗面条,这是何嫚用高粱面、地瓜面和白面擀成的面条。他们已经下地干活去了。只剩下了何嫚一人,待在杯盘狼藉的伙房里,炉膛里的火正在渐渐地熄灭,她舀出锅里余下的面条汤,不慌不忙地洗着餐具,偶尔停下来伸伸腰。何嫚洗完餐具,又抹了桌子,清扫完地面,心里七上八下闷得慌,她望了望黑黄色的黏土墙,屋顶上熏黑了的木梁还有角落里挂着的蜘蛛网,叹了口气坐下来,想起支书婶子给自己提亲的事儿就心烦意乱。
前些日子,支书婶子来到知青宿舍,满面春风神神秘秘地对何嫚说:“何嫚,援朝相中你了,让我送给你块花布做衫子穿。”
何嫚的脸一下子红了,慌忙摇头:“我还小呢,不考虑这事儿。”
“不小了!上级不是号召你们安家落户么,援朝家三代都是贫农,根红苗正,跟着他吃不了亏。”
见何嫚低着头不作声,少许,支书婶子又亲昵地凑到何嫚的耳旁小声说:“你出身不好,结婚以后有援朝护着你,没人敢欺负你。”
见何嫚还不言语,支书婶子笑眯眯地把那块花布塞到何嫚的手中,“我先走了,有空到援朝家坐啊。”
何嫚头脑一片空白,呆呆地看着手中淡绿色的小格子布,它很像自己用过的作文本,记得老师曾在这些小绿格子里用红笔批改过自己的作文,她又想起遥远的家,多病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自己在农村嫁人了,他们以后怎么办呢?无限的忧虑充满了心头。
黄昏,当晚霞消失以后,天地间变成了银灰色。
何嫚和马莉莉漫步在小河边,“你真的要嫁给援朝吗?”马莉莉看着何嫚的眼睛,试探地问。
闻言,何嫚收住脚步,一言不发,怔怔地看着远方,紧闭着嘴,她的内心充满了尖锐的隐痛,嫁还是不嫁,这些矛盾在她的心中乱碰,家中来信让她自己拿主意,她知道这辈子是跳不出农门了。一颗眼泪慢慢地从她脸上流下来,接着大颗大颗的泪水涌出眼眶,霎时泪流满面。
“不愿意就不嫁!……”马莉莉也哭了,她抱住何嫚哽咽着说。
何嫚的泪水无声地流着,擦去,又流出来……真的是心有不甘啊。“可我出身不好……”何嫚抽泣着说。
无奈的委屈像挣脱不开的大网紧紧地罩着她,令她窒息和无望,万千的伤感化成泪水涌出她的眼睛,何嫚心中的白马王子不是这样的!!!马莉莉也哭,她哭何嫚,也在哭自己。她们依偎着坐在黑幽幽的河边,沉默了许久许久,怎么办?何去何从?没有人告诉她们怎么办。月亮时隐时现地穿行在云朵之中,偶尔露出脸看看河边的这对小姐妹,又躲了起来,朦朦胧胧的,神秘莫测,一种深深的忧伤充满了何嫚的胸怀。
半夜已过,何嫚躺在床上,内心焦躁不安,一会儿浑身热得发烧,一会儿又冷得打颤,她听得出自己心跳的声音,内心十分痛苦,泪水不知不觉湿透了枕头,“我不爱他,为什么要嫁给他。不嫁给他,又能怎样?”何嫚和心里的自己狡辩着。自从支书婶子和她说了这个事情以后,无端地她竟然生了好几场大病,病愈后脸色焦黄,看见她的人无不惊讶。
二
那天的晚饭依旧是地瓜,何嫚和马莉莉每人拿着一个地瓜往宿舍走着,村里人家的屋顶上冒着袅袅的炊烟,整个村庄安静而沉思。
蓦然,小莲翘着两只小辫跑到何嫚的跟前,拽着她的衣角小声地说:“姐姐,我娘让你到我家吃饺子。”
“饺子!”马莉莉闻言,跑进屋子拿出一个空饭盒笑嘻嘻地塞到何嫚的手中,推拥她和小莲快走。何嫚不情愿地拉着小莲的手走在村子里的胡同里,小莲是援朝的妹妹,个子很瘦小,好像不过七岁的样子。援朝家在胡同的尽头,这条胡同里的狗很凶,小莲拉着何嫚的手,闻声跑到门口的狗看见小莲,立马摇着尾巴显出一幅低眉顺目的样子。
何嫚一进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援朝家人热情地邀请何嫚上炕吃饭,农家人朴实,怕客人不好意思吃,把饺子捞在了盖垫上,这样吃多吃少谁也没有数。
何嫚拿出饭盒,不好意思地说:“她们让我捎点……”
“好,来!”婶子爽快地接过饭盒把饺子往里拨,何嫚一看剩得不多了,连忙说:“好了,好了,够了。”
“那我回去吃了,谢谢啊。”
援朝娘示意援朝送送何嫚,“我送送你。”援朝连忙说道,何嫚怕狗,援朝走在她的前面,一直把她送到知青宿舍门口,一路无话。
“你回去吧。”何嫚说。
援朝咧了咧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憨憨的点了点头,扭头往回走。
女知青们见援朝走了,关上门,打开饭盒一下子把饺子抢着吃了个精光。
“哎——你们尝出是什么馅儿?”晓雅的筷子还没放下,睁大眼睛吧嗒着嘴问大伙儿。
“嗯?什么馅儿?”大家问着,相互看着谁也说不出来,吃完了居然还没尝出是什么馅儿。
“哈哈哈……”她们捂着肚子笑出了眼泪。过了一会儿,马莉莉收住笑声说:“咱这——可是沾了何嫚的光……”大家一时语塞,心像被捅了一刀!
何嫚眼里含着泪花说:“没事,吃吧。”她们哪里知道,何嫚什么也没吃。
支书婶子不断地来知青组找何嫚,小莲也不断地来拉何嫚到她家吃饭,这时的何嫚头脑完全是个空白,不再想什么,也不再希望什么,还希望什么呢?自己早晚要嫁人。但她心里知道同学于博闻对她有意思,他虽没有向自己表白,但她从于博闻那忧郁的眼神中早已读懂了他的心意。可于博闻和自己一样,出身也不好,他当教授的父亲还是右派,全家都被遣送到农村接受改造。何嫚她权衡过,若是嫁给于博闻,后代还是黑五类,还是要受人歧视,什么时候才能改换门庭,堂堂正正做个人?不行,为了后代,也要嫁个出身好的。
可是,何嫚又心有不甘,自己爱于博闻身上透露出的儒雅气质,虽然他干农活不行,但他干净,宽容,有思想。可有思想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别的男生一天都挣10个工分,于博闻只能挣8分,比自己才多1分,将来在农村能活下去吗?不行,不能嫁给他。何嫚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些矛盾在她的心里乱撞,那出嫁以前也要和于博闻讲明白,自己嫁给援朝也是不得已的事,让于博闻原谅自己。这些想法一天到晚地搅扰着她,一会儿想到博闻,心里一热;一会儿又想到援朝,心中又一冷;自己和他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另一个声音又说:共同语言能当饭吃吗?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的何嫚,原始的生存本能站了上风,但心灵深处的对博闻的爱还是心有愧疚。于是晚饭时,在递给博闻窝头的时候,顺便夹带着一张纸条。
月牙儿惨白地挂在空中,于博闻应约来到了小河边的树林里。何嫚早已在等着他了。树上的知了讨厌地“吱吱——”叫个不停,河边上的青蛙也“呱呱——”地凑热闹。何嫚用手指不断地缠绕着自己的辫子,她看着博闻清瘦的面容,低下头小声地说道:“博闻,你别怨我,我也是没有办法。”
博闻知道何嫚说的是她和援朝的事儿。他咬着嘴唇看了何嫚一眼,马上把目光移到别处,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于博闻停顿了一下:“只要你过得好,就行。”说完,鼻子一酸,眼睛里立刻盈满了泪花。
“要是咱俩在一起,以后的日子,”何嫚顿了一下,抬起头来大胆地瞧着博闻,“可怎么过。”
“我知道,”博闻擦了一把脸上的泪,但不争气的泪水依旧哗哗地流,他努力地紧闭着嘴,然后嘘了一口气,盯着何嫚的眼睛说:“我也出身不好,我不能拖累你。”
闻言,何嫚的眼睛里顿时涌出了泪花,“他知道我的心思。”何嫚心里一酸,勇敢地往前走了一步,靠近了博闻:“抱抱我,博闻。”博闻迟疑了一下,然后伸出双臂紧紧地把何嫚拥在怀中!这是于博闻多少年来的梦想!他爱何嫚的善良,爱她美丽的眼睛,爱她娇小的身材和美丽的容颜,爱她那两条大辫子,他爱她的一切!于文博浑身颤栗着,内心有某种渴望,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行!何嫚是自己心中的女神,神圣不可侵犯!何嫚泪如雨下,她紧紧地依偎着博闻“对不起,博闻。”博闻紧紧贴着何嫚的脸,哽咽地说:“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他用舌头舔着何嫚的泪珠咽了下去。
“我们下辈子在一起啊。”何嫚哭出了声,呜咽着说。
“好,我会想着你。”博闻镇静下来,掏出手帕擦着何嫚不断涌出的泪水,“回去吧,好好过。”自己的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
月牙儿无力地挂在天边,好像衰弱的不能走动,只有在天上待着。它也没有自由,也是要受到约束。它被天空中的肃杀之气威逼得麻木了,无奈地向人间挥洒着了无生气的黯淡的光。
秋后,援朝家把一间房子收拾干净,用作何嫚和援朝的新房,援朝一家人对她极好,尤其他奶奶,拉着何嫚的手,端详着她的脸,用粗糙冒着青筋的手,爱怜地在何嫚的脸上摸着:“城里的妹子就是耐看,皮儿这么细。”而何嫚和援朝婚前连手也没有拉过一回。
马莉莉送给何嫚一双红袜子,婆婆给她买了一双带着花的红绣鞋,几个女生看着这双绣花鞋捂着肚子笑弯了腰,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们看,这红花绿叶的,土不土?”晓雅手里拿着一只红绣鞋端详着说,有人捅了捅她,她马上改口说:“哦、哦,不土不土,结婚就得穿红戴绿嘛。”不知是谁抽抽嗒嗒地哭起来,大家都不作声了,忽然,晓雅也“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于是这几个女生聚在一起抱着呜呜地哭起来,不知是她们是在哭何嫚,还是哭自己。
知青组送给何嫚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语录作为陪嫁,扉页上写着:祝你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扎根农村干革命!
那时的婚礼是革命式的,援朝家黄色的土屋前,摆着一条长条凳,何嫚和援朝坐这条凳子上,何嫚穿着一身洗的掉了色的黄军装,红袜子配着红绣鞋和胸前的大红花,何嫚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绣花鞋,心里充满了委屈,她想起家里生病的妈妈,心里就想哭。
长条凳的旁边放着下乡时妈妈给买的帆布行李包,这是何嫚的全部家当。秋天的阳光耀得她睁不开眼,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喜气洋洋地围着新郎新娘看热闹,何嫚看见知青们混杂在老乡们中间,却没有见到博闻,一丝惆怅涌向心头。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人们在交头接耳,品评着新媳妇。何嫚突然地想起了妈妈,在这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没有娘家人来送别,自己从此没有了自由身……
“新媳妇!笑一个!新媳妇!笑一个”孩子们不知道在谁的唤使下,大声地朝何嫚吆喝着,何嫚笑不出来,满心身地委屈。
她低头斜眼看了一下援朝,他正咧着嘴笑着,胸前的大红花映的他的脸红彤彤的……
等所有的三邻五舍都走了以后,何嫚累得依着床边上的被睡着了。朦胧中醉醺醺的援朝喘息着在扒着她的衣服,本能的抗拒使何嫚转过身去,却被援朝粗鲁地一把掰过来……一行清泪从何嫚的眼角流下来,新婚之夜,竟然连彼此的拥吻都没有……
三
何嫚成了农家媳妇。婚后,她领着援朝回了一趟城里的家,令她尴尬的是援朝居然有椅子不坐,却蹲在上面抽烟,他把椅子当成了田间地头。看见母亲皱着眉头瞅他,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没说,何嫚一把把他拉下来,他懵懵懂懂地不知犯了什么错。在家里没住上两天,他们就回来了。
婚后的一段时间,婆婆家里的人待何嫚如上宾。他们家因援朝娶了知青做媳妇在村里很是风光,就是知青组的男知青们也没这个福分。
可没过几天,援朝对何嫚说,过了这个月她要在床边站着吃饭,看见家人谁吃完了,马上要给他们盛饭,农村的媳妇都是这样的。
“我又不是农村媳妇!什么年代了,那些陈旧陋习早就应该破除了。”何嫚不屑地说。
吃饭时何嫚低着头吃,对他们伸过来的碗视而不见,没办法他们就自己盛,何嫚为自己破除了旧习惯而沾沾自喜,没有注意婆婆的脸可是越来越阴沉了。
农家的生活调剂着吃,总比知青组吃得好些。有一次家中包饺子,何嫚想着组里的姐妹们,就先送了一碗给她们,回来后竟然没有她吃的了,一家人谁也不理她。
晚上,援朝试图和她亲热,何嫚早就厌烦了他晚上不刷牙不洗脚的恶习,转过身去讨厌地说:“上一边去!”由于何嫚经常回组里看望同学们,婆婆的脸更长了。
农家厨房都是在屋内的侧边盘一个灶台。有一天,婆婆做猪食,何嫚在灶台前古达古达拉着风箱,柴草冒着青烟熏得她睁不开眼。婆婆把开水舀进一个黑色的瓦盆里,用劲地搅着地瓜面糊糊和一些糠皮,“你去把这些倒进猪食槽里。”婆婆说。
何嫚站起来,不情愿地端着温乎乎的瓦盆向猪圈走去,见她走来,两只猪哼哧哼哧地拱着圈门,何嫚刚要把盆放在地上,谁知脚下一滑,“砰!”失手把瓦盆摔碎了,猪食淌了一地,也撒了何嫚一身,饿极了的两只猪一下子拱出了圈门,呱唧呱唧地舔吃着流淌在地上的猪食。婆婆气得把手里的炊帚使劲地扔打在何嫚的头上,“砰”地摔门进屋了,何嫚愣在那里不知所措,恰巧援朝干活回来,见状竟上来给何嫚一拳,骂道:“你怎么这么笨!你能干什么?!”又气愤地朝着她的小肚子踢了一脚!何嫚一下子跌倒在洒满猪食的地上,两只猪吓了一跳,见没人打它们,又呱唧呱唧地舔吃着何嫚身边的猪食。
何嫚坐在洒满猪食的地上,援朝的那一拳打得真疼!自己从来没有被人打过!悔恨、屈辱的泪水像瀑布一样无声地流下来,她在新婚的当晚就后悔了这仓促的婚事,后悔了这没有爱的婚姻,后悔为了逃脱知青组艰苦的生活而误入歧途的人生之路。“妈妈——”何嫚哭出了声,没人理会她。
婆婆出来把两只猪赶进猪圈,奶奶听见哭声,出来把何嫚拉起来,摸着她的头含着泪说:“可怜的孩子,你不是学生了,做了媳妇就要干媳妇的活呀!千年的媳妇熬成婆,慢慢地熬吧。”何嫚弯着腰皱着眉头,手捂着肚子直喊“哎哟,肚子疼”,奶奶往后一看大惊失色,何嫚裤子的后面沾着的猪食和红色的血迹混合在一起。“援朝他娘,快来!何嫚好像小产了!”闻声,婆婆赶快跑过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们怎么也不说?”说着,朝着身边的援朝就是一巴掌,“这些不省心的孩子。”
何嫚也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他们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学过生理课,不懂的这些事。婆婆把援朝撵到另一个房间睡,自己和何嫚睡在一个炕上“可惜了我那大孙子。”婆婆不停地嘟囔着,“好好调养着,说不上下个月就又怀上了。”何嫚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半个月,何嫚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回了知青组,睡在了她原来的床上。见姐妹们都睡着了,何嫚披着衣服走到屋外,四周全都是夜色,那种深入骨髓的落寞、绝望,使她心灰意冷,她感到冰窖似的悲凉,原想脱离知青组的清苦,没想到又掉进了苦难的深渊,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渴望在博闻怀里痛哭,向他诉说个痛快。不行,自己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何嫚想到了死,活着有什么意义?死了就没有痛苦了,自己的灵魂会随着风随着云在宇宙中飘流,自己再也不用别人来摆布自己的命运了,天上不用上山下乡吧?那里没有痛苦。何嫚望着黑黝黝的天空胡思乱想,仿佛又看到母亲抚着自己的尸体嚎啕大哭的场面“嫚啊——”“妈妈——”想到这里何嫚浑身颤抖着忍不住地哭出了声。
夜深人静,何嫚压抑的哭声还是惊醒了室友,马莉莉和君萍她们点起了煤油灯,寻声来到何嫚面前,“别哭了,援朝真不是东西,还打人,不行就离婚!”她们义愤填膺地劝慰着何嫚,“你们快睡吧,明天还得干活。”何嫚推搡着她们,泣不成声地说。
她满心地悔恨,后悔自己轻信了报纸上的宣传,当时报上说:家中有两个应届毕业生的,下乡一个就业一个,为了弟弟能留在城里就业,自己才下的乡,当然还有那所谓的理想。现在报上又说,家中有一个就业的,其余的都下乡,无奈弟弟也下乡了。无限的忧愁和悔恨浑浑噩噩地充斥着何嫚的心。一夜无眠,直到村里的鸡叫了,她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乡间的早上空气清新。知青们围坐在小饭桌前吃地瓜,援朝和他娘来叫何嫚回家吃饭。何嫚低头不语,于博闻挑了一个红皮的地瓜递给何嫚。马莉莉手里拿着地瓜站起来对援朝说:“何嫚宁愿在这里和我们吃地瓜,也不回去了!你还敢打知青!等着离婚吧!”
援朝娘正要和她理论,组长老大站起来边剥着地瓜边呵斥着马莉莉,“少说话!”
他把援朝娘俩拉到一边,摸着嘴说:“你们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听说援朝你还打了何嫚?知青是随便打的么?我们是毛主席派下来的。何嫚就是你媳妇,也不能打人,是不是?”
听了老大慢条斯理有分量的话,援朝娘满脸赔笑:“我们打人不对,以后不敢这样了,让何嫚回家吧。”
“你呢,援朝,男子汉打女人丢不丢人?”
援朝扭过身子不语。
“你们回去吧,吃了饭,我把她送回去。”
援朝娘看了一眼何嫚,陪着笑脸拉着儿子走了。
四
何嫚结婚半年,小产后竟再也没有怀孕。这在乡间又引起了闲言碎语,农村的晚间,除了寒冬外,媳妇们聚在门口说三道四,议论着东家长西家短的,有什么新闻就像长了翅膀立马传遍了全村。
“听说了没?援朝说了知青媳妇,光好看不中用,活不会干,连孩子也不会生!”
“第一次喂猪,就摔了盆!哈哈哈……”
援朝的家事成了村里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闲话传到了援朝娘的耳朵里,心里又生气又着急,自从何嫚挨了打从知青组回来后,支书来他家把援朝和她训了一顿,以后她家虽没再难为何嫚,但结婚半年还没怀上孩子,她的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
始料不及的是,传说知青可以回城啦!这个消息在知青们中间炸开了锅,他们奔走相告,日子终于有了盼头!何嫚听说以后,在家里更是魂不守舍。现在知青组已经有三个回城就业了,余下的知青已经没有心思在农村干活了,马莉莉也整天骑着自行车跑县知青办,她家人已经在城里给她找好关系准备回城。还有的家长从城里买了礼品不断地往支书家里送,家长们动用了各种关系想把自己孩子拉出农村。就在何嫚一筹莫展,度日如年的时候,姐姐和姐夫来了,要把她带回城,说她妈妈病了,要她回家伺候。援朝要跟着进城,被何嫚的姐夫阻挡住了。那条黑狗摇着尾巴跟着援朝的身后,把何嫚送到村头,何嫚拐弯的时候,看见援朝和狗都还站在那里……
半年以后,姐姐和姐夫给援朝家送了很多的礼物,要援朝和何嫚离婚。援朝自然不同意,援朝娘考虑再三,劝说援朝放过何嫚,她终究不是乡里人,在这里扎不下根,除了不会干活,最重要的是她还不能生孩子。
知青们全都回城了。在这片漫漫的黄土地上,只留下了在今天看来是故事的故事。岁月无痕,知青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屋早已倒塌掠为平地,淹没在成片的庄稼地中,随着村里老人们的离世,连那些故事也随风飘去了。
而黄土屋前那无奈憋屈的婚礼,却像一张油画深深地印在了何嫚的脑海中,像一根刺扎在了心里。
那如花的青春……
宋慧珠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