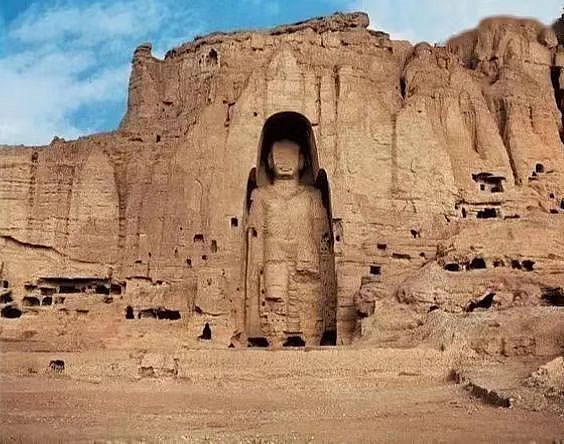你且坐下来,容我慢慢讲给你来听。
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望,很感激你成为了我的聆听者。有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个人心里藏了巨大的秘密,不敢语人,于是就跑到一个树洞前说给那树洞来听,说完后再把那树洞给填起来。我不是那个人,没法把那个秘密烂透在树洞里。那个故事分明是在自欺欺人。我不可能要求你做那个树洞。我知道,当我把秘密吐露给你的时候,畅快一时的是我,背负这秘密的却变成了你。如果要你为我这秘密感到了负重,我仍不能得到解脱的。那么,索性让路边的陌生人都来聆听吧,等说出来,不再成为秘密了,我就把它永久地卸下。
在我的高中时代,曾经喜欢过一位男生。是的,这太正常不过,每个女生在懵懂的青春期都有过懵懂的情思。我记得自上初中起,就没断过被男生的追逐。此刻告诉你这些,我没有任何的炫耀,只有十八二十来岁时才会有那样的炫耀心理。实际上这些给我带来更多的只是麻烦。好在那时学习成绩还不赖,为我抵制了许多的流言。
也许我是天生的多情种——我想这并非我的羞耻,亦非我的荣光。只不过是,唯有爱,才能成为我唯一的秘密。我想澄清的是,高中时代,我真正喜欢过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这名男生。他高我一届,却小我一岁。后来有位校友说,在长麦一中,你可能叫不出班上某个同学的名字,可能不知道校教导主任是谁,但郑少洋的大名你不会不知道。郑少洋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我生命里隆重出场的。
我本可能更早些认识这位成绩优异、个性张扬的学生会主席的。那是高一开学不多久,学校举行了一次秋运会。我记得首轮项目是各年级各同学都需参加的第七套广播体操赛。比赛是从我们高一年级开始的。在体操进行时,一位中年教师忽然急匆匆地走到我们班矩阵队伍的前列来,对正检阅着我们的班主任不知耳语了些什么。我看见班主任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待我们年级比赛结束时,班主任喊住了我,示意我跟那位中年老师过去一趟。那中年老师说,他们班有位女生病了,让我帮忙去代她参加他们班的体操赛。我有些慌,因为刚才在自己班上的队伍里我们班主任都纠正过我的一个错误动作。
于是我在仓促里又加入到这个高二二班矩阵队伍中,站在了前排最边上那个缺角的位置。孰料,刚刚站定,身后却传来一阵哄笑声。我掉过头,用抗议的目光扫视了一眼这群对我的加入不够礼貌的同学,然后保持好体操前的站姿。
高二年级的体操赛也终于跟着结束了,我等不及谁来喊“解散”,拔腿就走。然而没走上两步,便听见身后一声清脆的哨响,接着是一个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停一停,别忙着解散!”
我回过头,看见一名架着茶色眼镜男生的侧影。他朝我瞟了一眼——似乎略带着对我贸然离开的不满,然后对着开始松动的队伍发话:“待会再解散,大家排好队!”
我迟疑了有两秒要不要再归入他们的队伍。但转念想起自己并不是他们班的,班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已完成,再排什么队应与我无干,于是仍旧跑开了。
那人就是郑少洋。但那时我并没敢将他看清楚,甚至这个后来回忆起来的情节其实都很模糊。而郑少洋应早就认得我了,高一下学期开学初,学校各班盛唱校歌的时候,我们班班长尤勇跟我提过几回,他告诉我说,高二二班班长想让我去教他们班唱校歌。尤勇说,他们班没有一个人能唱完整的。
我猜想郑少洋之所以想让去教他们,原因不外乎两点:一,这首校歌是我们语文老师作的词,且由语文老师亲自教我们唱的,我们班的歌唱水平可能比其他班级略强些;二,我去过他们班做广播操,再去教他们唱校歌仿佛顺理成章。
我不敢答应下来,原因也很简单:我对乐理知识一窍不通,因而对自己的唱歌不自信;我也绝无当着一整个陌生班级同学的面唱歌的勇气。但我对这名班长忽然就感到了好奇。
我终于知道了学校里还有郑少洋这个人。那是四月里的一天上午课间时,我坐在课桌前,远远地望见有位英俊男孩的身影忽然映在了窗外——
那名远距离的男孩向着窗口渐渐靠近,像电影画面中的特写镜头推置于我的面前时,我有些怔住了。
我出神地打量着他:棱角分明的面庞,两额浓黑的鬓角,直挺的鼻梁上架着的茶色眼镜使他增添了一种神秘感,嘴角流露出的笑居然是那么摄人心魄!我觉得似乎在哪见过他,但过了几秒我就迅速断定,在今日此时此刻之前,我绝没有见过他,否则这样一位英俊男生,不可能不会在我心里产生印象。
他是来找坐我后排的班长尤勇的,我听他用了略带沙哑的低沉的嗓音与尤勇说着什么。我听出像是在向尤勇交代学生会的某些事情。也许是有异性在望着他,我觉察他似乎有意在将与尤勇的交谈延长。
我不顾尤勇的后来直瞅着我笑,一直盯着直到这位帅哥转身从窗口离去直到消失,然后说:“他是谁?”
“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啊!他就是校学生会主席、高二二班班长郑少洋。”
“郑——少——洋——”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惊讶地说:“他就是想让我去他们班教唱校歌的那位班长?”
是的,我承认,那刻起,一种与融融春光相谐的莫名感觉进驻到我心上来了。
隔了一天,仍是课间时分,前后排的同学都出教室了,平常我也到教室走廊上晒晒太阳的,那天却为着一种莫可言状的奇妙感觉留在了教室里,向着窗外出神。结果窗口真的把那道风景又推到了我的跟前。
我看着郑少洋向着窗口走过来,还拿了一卷什么资料在手中,便知道他又是来找尤勇的,因为尤勇不在,窗口左右别无他人,我的脑海里很快便闪过一个意念:他大概会找上我说话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盯着桌上的书,眼睛的余光瞥到他左右张望了一会。我倒真担心在他左右张望的这一会,尤勇会忽然回到座位旁来了。也许我与他的首次对白注定要在这情形里开场的,果然,郑少洋彬彬有礼地对我说:“对不起,麻烦你帮我把这份资料交给尤勇。”
这回我只当他是名普通的男生,甚至假装正眼都不瞧他一眼,随口就答应说:“可以。”然后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将他手中的资料接过来随意地就放在课桌的一角,并不去关心里面是怎样的内容,而只盯着我桌上的书。
也许他对我的这种与那天见他时的反差态度心有不甘的,又补充一句说:“请帮我转告尤勇,里面的干部名单我已核实过了。”
我点头,一个字:“好。”仍旧盯着我的书。
我能感觉他还想说上些什么的,但他终于走开了,而且有意显得匆忙。
再见郑少洋,是在隔了近半个月后的某周六。那天我坐在教室里看了半下午的书。从教室出来时,我望见有名男生正低着头,在我们教室后的草坪上来回走着看书。开始在教室的时候我就感觉窗外有人在出声地朗读着什么,我竟一直没留意。不过这会他的高声朗读早变成了默读了。而且这会我才发觉这男生居然很像郑少洋。自那天我佯作着无所谓的态度替他把资料转交给尤勇后,我以为会因着我的无所谓再见不到这个男孩了。
我怕我是看错了,便停下脚步来看着他。他却很一副专注的神情仍只是低着头,仿佛全然不曾觉察正有人注视着他——然而,只在忽然间,他猛地抬起了头,朝正傻愣愣地望着他的我递过来一个让我猝不及防的微笑!我赶忙低下头。他的微笑实在迷人的。我懊悔不该这么快就从教室出来,有心转身回去,可又怕被他看穿,只好慢慢踱回宿舍。
吃过晚饭,我早早去教室,远远能望见教室后边草坪上仍有人站着看书,但已不是郑少洋了。
写到这里,我想我得插叙另一个情节,另一个人。你肯定留心到,前面我说过,高中时代,我真正喜欢过两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游方明。
他很关心我。你或许要说,老师关心自己的学生太正常不过。的确是的。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受着班主任老师的关心。但那些老师关心更多的只是学习。游方明不一样,他关心每一个学生,他能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
那段日子,我能敏锐地觉察到,每次的班会课上,他有甚至三分之一以上的话是说给我一人来听的。他常与我谈心,或者在教室外的廊道上,或者就在教室后草坪旁的石子路上。我的微妙的少女情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起变化的。是的,整个高中,班主任在我心中占据的分量其实更大。关于我的班主任,我也可以写上长长一篇文了。那些过往都历时弥久,我已经不准备把它当秘密了。其实我是不情愿把一场感情当成秘密来叙述的。如果是爱,是情愿全世界都来知道的。
我很多情,但你不要以为我滥情,否则我会感到委屈。谁来断章取义地截取事物的表象片面地加以夸大扭曲,都会让我觉得委屈。对他们的喜欢我都是在心里的,甚至带着膜拜的。如果这也值得嘲笑,那么我想那些疯狂的追星族会更加可笑。
我的秘密不只是我喜欢上了他们。其实这同时的喜欢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是有裨益的。因为班主任,我能克制自己对郑少洋的情感。我让他们在我心里互为掣肘,让我对他们的喜欢仅仅停留在暗自的喜欢上。
但事情并不可能按照我的预想发展,中途出了场风波。插进一名毕业班男生。这是名有心计会耍手段的卑鄙男生,他经常在下晚自习时守在教室门口等我,我优柔的性情却未能让我摆脱他的纠缠。游方明对我的关心让这名男生心生疑窦,为讨我欢心他不惜在我面前诋毁游方明,甚至对我欲加非礼。
事情闹得很大,惊动了学校。关于我与游方明的流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请原谅我只能说得简约些。那段日子,我特烦,觉得所有男生都不可靠近且可憎。但两个人例外。是的,游方明那时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还有一个人,郑少洋,他其实也一直在留意着我。
那是晚自习时,班长尤勇把我叫出去,我惊讶地发现郑少洋出现在教室廊道上。当尤勇开口问我有没出什么事时,我很傲慢的态度瞟他一眼,回答说:“不用你来管。”
郑少洋马上接过话茬,很有些严肃的口吻,说:“你们班长是关心你,你怎么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
依旧是那个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我怔了一下,从他口里说出的话,居然会对我产生威慑力。
之后与郑少洋的一次交谈,是在临期末考试的前几天。傍晚,我望见他正站在教学楼上的,我们相视笑了一下,于是他也来到人来人往的操场上,走近我,很自然地我们就聊了起来。当然只是关于学习。很短的几分钟,我们就各自回教室了。
我与郑少洋高一时的整个交往,就这些。我如数家珍地把所有情节都写下来了。到高二时,也只在开学初,在有好几名同学在场的课后,我与他有一两回遇见,就学习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再后来,甚至难得在校园的半路上见到他,郑少洋给我的心动感觉几乎快随时间消失了。
到高二时,我敏感地觉察到班主任对我的态度有所变化了,觉得他不如以前那样关心我了。他不避讳其他女生课后找他聊天,可有一次我有事找他,他一个有意后退几步表示出对我的疏远的举止让我怔了半晌!有一次语文课堂上我开小差,语文老师动了怒,直言不讳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告诉我说,游方明本不希望我读他带的文科班!
其实游方明想让我去别的班级都找我谈过的。现在想来,是我太饕餮了;游方明对我的关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我想要且我以为曾得到的至高点。但我受不了那种落差,到后来甚至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方式来抗拒游方明对我的冷落。我有意在他可能预知的情形下旷课,有意在他的科目测验时交上足以让我考全班倒数第一的答卷。更为极端的,我要让自己的情感转移,于是很自然地就想起了郑少洋。郑少洋或许至今都不知道当年我后来的对他主动出击,其实是更多是因着游方明对我的冷落这样一层缘由。
我这篇《秘密》的真正秘密其实就在这里。
那一天,正是下课的高峰期,氤氲的雾霭里透着冬至的寒气。我迎面望见郑少洋,穿着一套绿色的运动服,夹在下课的学生群中从对面那栋高三教学楼里出来了。我与他的目光撞上了,未用任何言语的表白,解风情的郑少洋瞬间便会意了,且同时我就收到了他目光的回馈。
学姐雨蒙曾对我说,女孩子有两种,有一种眼睛会说话,有一种眼睛不会说话。她说,我属于前一种。我也对此自信。一个眼神的传递,整个世界仿佛都变了。郑少洋的身影日渐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仿佛每一回目光的相遇,我们都要从对方身上进一步验证这微妙情感的真实与可靠性;每一回目光的撞击,我们都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暗合与投契。我走在教室通往宿舍的路上,走在宿舍通往食堂的路上,走在校园里任一条有人行走的小路上,我都冀望着能与他相遇,能从与他目光的对视里感受这温柔的美丽。
然而这个学期很快要过去了。与他眼神的交流也许就仅能这样,仅止于眼神的交流;若再长一些,延伸到下学期末,到他高考,到他离开。我们这一目光的对语终究会像一阵风,消散在校园的空气里,无人知晓;甚至于若干年后的我和他,这记忆不过只如浮光掠影,乍现即凋零!
我不要这样温柔的、暧昧的沉静,我想要打破什么,想要让自己真真实实地感受到这份情感的存在。——因着这样的欲念,我随意找了个借口,于一个周末的傍晚,跟着学姐雨蒙去她班上玩。是的,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郑少洋的班级就在雨蒙班的隔壁。要去雨蒙班上,是得从郑少洋教室旁经过的。
上得楼梯,便听到从郑少洋班上传出来的吵嚷声。他也许在的,要不这个时候他能去哪儿呢?教室内的灯光从他们班的窗口和敞着的门口射出来,映在外面的廊道上,但看不到有人从里面出来。在从他们班的窗口经过时,我有了一丝胆怯,不敢朝里瞥上一眼。我想,如果他在,他定能知道我从这儿过去了的,即使我只是从窗口一晃而过。
曾几回来找雨蒙,这廊道尽头的护栏旁,常立了几个她班上的男生,见到有点外班级的女生来,他们总喜欢大声喧哗的。我想,这回就让他们大声喧哗好了,如果能让郑少洋知道我来过!
雨蒙热忱地向我介绍着面前一位名叫黄庆的男生。换了以往,我会不耐烦的,可此刻我希望我们就定格在这里。虽然我无法想象,就算郑少洋知道,我又能怎么样?
我笑听着这位自称雨蒙哥哥的男生说着要收我为妹妹的戏言,心不在焉地随口答应,目光却在那个敞开着的教室门口游移。这下也好,我们的谈话,把雨蒙班上其他几名男生也引了过来。我倒希望这于我无兴趣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教室熄灯——倘若要那么晚,才见到郑少洋从那个教室门口出来!
众人的侃侃而谈似乎让隔壁班教室有了小小的骚动,不久我就看见有男生出来,但不是郑少洋;接着又出来名男生,在他们那边廊道上来回走上一圈又进教室了;后来又有名男生从那个门内探出个脑袋,朝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旋即缩回去,“砰”地一声把门带上了。
那边的门忽地又开了,那扇门内人员的进出让我形成了条件反射,让我不由自主就将目光移向了那里——这回,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是郑少洋,是郑少洋终于出来了!虽然是在这样黯淡灯光的夜晚,在我感觉里却是那样光彩夺目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看见他手里握了一本书,穿着平日里惯穿的那套绿色运动服。他望了我一眼,慢慢地向着楼梯口那边走过去,口里还唱出了一句歌词:“好想说声我真的爱你……”我听出这歌分明是唱给我听的。他的歌声撩拨着我,让我在忽然间就有种想追上去的冲动。
雨蒙班上这些聊侃的男生渐渐散去,但她的结拜哥哥黄庆还在。我是再无心去雨蒙班上了,却不料引起了雨蒙小小的误会,以为我是因着她的这个哥哥黄庆还在身旁的缘故。雨蒙诡秘地朝我们一笑,独自进教室去了。到最后走廊上只剩了我和黄庆在。我正思忖着郑少洋去了哪里,却见他复又握着书从楼梯口走过来了。这么近的距离,我不敢直视他,低头盯着他的脚步渐渐走过来,然后走进他们班教室。他班上又不知哪个男生探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下,然后把又“砰”一声把门带上了。
我听见郑少洋隐约的说话声从那扇带上的门内传了出来。他就在那门边上,分明也想听着门外的动静!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旁边的黄庆陪着我一直沉默着,我不想教他误会,说:“你先走吧。”黄庆“哦”了一声转身走了,并没有去教室,而径直下了楼。
我仍听得见郑少洋与人说话的声音,就在那扇门边。他的声音撩拨着我,让我脑海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霎时间就作出了一个我自己几乎都意想不到的举动:我走到那扇门边,低低地喊了一声:“郑少洋!”
我以为我的喊声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但那扇门旋即就被打开了,郑少洋看着站在门口惊慌失措的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又有人欺负你了吗?”
我看着他把身后的那扇门轻轻带上,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就朝楼梯口走下去。
这一路行走的过程我们彼此都不曾说话,下了楼梯,直走到前后两栋教学楼之间的一条石子路上,停了下来。
夜空里没有月亮,也看不见一颗星,除了教室里投射出来的灯光,周遭是黢黑的一片。踩在石子路上,脚底下有些冷飕飕的。我意识到寒假快到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踌躇了一会,郑少洋说。我能感觉他把“找我”两个字音念得很重。
“没有。”我低头说,紧张得厉害。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他关切地说。
“没有。”我说。
“那……你找我什么事?”我想他俨然在明知故问。
我本想说:“没有什么事。”舌头一转,自己都不知道下面的话怎么斗胆冒了出来——“难道你会没看出来吗?”
他低了头,踟蹰了一会,说:“……我们回宿舍去吧,天好晚了,站在这里会好冷的。”
我站着没有动。
他侧过身来扶住我的肩,我飞快地甩开他,盯着他的眼——从中投射过含情目光给我的那双眼。
他愣了一下,低下头,轻声说:“其实,你的心思我早看出来了。”他复又用胳膊轻轻搭在我肩上,然后我们并排沿着石子路朝宿舍楼后绕走过去。这一刻我才感觉到天的确很冷了,但我也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这一刻,我与他挨得如此切近,我想他的体温是否经他的手臂传递到了我身上。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换了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胆量。”他用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其实我的感情甚至比一般人要更强烈,但我只能克制自己……我父亲三兄弟,大伯、二伯的儿子都考上了大学,我大哥为我失去了念高中的机会,现在我们大家人都指望着我了……在高二时就已经做到了自我克制,现在我都快面临高考了,更不可能再……如果你真心,我们以后大学校园里见……”
他大概是把这话语的容量与我们所行走的步速掌握得恰到好处,等到他说完最后那句话时,我们快走到宿舍楼门口了。我只顾着低头听他说话,忘了这一路走过来,郑少洋的胳膊一直搭在我肩上。
他停住,把手抽了回去,说:“你先回吧。”于是我朝宿舍走去。我回味他说的话,不知道过了今晚,该怎样来握持这份感情?
我们的期末考试较高三年级提前了好几天进行。在考试之前,我仅在路上遇见一次郑少洋。我不敢去看他,但我听见了他的歌声,他用歌声传递给我这个信息:“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只是不可以……”
那个学期就在一切都毫无头绪里结束了。我不太想回家,可我所做的只有回家。我磨蹭了好久才收拾了大包小包踏上回家的路。出宿舍楼门口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班主任游方明正与一家长站在路边谈话。游方明对我说:“这么晚回家啊?”我几乎带着报复的傲慢口吻,回答说:“是啊,不可以吗?”
辗转了半天到达可以抵达老家的车站,我才发现自己错过了最后一趟车。于是,我在夜色里又返回到长麦一中来。到达学校的时候,我望见高三教学楼的教室里仍亮着灯光。
雨蒙当晚便知道了我还留在学校。她神秘地笑着,开口便问我的滞留是否因为郑少洋。我本想说明原委,终懒得解释。最后我和她约好,等她两天后考试完,与她一道回家。
第二天,一整个上午,我坐在宿舍门口,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听着课间的铃声响过一次,响过两次,响过三次……直到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声响过时,我看见匆匆赶过来的雨蒙。
她说:“走,我们快吃午饭去,吃完饭送你回家。”
“不是约好同走的吗?怎么变卦了?”
“不是我送你,是郑少洋要送你!”
我感觉心倏地跳了一下。我怨怪雨蒙:“你怎么会去告诉他?”
“我才没有呢。是他看到了你还在学校,亲自过来问我的。他问你为什么不回家,我一下怔住了,他旋即就说,‘中午吃完饭我送她回去!’他的语气好像挺严厉的。”
我不满足,又恐雨蒙给我带来的不过是个错误的信息。接着说:“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还说,他还说,”雨蒙瞪了我一眼,“快点去吃饭,要不晚了,等不到他来送你了!”
饭是胡乱地吃的,不知道吞咽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末了,跟在雨蒙后面,仿佛不懂事理的孩子,听凭她带着我走出宿舍。
不一会,郑少洋来了,身边还带了名他班上的男生。我们一行四人出了校门,走在长麦的大街上。这个时候,我是不敢主动与郑少洋说话的,甚至瞟上他一眼都是慌乱的。他也只是偶尔和雨蒙讲上几句关于补课之类的于我无关的话。一路上,他什么话都没有对我说!甚至我怀疑他都没认真来看上我一眼!
远远地就能望见车站了,郑少洋忽然说:“等一等!”我捕捉到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半秒钟,立刻就移开了。
我们停了下来,郑少洋跑向了附近一家商店。不一会,看见他买了两张画过来,是影星周慧敏的画像。一张送给了雨蒙,另一张他把它递给了我。他似乎想和我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很快到了车站,我指望在站台上多停一会,但车很快就开过来了。我走进车厢,郑少洋走上前,站到了车门口。我终于敢大胆地用目光来正视他,但他扭头转向了别处。旋即车门就关上了。
我握着卷好的已成为我信物的那张画,知道却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那个寒假,我做了个梦,梦见一口古老的井,我和郑少洋双双坠入那井里。井沿上,站着个人,我的班主任游方明,对着我漠然相向。
那是高中三年间我能记得的唯一的梦。
终于盼到了又开学。你肯定能够猜想到的,那一时候,我的班主任游方明在我心里淡下去很多了。尽管那时,我已意识到我主动追求郑少洋时的非纯粹动机,但经了这寒假,我准备让自己对郑少洋的恋情就这样默默下去,与游方明无干了。
我坐在教室窗口边,望着对面那栋教学楼的那条廊道出神。——我得补充,这个窗口的位置已从高一时前面换到后面来了。高一时游方明动了全班同学的座位都不曾动我的位置,到了高二我的座位顺理成章地被忽略了。这但个位置却为我遥望对面教学楼的那条廊道提供了恰好的便利。班上小组的座位是半个月就要和其他组对调的——也就意味着,两星期后我们这个组得换到靠教室门的那个组,那时我的座位就只能靠着教室的那堵墙了。因此,现在我坐在的这个靠窗口的位置,是于我学习之外的最好的位置,因为它可以让我不定时地望见对面教学楼那条廊道的郑少洋!
我坐在窗口边,望着对面那栋教学楼的那条廊道出神。每天吃过了早餐,午餐,晚餐,我不再多在宿舍里耽搁,而是早早来到教室,坐在这个游方明曾解释说因为我个头高而得到的倒数第二排的位置上。自坐到这个窗口边,我是早自习时极少外出进行晨读了,除非我能判定郑少洋绝对不在教室。当我确信郑少洋不在教室里的黄昏,我会捧了书去室外看的。书中的字里行间总参杂了一半他的影子!每天每堂课的课间我都一动不动地守在我的窗口,挨到放课我总是守到他们班的教室人群散去才肯离开。我不知道每天要有多少回假装无意却分明有心扭头去看窗外,去搜寻对面那条廊道上的那个人!
我无法设想这一个学期是否就这样在我的守望中持续下去,却在某一天的傍晚,郑少洋来到我们教室门口找我来了。
我看着他飞快地下了楼梯,向着我这栋教学楼走来。这学期一开学我就发现他理了个极短的平头,后来我听说,其实他弄了个时下正流行的发式,却被他班主任训斥了一顿,就把发型又改过了。
我还未猜测到郑少洋要来这边干什么,他的身影已出现在我们教室那边的窗口。
很快班上就有同学过来告诉我说:“外面有人找。”
我忐忑不安地走出了教室。出了教室,我才发现他手里还拿了一本书。他脸上掠过了一丝严峻,那种严峻立刻就对我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才能够完全相信他的学生会主席身份是非他莫属的。
走到楼梯口的廊道边他停下来,然后我们一起伏着廊道边的栏杆,凭眺着前方。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他说,“我现在只要一看到你,就一点书都看不进去。我求你帮帮我,我只有这一个学期了。”
我很快明白了他要我帮忙的意思,最好连在他的视线里出现都不要!
“我并不是否认你在我心中的位置,”见我不语,他补充说,“我也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但我别无他法,我对不起你。”
“不,”我赶忙说,“是我对不起你。”我奇怪自己竟这样容易流泪。
“不管怎样,你必须帮助我。”他加重了最后这句话的语气,然后转身“咚咚”地跑下了楼。
因为郑少洋告给我的话,我几乎不敢守在那个窗口边了。好在没过几天小组就互相轮换了位置,我们这组搬到靠进教室门的那组了。当然,我的座位仍是倒数第二排,这是不可能变更的!
课程表上的那些课每天都毫无变更地上下去。耳朵里是不断的上课铃声、不断的下课铃声,那道道紧逼的铃声像是在催促着我有限的青春,催促着我有限的生命。我想要将时光滞留,把大学梦极力地推向遥远,却过早地把爱情梦招揽在了身边。
我的座位又换到那个可以望到对面那栋教学楼的窗口来了!坐在窗口,我情不自禁地扭头就朝着那边的廊道上张望!
不止是课间时分,就是上课铃声响过,廊道上空无一人之后,我都要条件反射地朝着窗外痴痴地凝望上一回。我不知道郑少洋这段期间是否想起过我,为了不致让他感觉我又回到了这个窗口,我选择在听不懂的物理化学课的课前,偷偷溜回到宿舍去。
这种无声的游戏不知他能否知道能否看懂。逃了几次课后,觉得这终归不是办法,于是我又规规矩矩坐到教室里了。依然是有些犯着贱地对着窗外凝望,于课间时在麇集廊道里的人群中寻觅着他的身影!唉,让我怎么帮他,我怎么消失在他的视线里?难道我坐在教室里自己的座位上,偶尔扭头向窗外的动作都成了一种罪过吗?事实上开学以来我几乎没在课后的其他地方见过他!即使每日在这窗口,我也难得匆匆瞥上他一眼!
这天的晚自习课间时,分在了理科班许久没打过交道的尤勇忽然来找我。尤勇望了我一眼,说:“郑少洋找你。”
“郑少洋”三个字让我感觉心猛地跳了一下。我左右张望,但不见郑少洋的人影。
“他在楼下,操场上。”尤勇说。
我飞速扫了一眼操场。操场上黑黢黢的,什么都望不见。我很快意识到郑少洋找我的缘由和头次差不离,但想见他的欲望却占了上风。
尤勇边走边告诉我说:“你要理解郑少洋。他告诉我说,现在是一看见你就静不下心来,一点书都看不进去,每天他都想法躲起来,躲到你涉足不了的地方看书。可校园就这么点大地方,他又能藏到哪儿去?”
“他说他现在学习成绩已在急剧下降,原先一直在班上前几名的,这几次摸底测验,连中上都快赶不上了。他们班主任不知怎么听说他竟在这节骨眼上与人恋爱,把他大骂了一通,对他的高考都不抱希望了。”
说着我们就下了楼,走到了操场上。待走到距他一米远的地方我停了下来,从教学楼里投射到此的黯淡灯光让我看清他原来背对了我。
——大概他是将学生会主席和班长的双重身份培育出来的颐指气使的态度嫁接到情感上来了,很生硬的口吻,他说,“为什么我说的话你不听?你想要怎么样?”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了,我讨厌你,你让我感到心烦!”依旧是生硬的口吻,说完,旋即朝他教室方向跑过去。
我已是泪零如雨,立刻也掉转身朝自己教室跑。轮到尤勇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那是生命里心头一次被掏的感觉。但郑少洋这样的态度给我,或许只是为了让彼此将这感情迅速消灭掉?我忽而想起雨蒙告诉过我,那次郑少洋送我去车站返回时,曾向她打探我厌恶怎样的人。雨蒙说郑少洋是想做个让我讨厌的人。想起这些,我的委屈又减轻些了。我觉得我的确该为郑少洋真正做些什么了。我与他之间无论如何是我错在先。
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教室里首先做的,就是将我位置旁边的这扇窗关闭起来。然而窗子关了不到半分钟,前后排的男生都同时夹击抗议起来,说又不是大冷天,大清早的,关窗做什么!其中一个毫不客气地就把窗子推开了!
没有办法,我便将自己的座位与同桌对换了一下,这样最靠近窗口的那个人总该不是我了!同桌一脸的诧异望着我说:“你是怎么了?又是关窗又是换座位?”
我回忆起尤勇告诉我的郑少洋班主任对他高考不再抱希望的话,怀疑郑少洋会不会像我在受了班主任冷落一样自暴自弃。在忽然之间我便想到了去找他的班主任。也许我有必要去向他的班主任澄清原委,承担起我该承担的责任。我要让他的班主任重新给他以鼓励,以高考必胜的信心。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酝酿怎样向郑少洋的班主任道白,因为怕心慌,怕唐突,我甚至把一些应该说的有关内容反复在心里默记下来,就差没写在纸上了。
我怕自己陷入长时间的犹豫里,打定了主意,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找郑少洋的班主任。高一那次校运会,郑少洋的班主任俞老师曾把我带到他班上参加过体操赛的,可此刻我对他的印象早已全无。
到俞老师家门口,定定神,然后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女孩,她问找谁?我说:请问俞老师在吗?她说,你等一等。然后便进里屋去了。
这“等一等”的时间里,我忽然胆怯起来,脑海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当俞老师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这空白状态延续了几秒钟后,我总算记起了我要说的第一句已知故问的话:“请问,您是郑少洋的班主任吗?”
我承认即使早已作了心理准备,此刻仍消灭不了内心的紧张感。我在脑海里搜索着在他点头默许之后接下来应该说的话,岂料这位俞老师在点头之后,很快就悟出了我是谁——不过并非是记起了我曾在他班上参加过体操赛,而是悟出所谓的“郑少洋在与人恋爱”的那个对象就是我——“怎么,他欺侮你了吗?”他很严肃的表情问道。
“哦,没有,没有的。”我赶忙说,语言立刻变得结结巴巴的,因为他的问话把我准备好的“台词”给打乱了,“……不是,郑少洋学习成绩的下降,其实……都是我造成的……是我影响了他的学习……我希望你不要去责怪他……”
他轻微地点了点头,不等我把我终于记起来的台词衔接下去,接着问道:“你是哪个班的?”
我原想等我把造成郑少洋学习下降的缘故往自己身上揽过后就离开,也不必让俞老师知道我是谁,这样就行了,此刻他一问,问得我更心慌,我想撒谎随便报出一个班级,但舌头拐不了弯,如实就回答出:“高二文科班的。”
大概是我的声音听起来像蚊子哼哼,他又重复问了一遍,待我回答后,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在把自己名字告诉给他的刹那,我感觉自己就像逃亡了多年的案犯,终于前来自首时得到的却仍是死刑的宣判。
俞老师点头说:“好,下次我们找个时间再聊。”
像逃离第一作案现场一样,我心“咚咚”跳着朝教室奔。起初我还只是些微的懊悔,从俞老师那回来我是非常后悔不该去找他了:缘由就是他说的下次找个时间再聊。我实在不想把这事再牵扯到下次。
“下次”到了期中考试过后,时间过了有半个月,俞老师于晚自习时径自走到我们班教室来了,居然一进来就知道了我坐的位置。那晚游方明恰好也在,游方明破例地坐在了我后排的一个走读生的空座位上。开始我觉得诧异,很快我明白了:我与郑少洋的事俞老师已告诉游方明知道了。
那晚我向俞老师谈起了我和郑少洋交往的经过。我知道我不是来倾吐这些的,我必须承担起我该承担的一切。或许在感情里谁主动出击,谁就该来多担待。
“你和郑少洋之间的事,前段日子他主动找我说过一些了。”俞老师说,“我就觉得奇怪,你们就这么几回交往,怎么就都陷入得这么深?他说他现在看见你就一点书都看不进去。我就责骂他,你要对人家没感觉你干嘛看不进书?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老缠着他!”
俞老师说完最后这句,就直盯着我,似乎我神情中的反应是他能掌握的关乎郑少洋学习成绩下降的重要因素。
“我没有。”我说,可我的回答并不坚决,因为我忽然怀疑,我日日坐在窗口对着那条廊道张望,是否也算是对郑少洋的一种纠缠?
显然是我的不够坚决让俞老师有所怀疑,他又说:“可他就一口咬定说,你天天纠缠着他,搅得他没法看书!”
这样的语言让我感到一丝激怒,从而让我坚定了信心说:“我没有缠着他,我和他这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单独在过一起!”我暗想,何止是没单独在一起呢,每天是偶尔瞥见他一回都难得!
“这么说,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感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伤害,但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压根就不是想要让与俞老师的谈话换取来偏袒我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说:“这都怪我,明知他都进入高三了,当初不该先主动找他。我没想到他的学习会下降那么快。”
“你说是你主动找他,可我认为是他主动找你!你高一时遇到事自有班主任帮你解决,要他来插手干什么!你这样为他袒护,你知道他想让你做什么吗?他想让你转学!他脑子里有鬼,他把他成绩的下降全归咎在你一人了。”俞老师说,“郑少洋是个自私的人,他不值得你为他这样。年轻人,早恋不可取啊。”
……
这场谈话过后,大约过了近一星期,那天课间时,有个陌生男生来找我,微笑着递过来一张纸条。尽管我迅速就意识到这字条里或许藏着什么玄机,但那微笑的示意,让我的行动还是先我的意识一步,把那张字条接了过来。
那个陌生男孩转身就跑了。我展开纸条,顿觉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字条是郑少洋写来的,尽管我这是头一次看到郑少洋的字迹,尽管他的落款并没有署上他的名字。我颤抖着手把字条扫描完卷起塞进上衣口袋,感觉到心内的血直往上涌,连日来对他的内疚都教此刻的愤怒遮没了。我想即刻就去了对面那栋教学楼,冲到郑少洋的班上,把他拉出来质问!然而从座位上起身的时候,我的双腿似乎不听使唤,有些僵立不稳了。
我晃晃悠悠地出了教室。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了楼梯的,满脑子里是字条上落款为“一个讨厌你的人”写下的不堪的污言秽语。纸条上流露着对我去找过他班主任而他大概又受了班主任训斥的极为不满。我的思维变得混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暂时性失忆症,是不是平日里真的去纠缠了他而我竟全然不知——否则郑少洋何以如此待我?我一边下楼,一边在脑海里冒出许多古怪的念头。
然而我并没有冲上对面那栋楼,冲到他班上去,最终我的脚步踅回了宿舍里。我的思维仍然有些混乱,好半天才让自己冷静,确确实实,这样一张侮辱性的字条就是他写的——它把他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然毁灭了!
“我早对郑少洋没好感,嚣张跋扈,不可一世!”雨蒙愤愤地说。当天晚上她又神秘兮兮地来找我,说,有几名男生很为我抱不平,想替我教训郑少洋,只要我点头,足以让郑少洋在医院躺上半个月甚至参加不了高考。
我忙摇头。那样的结果对我毫无意义。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什么都没发生。其实,当雨蒙告诉我说郑少洋近段时间整个人都像蔫了一样时,我又动了恻隐之心。我是希望他能顺利通过高考的。俞老师那晚曾告诉我说,如果郑少洋当年考不上大学,以后也别想再考上。其实我已有了思想准备,万一他没考上再来长麦一中复读,我都有转学的打算了。
八月返回学校补课。校门口的黑板报专栏里,每年这个时候都公布着高考录取者的名单。我搜索到了他的名字,他考上了北方一所高校。
九月里正式开学。我也上高三了,也不必转学了。我们的教室换到了郑少洋曾经教室的隔壁。好像是开学的没几天,在宿舍楼门口见到接替郑少洋学生会主席职位的班长尤勇。尤勇问我头一天去哪里了。头一天没有课,我不在学校,但至今我却想不起自己去了哪了。尤勇说:“昨天我和郑少洋到处找你,把校园都找遍了,都没见到你的踪影。”
我以为我听错了,说:“你和谁找我?”
“郑少洋。”尤勇说,“他要去大学报到,昨天的火车,特地来这里找你,想要你送送他。”
这一刻,我曾感受的委屈全然烟消云散。
“他说了,他会写信来。”尤勇说。
我不敢细问,郑少洋的写信,是给尤勇还是我。我把自己的幻望降到最低点。一整个学期,我和尤勇都没有收到郑少洋的任何音讯。但我却一直有种莫名的直觉,总感觉会再见到他一次。
我的确见到了郑少洋。下学期的开学初,上午,我走在校园里,半路里有名男生把我拦住了。是郑少洋。
北方的大学生活在半年内就让郑少洋起了巨大变化。身体竟有些微胖,他的茶色眼镜也不戴了,手里还拿了一支烟。我看他在我面前吸烟与掸烟灰的动作已非常娴熟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最初见他时的那个纯情男生永远消失了。
郑少洋问我:学习还好吗?
我淡淡笑着,摇摇头。我记起了他曾说的“大学校园里见”。
我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明天的火车。
仿佛是怕我有事,过一会他说,你先忙吧,回头我再去找你。
我于是一路走过去了。
我等到了晚上,我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我知道今晚他还在这里。我仿佛隐约听到了他在外面与人说话的声音,但我矜持着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动。
第二天,我们正式上课。中午,我遇见了尤勇,他说,郑少洋走了。
关于我与郑少洋的故事,到这里就全结束了。我也准备彻彻底底把它放下了。你也和我一起放下吧?可能你觉得还没完。是的,这份情感的结束让我重又得到了我的班主任游方明的关注。得失之间的况味,我想外人无法来感同身受。但也许你会更明白一些我,更明白一些这世上有些东西,守不住非因我亦非因你,而只因这充满变数的不居岁月。
何美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