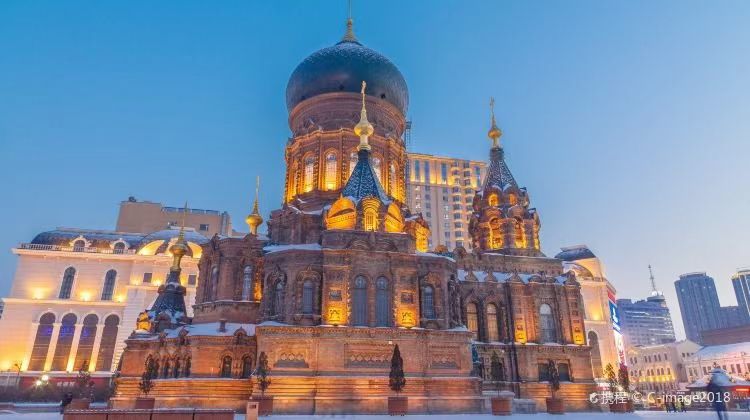四 不幸的婚姻
农历八月十二日,吴德来到周小红家定亲。
“姐姐,你愿意嫁给吴德吗?”周小青问周小红。
“姐姐不愿意呀!”周小红说。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和他定亲?定了亲不是就要嫁给他吗?”
“没有办法啊!咱娘生命垂危时,没有钱抢救。姐姐答应:谁能救娘的命,姐姐就嫁给谁。吴德出钱救了娘的命,姐姐就得嫁给他。姐姐还能说话不算数吗!”
“咱还他钱不行吗?”周小青仰起头看着姐姐的眼。
“许下的承诺怎么可以反悔?”
“反悔怎么了?我看他不是好人。”
“再说了,哪里有钱还她?”
“没有钱,先欠他的。等我长大了去挣好多好多的钱,到那时候再还他。不行吗?”
“我的好妹妹,你这么好心。姐姐谢谢你了!”望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妹妹那天真的样子,周小红蹲下身抱住了她;委屈、无奈、感动、酸楚、悲伤……心中五味杂陈,热泪涌上了眼眶。
吴德拿来了肉、鱼、粉条、大馒头“四色礼”和一身碎花布料、一斤红色毛线等定亲的礼物,还有60元定亲钱。
定亲的酒席上,周大娘请周伟和大嘴两口子过来陪吴德,周伟和吴德从中午一直喝到天黑。周伟喝醉了,大嘴扶他回家去。吴德喝得两眼通红打着酒嗝步履酿跄地来到周小红的闺房,借着酒劲赖在房里不肯走,说“定了亲就是夫妻了”,要住下和周小红“同房”。
周小红说:“不行!还没有领结婚证,就不是夫妻。这个道理你也不懂?”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来吧!”吴德涎着脸,抱过周小红按在床上就去亲嘴,一股刺鼻的气味直冲周小红的脑门。周小红挣扎着躲闪,可是吴德力大,哪里躲闪得开,一张喷着酒气的臭嘴压上了她的红唇。周小红咬紧牙关,闭住双唇,气也不敢喘;伸手去推吴德,一失手,把桌子上的茶具碰到了地上,哗啦一声,摔得粉碎。吴德一惊,放开周小红,回头一看,见是砸碎了一把茶壶和几个茶碗,回过身来又要纠缠,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周大娘进来了,见周小红刚从床上爬起来,衣偏发乱,知道是吴德胡搅蛮缠,指着吴德的鼻子说道:“别以为花了你几个臭钱,周小红就是你的人了。没有娶进门,周小红还不是你媳妇,不准你碰她一指头。”指着大门,“出去出去!还不快滚!”
吴德恨恨地瞪了周小红一眼,悻悻而去。
周小红认真地刷了牙、漱了口,又用香皂洗了脸。以后吴德多次晚上过来骚扰,周小红总是躲得远远的,或是和小青妹妹在一起。吴德想和周小红亲近,却始终没有机会下手。
订亲的第二天,周大娘让周小红把上次借的钱一一还清,周小红还给姥姥家和姨家每家多留下两元钱。
去小姨家还钱时,小姨依旧站在高高的山石上,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远处的大海。秋风吹拂着她凌乱的秀发和已经褪色的衣裳,本来白净的面皮比上次来借钱时黑了,如花的美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鲜艳,有些疲惫,有些憔悴;神情木木的,呆呆的;灵魂已经飞到海峡的对岸,躯壳也快化作望夫石了。
姑夫是供销合作社经理,利用手中掌管物资的权力勾引女售货员和附近的年轻女子,和她们乱搞男女关系。一个大了肚子的姑娘在家长的陪同下向政府告发,姑夫被开除回家,戴上坏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周小红去还钱时,姑夫正在扫大街。周小红想起借钱时的情景,也把钱扔到地上,转身走了。姑夫低头扫街,见扫帚旁落下五元钱,抬起头来,看见周小红离去的背影。他弯下腰把钱拾起来,吹了吹上面的土,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
报复的快意过后,周小红立刻发觉自己的做法不对:不管当初是什么态度,毕竟姑夫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解囊相助,凑够了钱领回小麦,解了全家的燃眉之急。这是恩,不是仇。她走出二十多米又返回身来,在姑夫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姑夫!侄女失礼了,对不起!”
几个月不见,姑夫已经今非昔比,面容明显地消瘦了,更是没有了往日的气焰,一下子老了许多。他热泪盈眶,讷讷地说:“小红,我说过的,不用你还,怎么……”两行浊泪沿着苍老的面颊缓缓地流向嘴边。
周大娘亲自去了趟学校,找到周小青的班主任孙老师。孙老师把周大娘让进一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搬来一把椅子,说:“大娘请坐。”又去沏上一杯香茶,放在周大娘面前,说:“请喝茶。大娘是为周小青的事来的吧?”
周大娘见孙老师是个女的,二十多岁年纪,中等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一脸的书卷气(一个人读不读书,从脸上就看得出来),虽然说不上多么漂亮,但是气质儒雅,举止文明。
周大娘说:“孙老师,给你添麻烦了。我来问问:这时候交上学费和书钱,能不能让周小青继续上学?”
孙老师说:“大娘,这事我做不了主。请您稍等,我去问问校长,行不行回来再告诉您。”
孙老师见开学没几天,不知道能不能收下周小青,就去找校长商量。不大一会儿,就回来说:“大娘,校长答应了,明天就叫周小青来上学。书的事我想办法解决。”孙老师收下学费和书钱,把周大娘送走。下午,孙老师把学费交到总务处,又去了趟书店,凑齐了一套课本。
第二天,周小青来到学校。孙老师知道周小青家里困难,把课本和学费收据给了她,书钱也退还了她,说:“周小青,这些书都是发行完剩下的,书店里不要钱。”其实,2元4角1分书钱如数交给了书店,一分不少,是孙老师自己垫上了——老师对学生说了谎。
之后几天放学后,孙老师把周小青单独留下,帮她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周小青勤奋好学,很快就赶上了学习进度。
这天夜里,周小红刚睡下不久,就见陈明来了,说:“小红姐,我哥请你到我家去一趟。”
周小红跟着陈明来到他家。陈聪从屋里迎出来,拉着周小红的手说:“我二叔从海外回家探亲,给了我一笔钱,因为他没有孩子,百年之后还要我去继承他的遗产。听说你和吴德定亲了,你要是不愿意嫁给吴德,就把亲退了吧!”
周小红高兴得心花怒放,连连点头说:“好,好!马上就退!”
不一会儿,吴德腆着肚子来了。陈聪甩给他500元钱,要他和小红退婚。吴德见钱眼开,连忙点头答应了陈聪的要求,捧着500元钱屁颠屁颠地走了;出门时还回头看了周小红一眼,骂道:“谁稀罕你这个破货!你信不信?老子有了钱去找个原装的。”
周小红高兴地扑到陈聪怀里,说:“聪哥,谢谢你!我知道你爱我,咱们两个结婚吧,我娘已经同意了!”陈聪却不理她,把她放在地上,转身而去。
“聪哥!你别走,等等我!”周小红边喊边追,却怎么也追不上,一会儿便不见了陈聪的踪影。周小红觉得浑身发冷,一睁眼醒了,被子已经蹬到床下。夜里下起了秋雨,风吹雨点打得窗户唰啦唰啦响,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早上,周小红早早来到G镇小学门口。红艳艳的合欢花不见了,树上已经结满成串的荚果。见陈明来了,她问陈明:“你海外的二叔最近有没有回来过?”
陈明说:“没有啊,怎么了?”
周小红说:“没有什么。”她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一个月过去了, 吴德催着周小红结婚。
周小红说:“嫁妆还没准备好,怎么结?”
“那你赶紧准备嫁妆。”
又一个月过去了,吴德又催着周小红结婚。
周小红说:“结婚证还没领,怎么结?”
“今天就去领结婚证。”
“我还不满十八周岁,不够法定的结婚年龄,婚姻登记处不给登记,怎么领证?”
第三个月过去,已经到了农历腊月十八。这天,吴德领着周伟和大嘴,一齐来到周小红家。吴德对周小红说:“你信不信,我已经去派出所查过你的户口,你是1940年2月5日出生的,已经满了十八周岁。今天就去登记领结婚证!”
周小红看看娘,娘在低着头擦眼泪。
周伟说:“大婶,你这条命是吴德救的。当时小红妹妹答应了人家,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且亲也定了,你可不能反悔啊!”
“别胡说!”大嘴瞪了周伟一眼:“大婶是那样的人吗?大婶几时反悔了?小红妹妹也没有反悔。前些日子不是年龄不够吗?现在够了结婚年龄,人家今天就去登记领结婚证。”
周大娘说:“小红,去吧!知恩图报是做人的本分。再说了,咱也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家。这是你的命,天命难违啊!”
周小红无可奈何,满肚子委屈地和吴德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
吴德终于盼来了结婚的日子,日子订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下午,吴家派了四个人来抬嫁妆,把一对衣箱、一架梳妆台和一套被褥几件衣裳抬走。四个人在半路上停下了来把衣箱内的糖果分着吃了。夜里开始刮起大风下起大雪,第二天依然纷纷扬扬下个不停,地上积了厚厚的雪,村舍、农田、小河、远山到处都是一片白。
当时娶媳妇已经不用花轿,改用自行车,新郎自己骑一辆,再请一个年轻人(俗称“小兔子”,一般是新郎的弟弟或堂弟)骑一辆载新娘。吴德结婚因为雪大路滑,自行车也没法用,只好步行,好在路程不远。
周小红抱着娘哭了一场,又亲了亲妹妹周小青,然后换上一身红色的新衣,薄施脂粉,头上戴一朵绢花,就跟着吴德向吴家走去。没有“送客”,只有媒人周伟和大嘴两口子和四个吹鼓手一路陪伴。路上风猛雪狂,寒气刺骨,吹手的嘴冻歪了,吹出来的唢呐声不成腔调;鼓手的手冻麻了,打出来的鼓点乱了节奏。吴德倒是欢天喜地,不时地看看新娘子如花的面容,恨不得一口吞下;周小红已经被连日来的痛苦麻木了神经,像是献上祭坛的牺牲,机械地迈着步子跟着吴德前行。
吴德有个老娘,七十岁了,眼花耳聋,喜滋滋地坐在堂屋中间,等着新人拜天地。
大雪封了路,路远的亲戚朋友来不了。因为天气原因,一切仪式从简。
拜完天地,宴请宾客。酒足饭饱的客人们一个个打着饱嗝离去;闹房的年轻人见天气不好也渐渐地散了,离开洞房时他们议论纷纷:
“哎呀!这新媳妇真漂亮!就像一朵鲜花。”一个女孩说。
“可惜啊!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女孩身边的青年长叹一声。
“吴德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一个中年妇女骂道,看电影时遭吴德猥亵的女子是她的妹妹。“世事难料啊!想不到癞蛤蟆还真能吃到天鹅肉!”
“媒人那天给我提亲,说的就是这个周小红。我娘说她作风不好,高低不同意。悔死了!悔死了!”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恨得直跺脚。
……
见闹房人已经离去,吴老太太累了一天,也早早休息了。大嘴端着盘子来到新房;盘子里一壶红酒,两个酒盅,两双筷子,几碟小菜,一盘喜糖。大嘴先剥出两块糖,分别送到吴德和周小红嘴里,说:“祝你们新婚幸福,甜甜蜜蜜!”二人把糖吃了。
大嘴又斟满两盅酒,分别送到二人手里,说:“吴家兄弟,小红妹妹,今天你俩喜结良缘,喝个合婚酒吧。”吴德接过来一仰脖子干了,一连干了三盅。
周小红说:“嫂子,我不会喝酒。”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不会喝也得喝。”
周小红勉强饮了三盅,已经微醉,腮上现出两朵红晕。
大嘴说:“祝你们恩恩爱爱,早生贵子!”说完,撤去杯盘,掩上门,退了出去,扶着喝得醉醺醺的周伟回了家。
屋里只剩下吴德和周小红两个人了。周小红心里一阵莫名的慌乱,她感到绝望,已经麻木了的神经又突然清醒起来。难道真的就要和这个连看一眼都觉得恶心的人同床共枕?她对吴德不仅仅是怕,更多的是厌。吴德的丑陋,吴德的肥胖,吴德的气味,吴德的粗俗,哪一样都惹她生厌。她觉得自己和吴德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物种。微醉的她想起了陈聪:陈聪的仪表,陈聪的体态,陈聪的风度,陈聪的气质;自己和陈聪才是同类。心爱的人儿,你在哪里?就在周小红思想纵横驰骋的时候,吴德也没有闲着,他先把自己里里外外脱了个精光,一个全身赤裸的吴德赫然站在周小红面前:黑黑的皮肤,臃肿的身材,胸前的黑毛越过硕大的肚子一直蔓延到跨下,大腿根部还有一块杀猪时不小心被猪咬伤留下来的疤痕。——裸体的吴德比平时更加丑陋,吓得周小红不敢睁眼。屋里生着火炉,正在燃烧的木柴噼噼啪啪地响着,炉火正旺。吴德醉眼迷离,嘿嘿嘿地笑着,露出满嘴黄牙,向缩在床角的周小红一步步走来,活脱是一只非洲大猩猩。
“小美人,来吧!看你还往哪里躲。你总不会以为今天晚上我还会放过你吧!”吴德喷着酒气,上前来扒周小红的衣裳。
周小红突然感到恐怖,像是世界末日到了,心里一紧张,感觉下身不对头,算了算日子,知道是月经来了。她说:“吴德,你别胡来。今天晚上的确不行。”
“什么?今晚你还想不让我肏?反了你了!”
“我来例假了,再等几天行吗?”
定亲以来四个月焦急地等待积累起来的怨和恨,在吴德心里形成了一座“火药库”,一个“等”字就是一根导火索,把这座“火药库”点燃了。
“等?还叫我等?要我等到什么时候?今天说什么也不等了!听见没有!”吴德的愤怒如冰雹般倾泻,最后四个字已经变成了咆哮。
吴德扑上来就是一阵猛烈地撕扯。周小红奋力挣扎,怎奈人小力微,敌不过吴德的凶狂;衣裳鞋袜扔了一地,不一会儿就被扒了个精光,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少女光洁白皙的身躯,肆意地展示着肢体的柔美,吴德看得目瞪口呆。周小红拉过一床棉被盖住身体,吴德把棉被抢过来扔到一边,扑上身来压住周小红。周小红拳打脚踢,不肯就范。搏斗中周小红虽然处于劣势,吴德的欲望却始终无法得逞。
突然,吴德放开手下床去站在床前,盯着浑身赤裸的周小红笑了,那笑声又古怪,又恐怖,周小红听得毛骨悚然。她两手本能地护着挺拔的乳峰,夹紧修长的双腿。吴德不慌不忙地从床底下拿出两条长长的绳子和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把刀放在嘴上叼着,压住周小红的身子,手脚并用把周小红牢牢地捆绑在床上:两臂分开,分别绑在床头两边的床柱上;两腿分开,分别绑在床尾两边的床腿上,整个人就像一个“大”字。尽管周小红奋力反抗,吴德还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周小红何曾受过这等羞辱,她愤怒地大骂:“土匪!流氓!你不得好死!”
吴德反倒不生气了,因为捆绑得顺利——毕竟捆一个弱女子比捆一头待杀的猪容易得多,把刀从嘴里取下来放在桌上,说道:“看来这个用不上了。”周小红奋力挣扎,双手乱舞,双脚乱蹬,可还是动摇不了分毫,绑得实在是太结实了——屠夫吴德的专业本领派上了用场。周小红看着桌子上的杀猪刀说道:“吴德,你杀了我吧!”吴德笑道:“我怎么舍得!”他嘻嘻地笑着,端过蜡烛,对着全身赤裸的周小红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端详,像是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这里用手摸摸,那里用舌舔舔,又像是在享受一桌美味大餐。
忽然,吴德似乎吃了一惊,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吧?”
他重新端起已经放下的蜡烛,又仔细研究了一番,满意的说:“原来还是个原装!先前冤枉你了。不过,倒是真的来了月经,这也没有关系,爷爷实在等不得了!”
周小红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一头钻了进去。她两眼含泪,柔声说道:“吴德,求求你了,饶了我吧!”
吴德专心致志,对于周小红的祈求没有理睬。
“啊!”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划破了夜空,尽管雪在飘,风在吼,声音还是传得很远。新婚之夜的洞房里,没有软语温存,没有怜香惜玉,没有温柔体贴,更没有款款深情;有的是:贪婪的肉欲,疯狂地占有,残忍的强暴和兽性的发泄。伴随着这一声凄厉的尖叫,周小红在有如被撕裂般的痛苦中结束了她一十八年的处女生涯。
……
第二天早晨,雪停了,天晴了,太阳已经升起老高, 洞房里还是没有动静。
吴老太太放心不下,推开虚掩着的房门进去看看,只见儿子睡得像个死猪,鼾声如雷;媳妇蜷缩在床边,面色苍白,无声无息;被子和褥单上有零星的血迹。
原来周小红被吴德几次施暴,痛得死去活来,心里想:快死了吧,死了就不用受罪了。她几次伸手想去拿桌子上的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吴德见状下床把刀藏起来了。半夜以后,吴德累了,翻身下来,呼呼大睡。周小红想到了逃,逃出这个令她伤心之地。虽然捆绑她的绳子早已解开,可是被捆绑过手脚又痛又麻,哪里跑得动?何况还是风雪之夜!火辣辣地痛楚和吴德如雷的鼾声又使她难以入眠,想起母亲关于命运的话,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我的命也太苦了吧!天老爷太不公平,为什么对一个弱女子这么残酷?人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从来不做恶事,一心向善,为什么不得善报呢?直到天将晓时,周小红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吴老太太见周小红呼吸平稳,没出大事,见炉火已熄,给她掖了掖被子,叹了一声:“可怜的孩子!”掩上门,踮着一双缠过的小脚,仄仄歪歪地走了出去。
天将午时,吴德和周小红才先后醒来。吴德见妻子美丽,又要上来求欢;周小红抡起右臂,给了吴德的左脸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手都痛了。吴德不但没怒,反而笑着说:“媳妇打得好!小手真软和,一点也不痛。”又向周小红伸过右脸来,说:“媳妇,再打这边。昨晚是我不好,粗暴了点,对不起你。再打一下解解气。”弄得周小红哭笑不得,没有再打,只是狠狠地骂了一句:“无耻!”
吴老太太见新媳妇整天愁眉苦脸,怏怏不乐,再想想被子和床单上的血迹,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见儿子出去了,老人来到新房,拉着周小红的手说:“孩子,委屈你了。我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东西。吴家两代单传,他爹五十岁上才有了他,拿着当宝贝疙瘩溺爱,把他惯坏了。要是他再敢欺负你,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周小红见婆婆这样通情达理又善解人意,不好意思再向婆婆吐露自己的痛楚,只是淡淡地说:“娘,谢谢你!”
第三天,沉迷于新婚中的吴德终于想起了答谢媒人。虽然天晴了,可是地上的雪却没化,吴德这次没有食言,提了两个猪头,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敲开了周伟家的大门。
大嘴连忙迎上前来,见吴德满脸喜气,说:“ 新郎官来了,恭喜恭喜!”
吴德把猪头交给大嘴,双手在胸前一抱,说:“同喜!同喜!”
收下两个猪头,大嘴眉开眼笑,瞅着吴德问道:
“怎么样?尝到小破货的好滋味了?”
“嫂子,你可不要胡咧咧,糟蹋你弟妹的名声。”吴德郑重其事地说。
“怎么?难道我说错了?”大嘴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你信不信?人家可是原装的。处女啊!”
“兄弟,别开玩笑。这是真的?”大嘴一脸愕然。
“嫂子,我敢赌咒发誓,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是兄弟亲眼所见!”吴德点了点头,满脸得意。大嘴惊得半天合不拢嘴。
“这么说,先前倒是冤枉人家了。兄弟,要不要嫂子给她恢复名誉,给她赔礼道歉?”大嘴心底升起了一丝歉疚。
“不用了。只是你再别‘破货、破货’地称呼你弟妹就行了。”吴德笑着说。
周伟笑了笑,说道:“ 你小子倒有福气,叫你捡了个大便宜。”
婚后第四天是腊月二十七,新媳妇回娘家“望四日”,周小红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娘家。周大娘背着吴德问女儿:“他待你怎么样?”一句话触动了周小红的伤心处,她伏在娘的怀里大哭了一场,多少痛、多少恨化作眼泪倾泻而出,一条毛巾哭湿了,又换上一条,娘的衣襟也湿了一大片。周小红怕娘听了难过,不敢披露那天晚上被粗暴强奸的细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事情的大体过程。
娘把女儿抱在怀里,哭道:“是娘害苦了你呀,我苦命的女儿啊!”
这年夏天,陈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师范大学,放寒假回家过年,急忙打听周小红的消息。听说周小红嫁了吴德,他的心陡然一沉:我只希望她能嫁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别跟着我受苦受累;谁料想嫁了这么个畜生!想起春末的农家小院之夜,是自己的怯懦把周小红害苦了。他撕扯自己的头发,狠批自己的脸颊,难过得心都碎了。
(待续)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