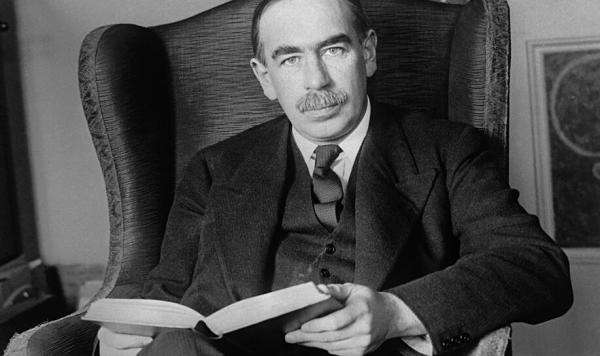梦归
宋元符二年(1099)岁末,六十三岁的东坡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夜梦登合江楼,月色如银,韩魏公跨鹤来,曰:‘被命同领剧曹,故来相报。’他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仇池笔记·梦韩魏公》)这一年距他渡琼州海峡到儋州三年将尽。绍圣四年(1097)六月,东坡谪居海南,在广州与家人作别,子孙齐集江边痛哭,是生离更像死别。当时,苏轼留书一封给广州太守王古:“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投荒海外,所能想到的无非一死。但是,死神尚未关注这位生命力极强的老人,初到海南,天涯沦落,“千山动甲麟,万谷酣声中”,东坡老人联想《庄子·秋水》,在陆行的轿里作起梦来:“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绝境中的苏轼竟然想到了回归,想到了中原,想到了人生的种种美好。“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命运似乎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试炼这位通才,让他体验到“材与不材”、“不归为归”,天人相胜的意境,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无边苍凉里保持乐观。海南三年,东坡老人食芋饮水,酿酒制墨,交友著述,在困窘中享受着自在。“半梦半醒问诸黎,朱刺疼少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一个通脱达观,不拘形迹的苏东坡在荒蛮之地复活了。
当然,中原依旧是苏轼渴望回归的所在,他在适应海南生活的日子里,北归中原的念想一直萦绕心头。某日清晨,苏轼对陪伴自己谪居的小儿子苏过说:“吾尝告汝,我绝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然后为了应验自己的预言,索性洗砚磨墨,焚香端坐,续说道:“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做八赋,当不脱误一字。”写毕果如所望,东坡大喜:“吾归无疑矣!”新年一过,六十四岁的苏轼老人活得好好的,而坚持“元祐臣独不赦”方针,二十五岁的哲宗皇帝却一命归天了。苏轼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转机。命运注定要让他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风风光光,要让他死得圆满,死得没有遗憾。
拟归
“回首繁华如梦渺,残生一线付惊涛。柳暗花明休啼笑,善果心花可自豪。”这是京剧《锁麟囊》里的几句唱词,用来写苏轼北归,很是恰当。
哲宗皇帝是正月驾崩的,三月初,消息才传到海南,与这一国家大不幸消息同时传来的是,苏轼兄弟将会内迁(当时苏辙谪居雷州)。尽管还没有确凿的信息,但苏轼已在规划回归之计了,对于前程,他毫无奢望。北归之目的地也未曾设想是中原,他希望很卑微,只想回到曾经住过的惠州白鹤峰。宦海荣宠,人间富贵,对阅尽世态炎凉的东坡早成一朵浮云。他作《和陶始经曲阿》云:“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北郊有大赉,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
给东坡老人通消息的是他的挚友吴复古,这位复古先生古道热肠,在东坡投身荒岛的日子里,几次跨海探访,给身心俱陷荒凉中的苏东坡送去温暖和生机,后来他意欲会晤北归之路上的东坡,走到清远峡时因病去世,时年九十六岁。苏东坡为他作祭文,称“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又是归”。他是苏轼北返之路上去世的第一位朋友,此后的一年里,这样的死讯一再纠缠老年的苏东坡,不断为他的情感增添说不清的哀愁。
归别
元符三年(1100)六月,在儋州住了整整三年的苏轼终于要北归了,他向街坊邻居一一道别,还特地为名叫黎民表的邻居写了一首诗:“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在海南的日子里,大诗人没少得到这位邻居的关照,他无以为报,只好赋诗留念:报之以诗人的一份真情,一点灵感和一种豁达。这首诗尚有一款弥足珍贵的题跋:“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原来,苏轼这些年白吃了黎家若干不花钱的蔬菜,临别之际只能以诗来抵菜价,诗人的窘迫,乡民的慷慨全包含在这八个字里了。六月二十日,苏轼登舟渡海,大海汹涌,思绪翻腾,往事历历,凝结成诗句:“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诗人晚年最好的一首七律,每读此诗都让人扼腕叹息,不生悲慨。不论怎样的凄风苦雨总有晴天的时候,这一刻真就是老天爷睁开了三分眼,天海澄明,毫无纤尘,原本诗人心里本就澄明达观,对于苦难已经超脱,留下的只是对“奇绝”游历的回忆,九死南荒相对于这一刻,又算得了什么?
归遇
跨海北归时,除了自然的衰老,苏轼身体尚无病患,即便经历大磨难,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逆境中渡过困厄时光的经验,能让他活得比常人要好很多。生活的艰难他能忍受,可是有一种打击对他坚强的神经具有摧毁性,那就是亲友遭受的磨难,即将面对的噩耗远远超过了他的承受力——他最欣赏的秦观竟然没有度过劫波。
时局变幻无常,苏门四学士随着苏轼的沉浮起落,在苏轼贬谪的同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无一幸免,而秦观贬得最远,他先是出判杭州,道途中再贬处州,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苏轼渡海到雷州,得以与秦观盘桓数日。两个惺惺相惜的文人,两个政坛失意的迁客,在这样的境遇里相遇该有多少话语啊,或许是过于敏感,或许是害怕黑暗,秦观对未来似乎更加悲观,分手时刻,他给苏轼看的文字不是他那灵光四射缠绵悱恻的小令,而是一篇《自挽词》,内中有这样凄惶无比的句子:“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一个能给自己写挽词的人,对于生死应该有超脱之意,但是,秦观的这首挽词写得是绝望至极,对其理解至深的苏轼不能不从中读出悲苦异常的况味,他只好安慰这位才思敏捷、思虑缜密的弟子:“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师徒二人就在这样气氛中匆匆作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二人于六月短暂相聚即分手,到九月苏轼在广西郁林(今桂林)听到了秦观去世的噩耗,尽管消息并不确凿,或者苏轼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在致友人书中依然表示:“闻少游恶耗,两日为之食不下咽。”等到噩耗得以确认,苏轼恸哭道:“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秦观比苏轼小一旬,刚过天命之年,他的一生竟是这样凄苦的结局,这是暮年的苏轼实在不忍心看到的。苏轼伤心至极,悲痛不已,他反复吟诵这位高才弟子晚年之作《踏莎行·郴州旅舍》:“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他将这首词写在扇面之上,写下了这样的追悼之词:“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从此,在苏轼北归之路的行囊里,多了一份弟子兼好友之死留下的悲哀。
归聚
年逾六十的苏轼一路奔波,又受秦观之死的哀伤打击,疲惫积郁,终于病倒在广州,这是他北归路上第一次生病。好在儿孙俱已会齐,聊慰老人愁绪。距离上一次一家老少团聚之日已有七年光景,儿子已是中年,孙辈也长成大人,这些都让苏轼由衷地释怀。一家人团聚,儿子苏迨说起苏轼的老友僧人参寥、守钦被迫还俗以及钱世雄(济明)、廖正一被废黜之事,苏轼作书宽慰钱世雄言道:“小人只能坏他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耳!”这番话铿锵有力,可谓夫子自道。然而,厄运毕竟还未远去,依旧有阴影笼罩在这位历经磨难的老人心头,在这番慷慨之后,诗人不免忐忑:“旧有诗八首寄之,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燔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想起自己因诗得祸,连累家人友朋,不能不做此沉痛语。但苏轼毕竟不是猥琐之辈,他宁可豁达面世,不会佝偻对人,即便“更此百罹,非复人事”,也能“置之,勿污笔墨”。
一家团聚,心清气爽,苏轼身体很快康复。广州是一个大都会,风俗气氛自与海南不同,这里富饶奢靡,名刹宝寺,诗书文章,美酒佳肴,应有尽有。岭南三监司之一的提举广东昌平孙鼛(字叔静)是苏轼老友,其为人澹泊,十五岁入太学既得老苏赏识,他的两个儿媳一位是晁补之的女儿,另一位是黄庭坚的女儿,与东坡可谓渊源深厚。苏轼到达广州,与叔静秉烛夜谈,“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其情其景感人至深。苏轼好热闹喜饮宴,尽管“我性不饮只解醉”,却又通晓“全酒未若全于天”,在孙叔静家的一次宴会上,“饮官法酒、烹团茶、烧御香、用诸葛笔。”让苏轼大感快意。对很多人来说,人生是一场苦难与幸福交织的行程,几起几落的苏轼对苦难和欢乐的认识,要比别人要来得透彻,他常常能在苦中造乐,能于乐中忆苦,在诸多“北归喜事”之中,于他最快慰的竟是用过一支顺手的毛笔,为此还专门写下《书孙叔静诸葛笔》:“久在海外,旧所赉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鐙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诗文是苏轼生命的寄托,一支顺手好用的笔对他的意义自是非同寻常!
想当年,苏轼甫进京都既得前辈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许,后来他得执文坛牛耳,也像他的恩师一样不遗余力推举新人,苏门四学士自不待言,还有一大批文艺青年得其揄扬。在他的晚年,广州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成为北宋文坛最后的幸运者。谢民师博学而工词章,为官之余,还置席讲学,从者甚众,苏轼来了,他不经介绍,自携所撰遮道来谒。读了谢民师的作品,苏轼大加赞赏:“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这句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年欧阳修推许苏轼的那句名言:“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将谢民师留下畅谈终日,离开广州后尚意犹未尽,在清远峡,他写下了著名的《答谢民师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达而已矣。’辞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沈德潜认为:“‘行云流水’数言,即东坡自道其行文之妙。”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封书信是苏轼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论,他激烈反对诘屈聱牙,为文雕饰,力倡“行云流水”,这是他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他平生为人之真实写照。
人老多梦,梦与现实常能交互,元符三年腊八夜里,苏轼梦见与老朋友苏坚相见,苏坚给他看的是一具乳香婴儿。几年前自己在九江曾与苏坚邂逅,之前也有一梦,绍圣元年(1094)六月,苏轼贬往惠州,七月途经九江与苏坚别。那一次二人曾有唱和,苏轼写有《归朝欢·和苏坚伯固》:“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淅。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傜新唱,谁谓古今隔。”今次梦见乳香婴儿乃是南华赐物,醒来苏轼纳闷,莫非这次还能与苏坚再得相见?其地莫非竟在南华?事有凑巧,第二天苏轼竟然得到苏坚来书,说在南华寺等他已有数日,这是心有灵犀还是命有奇数?苏轼不免感慨:“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在韶州,老友相见,距离上次见面已过去七年,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之后的苏轼,已经超越尘世的羁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一前一后,一词一诗,苏轼的人生境界亦有不同。法眼看天下,凡世尘垢岂能沾染真人,真正的达人岂能为电光泡影之身而徒生烦恼!在韶州,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曲江县令陈密在私宅宴请苏轼,席间叫出名唤素娘的侍儿唱曲侑酒,苏轼为赋《鹧鸪天》一阕:“笑捻红牙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娆。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据旧注,苏轼写此词时,写罢上阕最后一个“娇”字,不小心在其后误点了两个点,他略加思索将错就错,于是便有了下阕首句之“娇后眼”,接的可谓天衣无缝,苏轼天纵奇才,到老没有丝毫损减,这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
归路
从六月渡海将近半年,苏轼一路不是乘船就是骑马,历酷暑经秋凉,一出韶州,身体终于吃不消了,患的是大伤元气的痢疾,走不动了,只好在南雄调养,等待痊愈。这一年的岁尾,苏轼是在路途中度过的,“人生长如寄”,苏轼在诗中反复吟诵的这句话竟成了自己一生奔波的谶语。
转过年来,新皇帝启用了新年号“建中靖国”,欲以大公至正消弭党争,纠正偏颇。这一年正月初四苏轼再度上路,匆匆向北。曾敏行《独醒杂志》有这样一段记载:“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一路北上,诗情豪迈,岭南七年,苏轼在困厄中顽强生存,再次踏上大庾岭,正是早春时节,南国春早梅子已然结子,诗人不免兴动,作《赠岭上梅》:“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以品格高洁的梅花自喻,既不和“杂花”一齐开,也不和“行人”一齐来,冷静沉着,识时审势;不在梅子未成熟时就急急忙忙去尝青梅煮酒,而是“要看细雨熟黄梅”。这首诗可以看做苏轼遇赦北归后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新帝践祚,时局一变,元祐旧人纷纷起复获得重用,苏轼兄弟声望崇隆,很多人预估苏轼不会长此闲废,再度置身高位只是时间问题,《侯鲭录》记载:“山谷建中靖国间例复官职,有诗十首。一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谓东坡也。”这一段记载是当时政坛呼声、士林公论,在英州他与曾反对变法、上神宗《流民图》的诤臣郑侠相会,郑赠诗苏轼,期许他能像淋雨滋润苍生,苏轼回复《次韵郑介夫二首》:“一落泥途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长庚到晓空陪月,太岁今年合守心。相与啮毡持汉节,何妨振履出商音。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海上偶来期汗漫,苇间犹得见延缘。良医自要经三折,老将何妨败两甄。收取桑榆种梨枣,祝君眉寿似增川。”“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恐慌之情溢于言表,“自要闲飞不作霖”便不是自谦之词了。苏轼的内心对于政治已经心灰意冷,而且,时局的变化也的确不让他乐观,朝廷中已经有人因为屡次疏请招用苏轼而被贬官,在新皇帝心里面,苏轼依旧是元祐党争的罪魁。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五,苏轼重游大庾岭龙泉寺,七年前过岭题诗犹在,一晃七年过去,政坛冷暖苏轼岂能不知,旧地重过,诗人写下了:“秋风卷黄落,朝雨洗绿净。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在诗前诗人记述了写作的背景“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中用了一个典故,汉朝初创,叔孙通奉命制朝仪,尽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有二人不肯应召被目为“不通时变”的鄙儒,此刻在苏轼眼里,那两位未曾奉召的儒生恰恰是自己追慕的对象,政坛如泥潭,东坡老矣,不堪挣扎了,他无意去趟朝堂里那潭浑水了,在《过岭寄子二首》中,诗人已作退步之计,可以认为是南迁与北归的总结。
苏轼一生的沉浮与号称宋室贤后的高太后和向太后密不可分。哲宗时代高太后执政,他在朝里身居高位,高太后去世了,他就倒霉了。这一次是向太后说了算,他才能从悬居孤岛而得北返中原,没想到路程走了还不到一半,建中靖国元年正月里,向太后驾崩。太后一死,徽宗皇帝就没有顾忌了,太后启用旧臣的用人之策随着生变。“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经历过风浪的老人对于这样的变局比别人敏感得多,太后去世的时间是正月十四,苏轼在《次韵江晦叔二首》中写道:“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北归走到了江苏境内,苏轼先到金陵去崇因禅院向观世音像还愿。南迁之初,苏轼曾来此许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这次到来,苏轼如愿写了《观世音颂》。在金山寺,苏轼如约见到老友程之远和钱世雄,一起登妙高台,在这里,苏轼看到李公麟所画的自己的画像,百感交集,自题一诗于其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意出言表,千年后读之,犹觉义愤填膺。
苏轼开始寻找归宿之地了,苏辙邀其与己同住许昌彼此照应,但苏轼内心深处却不想去那里,一来弟弟一家家口庞大,并不富裕,二来许昌距离帝都太近,他心怀忧惧。在致苏辙的信中,他是这样说的:“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一生豁达的苏轼到了老年,对政局的动荡避之唯恐不及,从神宗到哲宗再到徽宗,党争阴影持续不散,而此时又是暗流涌动渐成汹涌澎湃之势,此时跻身时局,无疑飞蛾赴火,他自己还好说,怕的是连累亲人朋友,在致李廌(方叔)的一封书信里他惴惴不安地写道:“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甫(范祖禹)、少游(秦观),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生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忧患虽已过,更宜慎口以安晚节也。不讶!不讶!”这份恐惧不是一己之身的安危所系,他是文坛领袖,政坛元老,他的一身安危关系着太多人的命运,苏轼内心深处有一份大悲悯,他不能也不会只顾自己荣宠隆誉而牺牲那些无辜的粉丝们。
许昌不会去了,他想到了常州,并委托钱世雄代为购房,作久居之计。苏轼一面安排未来的住处,一面兼程前行。此时已经到了江南的酷暑时节,船到仪真,苏轼再次染疾。这次的疾病是冲着老人的生命来的,无论多少才情多么豁达终究战胜不了死亡。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苏轼依旧活得比别人精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见得最多的人是米芾,东坡老人在致米芾的书信中流露出的情感真堪做中国文人真诚交往的经典标本,“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这是苏轼给米芾的书信之一,写这封书信时,苏轼已经病魔折磨有日,从信中谁能读得出这是出自一位行将离世老人的手笔?在其后数日之间,身在病中的苏轼还有多封书信给米芾,二人惺惺相惜,这段交往应该是苏轼晚年最值得称道与纪念的。六月十一日,病体少愈,此时米芾也将进京,告别之时,苏轼坚持起床,抱病扶杖相送于闸屋之下。
归结
生命留给苏轼的时间越来越珍贵,六月十二日,从仪征出发渡江过镇江,往祭堂妹。恰在此时,归隐京口的前相苏颂去世的讣告传来,苏轼命子过代己前往吊唁。此时,朝野上下关于苏轼行将入相的传言也是甚嚣尘上,害得苏轼不得不修书辟谣。说来凑巧,苏轼北归之时正是他青年时好友、晚年的政敌章惇被贬之日,去到的地方又是苏轼刚刚离开的雷州,苏轼入相的消息让章惇一家陷于恐慌,可以说,苏轼的海南之贬,部分源于章惇,章惇的儿子章援作为苏轼的弟子因两家势不两立久废师礼,此时救父心切不得不写了一封长信致苏轼,这封信写得言辞哀婉,分寸火候俱佳,赵彦卫《云麓漫钞》详细记述了这段公案:“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过)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这是苏轼最后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得很长,是写给曾经迫害甚至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的儿子,心中没有一丝仇恨和怨气,没有幸灾乐祸的揶揄,苏轼真的是超越了。苏轼给章援写的信在章家珍藏很多年,见之者评价“此纸乃一挥,笔势翩翩”。字如其人,书乃心声,行将离世的苏轼心里不存一丝污垢。林语堂先生在其《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是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基督徒林语堂大概从这封信里读出了别人读不出来的滋味,他把这封信看作是“人道精神的文献”。千年之后有此一知音,苏轼大幸!
六月十五日,病体稍安的苏轼继续上路,坐船循运河去往常州,那是他准备归隐的地方,没想到他的生命就是在自己心仪处结束,这也算是老天对苏轼最后的眷顾。苏轼坐在船舱里头戴小冠,身穿背心,运河两岸站满了百姓,大家渴望一睹名士风采,苏轼回头对同行的客人说道:“莫看杀轼否!”这样的场景在魏晋名士风流的时代曾经有过,此时的东坡颇有魏晋名士之风流。
终于,苏轼病体难支,他最后的日子《春渚纪闻》有详细的记载:“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纯叟藏先生帖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先生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某曰:某获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迁寓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疫少间,曰:今日有意,喜近笔研,试为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明日又得《跋桂酒颂》。”从这一段记述中,我们感觉不到死神已经迫近,他还是那样从容,那样通脱,那样渴望展示过人的才华。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维琳方丈前来,陪伴着他。此时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他让维琳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纪年录》这样记载:“径山老惟琳来,说偈,答曰:‘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琳问神咒事,索笔书:‘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并出一帖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盖绝笔于此。”这是苏轼一生最后一首诗。即将脱离人世间的苏轼大叹:“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人生诸多苦难折磨,无一不是这具臭皮囊所带来。若能无此身躯负担,何来苦痛?到死,苏轼对于祈求神灵是不信的,这从苏辙为兄长所撰写的墓志铭可以得到认证:“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苏轼总结起起伏伏的人生:“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这句带着“业报轮回”观念的话,是对亲人的宽慰,苏轼告诉守候在旁的亲人“善者自有善报”。尽管这不一定代表苏轼面对死亡的态度,然而,却是一段极自负的告白。他告诉陪在身边的儿子们不用担心,自己必不会坠入地狱,到死依旧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其“慎无哭泣以怛化”应该是苏轼最后的死亡观,这句话典出《庄子·大宗师》:“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梨往问之,曰:叱!避!怛化!”子来与子梨的一番对话,是关于对死亡的认识,死亡无非是“大化”中的一种形式,实在无须紧抓住“人”的形体不放,苏轼此时借庄子的话说出的是自己“齐生死”的观点。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全家都在屋里,维琳方丈和钱世雄也在,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记载他们三人的答问: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宜勿忘。”公曰:“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钱世雄曰:“至此更须著力。”答曰:“著力即差。”西方极乐世界有吗?西方不是没有,但我这里使不上力气。这是苏轼最后的话!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更应该用力去求啊!”苏轼没有回答。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去世,享年六十五(虚龄六十六)岁。北归中原,一走就是一年。这是东坡老人生命中最后的一年,走在回程的路上,也是走向了生命峰巅。这一年苏轼完成了从庙堂到乡野从繁华到质朴的终极追求,走出了是非、恩怨和执着。苏轼死在建中靖国元年是他的福分,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宁元年,党祸再起;崇宁三年,他的名字被刻上元祐奸党石碑。他去世26年后,北宋覆灭。东坡历经过磨难,但逃过了亡国亡天下的倾覆之难,他死后,中国文化史上再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