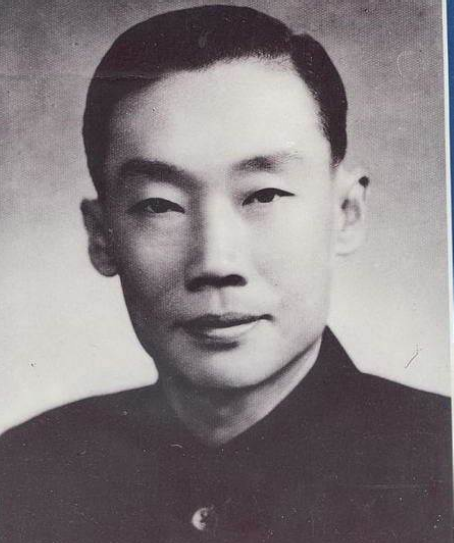凭着一种始自儿童时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汉娜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并给一些杂志做自由撰稿人。到了1943年,不断地有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消息从欧洲传来。人们知道纳粹的反犹立场,也知道剥夺财产和集中营的存在,但是当有系统有效率的大规模灭绝行动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还是大吃一惊。纳粹的罪恶远远超出想象。
汉娜开始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机理。她相信纳粹的灭绝机构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到底是什么传统丢失了,以至于这样的事情会成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历史潜流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汉娜开始阅读书籍,查找资料,她阅读纳粹的暴政,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书籍和文献,她在思考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机制,而这一切都必须在业余时间完成。
1945年5月战争结束。汉娜首先跟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取得了联系,雅斯贝尔斯在这场浩劫中终于活了下来,汉娜得到消息后立即给她的老师寄了包裹,因为在一片废墟中的德国各类物资奇缺。
经过多年的压抑和排斥,雅斯贝尔斯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像一个德国的招牌。他急切地想知道汉娜在美国的生活。汉娜写信说道:“我始终都认为今天一个人只有处于社会的边缘才可能保持他合乎人的尊严的存在方式,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无非拿或多或少的幽默冒险,而这既不会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也不会让他饿死。我在这里相当有名,有一点儿可疑的威望,也就是说,他们信任我。”
雅斯贝尔斯从海德堡写信来,他又恢复了与海德格尔的联系。战后的海德格尔不得不接受一项“清查委员会”质询。他竭力为自己申辩,可是最后还是被法国军事占领当局剥夺了教席。军事当局在判决时,引用的恰恰是雅斯贝尔斯的见解,这些见解表达了对于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疑虑,称其为“不自由的、专横的、封闭的”。
1946年海德格尔经历了一次身体和灵魂的崩溃。恢复健康以后他重新过起了隐居生活。尽管雅斯贝尔斯基于哲学的考虑请求恢复海德格尔的教职,不过他依然没有打消对他的疑虑。他说,在他收到的海德格尔的信中,仍然感到有一种“不洁净”。
相对来说,汉娜在自己的评判中没有像雅斯贝尔斯那么冷漠,在她看来,所谓的“不洁净”是一种“意志薄弱”。看起来汉娜仍然受到她的老师的影响,这种暧昧不清的“阴影”可能一生不曾改变过。不过,她在他们关系破裂之后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里语出多讽:“那种在托特瑙堡的生活,咒骂文明,独处并写作,的的确确只是一个他退隐其中的老鼠洞,因为他有权利相信,他在那里需要观看的只不过是那些心中对他充满景仰前来朝圣的人们。”
汉娜同时兼任多份工作,主要的生活费用来自于舍肯出版社,她在舍肯出版社工作了两年,期间她最感欣慰的是编辑出版了卡夫卡的日记,其时,这位1928年逝世的作家在美国依然默默无闻,以至于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人问她,这位“弗朗西斯·卡夫卡”究竟是谁。
汉娜隐隐觉得她目前所做的思考与卡夫卡的文学幻象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种幻象就是,屈从于一种必然性外衣的法律是如何成为人类的宿命的,而此刻,她也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机器。汉娜·阿伦特没有像卡夫卡那样创造一个文学形象,表达一个人面对万能的、无懈可击的法律或者面对一个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着是非曲直的城堡主人的故事。她的天赋在于历史和哲学的思考,她梳理着历史,为的是寻找那个最终导致了纳粹极权国家的根源。
早在1944年,她在投给德语杂志《转折》的稿件中,设想了一个“醉心于家庭责任的父亲”,他不是狂热的信仰者,不是虐待狂和杀人狂,他是一家之主,对于他来说,他的私人生活凌驾于一切之上,他随时准备着为养老金,为了生活保障,为了妻子儿女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背弃荣誉和人的尊严。他完全可以是一个好人,在家庭角色中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问题在于,这位平时不会欺负弱小的家庭主人准备好了成为罪犯或者杀人犯。也就是说,心甘情愿地成为一部死亡机器的一个零件。
汉娜将她所有的思考都写进了那本后来让她扬名立万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用英文写就的,一部500页的、印得密密麻麻的手稿在1949年就已经完成,但是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付梓。这部手稿讨论了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一种统治模式,这当然首先是纳粹政权,也涉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当人们第一次听说纳粹死亡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传闻,对他们来说,这些传说中死亡机构完全难以置信,既不是出于军事目的也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正相反,这些机构的设立还需巨额资金,而且大规模灭绝行为最终对于战争胜负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汉娜才渐渐懂得,极权统治空前绝后的特征恰恰在于这些无意义的行为之中。
健全的人类理性不得不面对“彻底的虚无”。这个纯粹的虚无最可拍的地方在于,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还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被送进毒气室是无所谓的。在这里,作为人的本质这一点已经消失殆尽,所有的权利和尊严都被剥夺了,起作用的只是严格遵守的批量屠杀的份额,犯罪消失在了“清除”的流水线之后。
不管是人种的优越性和阶级的纯洁性,这些疯狂的目标都有可能通过暴政和组织的手段成为现实,而实现这些伟大目标的过程中,人只不过是所谓的材料,是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作为执行者,可以全然没有任何怜悯心,只是出于一种对于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组织的忠诚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以历史使命的名义大肆屠杀芸芸众生是极权统治的秘诀,而为了显示依照一种理想的律令改变世界是可能的,极权统治者必须虚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排斥任何一种与之相矛盾的经验,通俗地说,就是制造一种“歪理”,而这种“歪理”常常在人类的“常识”之外,用一种幻想体制替代现实性。
这个徒有虚表的世界一旦成型,一场运动便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共同体,个体的人一旦堕入这个共同体,便随之起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精神病院一样的东西在这个系统之内则是完全正常的。
汉娜认为,要缔造这样一个极权体制,群氓、宣传和组织缺一不可。群氓由孤立或孤寂的个体组成,一种原子化了的个体主义便开始主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宣传提供一个虚构世界的图景,极权主义组织采纳了这一虚构,并且把它当做现实来操作。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卷直接处理极权主义的问题,以至于有人建议直接从第三卷读起。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并非暴政的一个形态,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比喻,用以在暴政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区分,她说,暴政是类似于沙漠的一种政治形态,而极权主义则是吞噬一切的沙漠风暴,窒息并灭绝这一世界。
原载 葛陂小记
张祚臣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