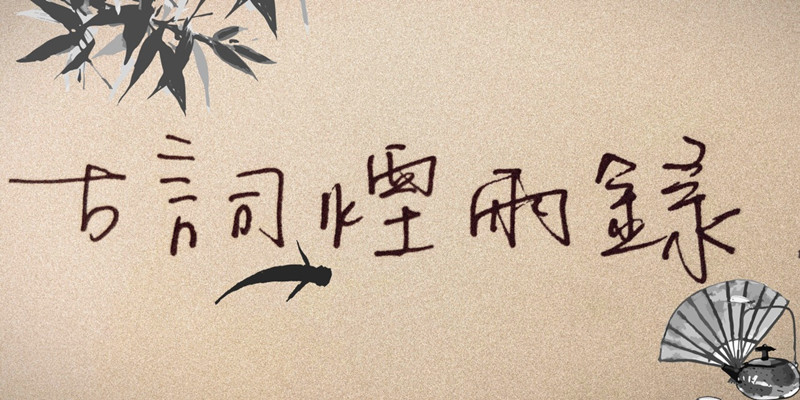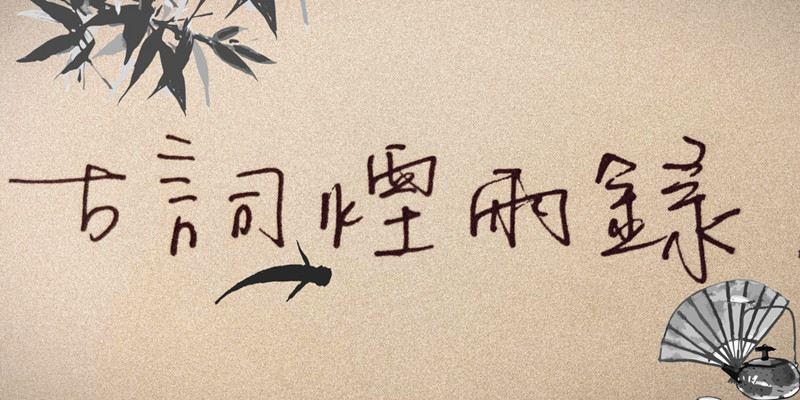六、屈原沉江文字之研覈
(一)幾個關鍵字眼之別解
其實,有關屈原的《楚辭》、楚國、自沉等字眼,往往都另有一種含義。這些概念所涉及的文化歷史環境必須逐步廓清,先看以下例子。
其一,何為楚詞?《九辯章句·敘》「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楚詞》即《楚辭》,此處對《楚詞》的界說,是給《楚辭》做了別樣解釋。「故號為楚詞」的原因,是劉向等「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是強調「楚」字顯著的「悲」意。豈只如此,悲痛艱辛酸苦凄慘哀愁創傷憂戚冤煩,都可遇「楚」而成詞,表達幾乎所有被殘忍折磨的冤枉委屈、憤怒懊惱、五內俱焚和肝腸寸斷,都是靈和肉之極端負面的刺激、劇烈虐待;臣之「懷忠貞之性」,偏偏「被讒邪」,唯一能寄希望的「君」又如此「闇蔽」;在極端絕望之下,靈魂發出的呻吟,以及已被暴君的高壓變了形狀變了腔調的同情,此之謂《楚辭》。王逸給《楚辭》所下的這個定義(另一個定義出自班固),應該也得到注意。
其二,何謂楚國?《九思·遭厄》云「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賢者質美,故以比玉。何楚國兮難化言楚國君臣之亂,不可曉喻也。迄於今兮不易。」這幾句話,作者由屈原的第一人稱忽換對於屈原是第三人稱的王逸自己,並說:悼念遭難的屈子啊,他在汨羅江沉沒了寶貴的玉體。楚國何故難以達成君聖臣賢的教化,真是頑固不化啊,直到今天也一點不變易。可以看出,所謂於今者,王逸之時也;不易者,楚國之不化也;楚國者,漢朝之喻指或代稱也。則遭厄之悼念,為漢本朝「屈子」而發也。順便說,所謂屈子之稱號,本自《淮南子·道應訓》及《史記·三王世家》所記楚在魏之宗室大夫屈宜臼(臼一作咎),其人以賢而有遠見著名,而被稱屈子,可算作楚國屈姓頗有名氣者,而給予假造歷史者以啟發也。而此處「湘汨」者,作為「一般態度」的表象,也失去了其原來的意思,大概可以讀成「暴君所設的災難」吧。
其三,何謂楚懷王?《九歎·離世》曰「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言懷王闇惑,不知我之忠誠,不聞我之清白,反用讒言而放逐己也。就靈懷之皇祖兮,訴靈懷之鬼神言己所言忠正而不見信,願就懷王先祖告語其冤,使照己心也。鬼神明察,故欲愬之以自證明也。」「靈懷」二句,表面上說楚懷王不瞭解自己的智慧和忠誠,也不聽自己的勸諫和清白名聲。但這兩句雙關另一層意思:楚懷王根本不知道還有個我,他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我!這一解才是歷史的真實!戰國後期的楚懷王怎麼會知道漢朝的屈原呢?可見屈原這個名字,屬於漢人偽造,而偽造者試圖把他嵌入楚國的歷史;嵌入的破綻早被許多《楚辭》學者看出,卻又被另外一些學者不相信而勉強彌合。這種託名楚懷王的詭異策略,倒把真的把事主漢武帝變成楚懷王擴大而朦朧的影子。所謂靈懷,本來帶一點淮南子神學痕跡,是描寫聖尊者懷抱的,用來指楚懷王或者漢武帝雖不同,都是一種含諷的恭維。
其四,子蘭、子椒何謂也?《離騷》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史記》謂懷王少子),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樧又欲充夫佩幃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我們已指出,楚懷王根本不知道漢朝的屈原是誰。以上《離騷》中關於蘭、椒的句子以及王逸的注解各有其意。《離騷》原文,蓋形容在暴君和讒言的作用下,許多本來尚可同道的朝臣紛紛變節自保。蘭、椒具體指武帝朝何人尚待細求,但絕不指楚懷王時人。王逸注解的方式則頗為有趣,他以為「蘭」是比喻子蘭的,而「椒」和「榝」兩樣花卉是比喻子椒的。以花喻人是可以的,但以一花喻一人,同時以二花喻另一人,這真是從來未見的荒唐比喻。這種比喻產生的藝術效果,只能讓子蘭和子椒都歸於子虛烏有。他們是《史記·屈原傳》很有創造性的情節臨時產生的群眾演員,本來就是影子人物。
錢鍾書《管錐編·楚辭·洪興祖補注》(九)「蘭椒」條謂「屈子此數語果指子蘭、子椒兩楚大夫不?同朝果有彼二憾不?均爭訟之端。然椒、蘭屢見上文,王、洪注都解為芳草,此處獨釋成影射雙關;破例之故安在,似未有究焉者。」汪琬《堯峰文抄》卷二三《草庭記》云:「余惟屈原作《離騷》,嘗以香草喻君子,如江蓠、薜芷、蕾芎、揭車、蕙茝,如蘭如菊之類,皆是也;以惡草喻小人,則如茅薋、菉葹、蕭艾、宿莽是也。而或謂蘭蓋指令尹子蘭而言,則江篱、薜芷,又將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且令尹素疾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原顧欲『滋』之、『紉』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匿,亦豈《離騷》本旨哉!余竊疑子蘭名乃後人緣《騷》詞附會者。」錢引汪琬語深為可信,竊疑《離騷》中蘭、椒之名被用來比喻《史記》本傳中人物,是要造成《離騷》之文意與假的屈原傳之同步。
(二)彭咸式沉江的四種表述
接上文,其五,屈原自沉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構成屈原傳記和人格的關鍵性情節,我們不得不重視,所以試引《楚辭》全部有關文字而加以討論。
以下是前引《惜往日》的繼續:「何貞臣之無罪兮忠正之行,少愆忒也。被離謗而見尤虛蒙誹訕,獲過愆也。慚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愨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行彌篤也。臨沅湘之玄淵兮觀視流水,心悲惻也。遂自忍而沉流遂赴深水,自害賊也。卒沒身而絕名兮姓字斷絕,形體沒也。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上無撿押,以知下也。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棄草野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拔愁苦也。恬死亡而不聊忍不貪生,而顧老也。獨鄣壅而蔽隱兮遠放隔塞,在裔土也。使貞臣為無由欲竭忠節,靡其道也。」這一段前接的「秘密事以載心兮」一段,記敘一個因不肯趨炎附勢、也不肯對「淮屠」犧牲者說壞話,因而也被殺害者。這段所記則是一個無罪而被謗、被貶,乃至臨湘水投身自沉者。他即使「卒沒身而絕名」,君王也不覺悟。其君不識賢愚,使忠臣被遠貶到邊緣閉塞之地,而沒有活路,也無所解其愁苦,想盡忠都不可能,所以不能顧老惜命,只能自殺。這一段懇切陳情,使人動容,而不得不信。是因《楚辭》作者群中,確有投身自殺者。可惜,他已真「卒沒身而絕名」了。
我們再看《九歎·離世》以下文字:「身衡陷而下沉兮衡,橫也。不可獲而復登言己遠去千里,身必橫陷沉沒,長不可復得登引而用之也。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言己遠行千里,不敢顧念身之貧賤,欲慕高位也。惜君國失賢,道德不盛也。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言己放出國門,正心直指,執履誠信,幸君覺寤,賜己以還命也。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言己不自念惜身之放逐,誠哀僕御之夫,坎然恚恨,以數逢憂患,無已時也。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言己放出九年,君不肯反我,中心愁思,欲自沉於水,與彭咸俱遊戲也。惜師延之浮渚兮師延,殷紂之臣也,為紂作新聲北裡之樂。紂失天下,師延抱其樂器,自投濮水而死也。赴汨羅之長流言己復貪慕師延自投於水,身浮渚涯,冀免於刑誅,故遂赴汨水長流而去也。」
此處可看到託名劉向寫的一段「屈原」敘事抒情。王逸雖仍用「屈原」「言己」之句來解釋,讀者會發現不對了。這個「屈原」已被遠貶,還想被召還「欲謀高位也。」連他的「僕夫」都因跟隨他到處流放而非常不高興。他被放逐九年了(「九」表不能再多之複數),很想去找彭咸一起遊戲(是否投水,難定)。又惋惜(貪慕?)紂臣師延自投於水,且「冀免於刑誅,故遂赴汨水長流而去也。」投水是希冀因此「免於刑誅」?這就連《史記》說的屈原也不像了。我們再強調一遍:《楚辭》是由一群被冤枉被流放被誅殺的漢臣寫的。
這些人,被誅殺或早或晚、被流放或近或遠,其中可能不乏在流放中投水而死者。這個情節被奉旨編輯《楚辭》、並且創造一個人物而嵌入歷史(見下)的「史臣」們相當有創造性地利用了。王逸也舉不出關於「彭咸」的先秦文獻出處,而姑妄注之。正說明,經過秦火之後,漢代儒者著書立說,很有杜撰空間,「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的彭咸,就是這個空間中一個來歷不明的神秘人物。
以上寫莊重的投水者,整部《楚辭》都充斥其他類型的彭咸投水宣言,還有以下幾種例子:
1.《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補注曰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沉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2.「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3.《抽思》「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先賢清白,我式之也。」
4.《悲回風》「淩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沉沒也。」
5.《悲回風》「孰能死而不隱兮誰有悲傷而不憂也。照彭咸之所聞睹見先賢之法則也。」
6.《九思·怨上》「復顧兮彭務彭咸務光,皆古介士,恥受汙辱,自投於水而死也。擬斯兮二蹤願效法此二賢之跡,亦當自沉。」
7.《九歎·遠遊》「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言還見楚國風俗,妒害賢良,故自沉於沅、湘而不悔也。」
8.《九歎·逢紛》「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濿言己貪惜以忠事君,而志不合,故欲橫渡汨水,以自沉沒也。」
9.《七諫·沉江》「懷沙礫以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塞言己所以懷沙負石自沉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以上例子中,1.依彭咸之遺則;2.從彭咸之所居;3指彭咸以為儀;4.託彭咸之所居;5.照彭咸之所聞──對彭咸之投水,全說要則之、式之、儀之、伴之、以自勵,以建功留名,以諫時君。其中;6.以第三人稱提到屈子懷沙負石,6.自言效法彭咸和務光,又拉上一個投水事較為確實的榜樣;7.說楚國妒害忠良風氣不好,故必須沉湘江。8.說自己與君不合,要橫渡汨羅來自沉。9.說自沉,是因不忍心看君王被讒佞蒙蔽。以上9個例子都是一般地宣言,有很多是後人替屈原宣言,將要把這不明來歷的彭咸當成效法榜樣,尚未付諸行動。尤其洪興祖,說屈原之自沉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所以從懷王時初失意就考慮好了而決定將來自殺,過了若干年(幾十年)而付諸行動,好像只有他一個人理解屈原,大概是要表現自己也會如屈原這樣忠君吧。如此解釋前人來向時君表忠心的話,恐怕連他的宋朝君王也感到虛偽。
10.《七諫·哀命》有很生動的投水前後之描寫,其中妙語如珠;所以不忍刪掉一句,而全引之,略加說明:「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言己沉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屈原自言跳進汨羅江水中,是因時運不好,所以決不返回「楚國」、他自傷於被放逐、又與君王離別的雙重困擾,就順水而下,在江中載沉載浮了。看他在水中:「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言己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偃蹇難止,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他住在水底暗屋黑洞,也就是藏身岩石洞窟中,和蛟龍一起遊玩休息(王逸還煞有介事地說「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水底的山石很險峻,自己的靈魂也進退兩難,無法安居。在深水之中浸泡,還不知要在此耽延多久呢。再看下去「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捨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捨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己,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修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他形體離解,精神越裂,靈魂迷失,身沒名滅,卻還是自樂不改,還在追恨根本不認識他的昏君楚懷王、責怨影子人物椒蘭呢。下文接云「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言己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遙涉江而遠去言己念眾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己遠去也。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己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嶮,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沉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他說時代風氣不好,自己也很煩惱迷惑,眾臣如此自私不為國,所以我只好過江投水算了。雖念及女嬃為我流淚噓唏是為了我好,但我死志已決,無可追悔了。我即使死了,仍志潔於水、心高於山。我哀嘆高丘赤岸,就從這裡投下去吧,再也不回返人間了。最後「哀高丘」這兩句話,是他投水後對自己行為的解釋。依王逸,他是選了如此一個「赤而有光明」的風水寶地往下跳,有點幽默吧?你看他,都投水了,還說如此多閒話,是不是滑稽之雄東方朔在搞鬼?東方朔說的話和他讓屈原的鬼說的話,都是名副其實的鬼話。豈可輕信?又豈可不信鬼話後面的真義?王逸當然不信這鬼話,但他好像使勁板住面孔,忍住而不笑,不肯把「屈原投水已是鬼」說出來。換一個角度看,說屈原投水自沉,簡直是對他正身本尊本人的侮辱。東方朔揶揄的對象不是屈原,而是屈原神話和鬼話的製造者,恐怕也包括相信者。這一段對《楚辭》編輯者設計的屈原投水之深刻生動的諷刺,真應該表而出之。
再看以下例子,這裡的彭咸的形象和作用(包括王逸注解)就頗為曖昧了。
11.《七諫·謬諫》「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風俗,則為貪佞也。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偝書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
12.《悲回風》「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申徒狄也。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跡也。驟諫君而不聽兮驟,數也。重任石之何益言己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閒,以泄憤懣,終沉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13.《悲回風》「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言己見讒人倡君為惡,則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而不能忘也。」
14.《思美人》「命則處幽,吾將罷兮受祿當窮,身勞苦也。願及白日之未暮思得進用,先年老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此處王逸無注。
上述11把原句「棄彭咸之娛樂」解成「棄彭咸清潔之行」而「娛樂風俗」,顯然不合語言本身的邏輯,再加上「則為貪佞也」,更不成道理(把「之」解釋成「而」仍勉強)。照上下文看,當道者應不棄彭咸之娛樂,不滅巧倕之繩墨(繩墨喻先王之法則)。那麼彭咸之娛樂就應具有一種快樂的正面品質。王逸這樣注解,畢竟深意何在,尚需探求。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此處「彭咸」的身份可疑,不像是專門「投水」而「娛樂」的。
12.前文已見《悲回風》中「照彭咸之所聞」「託彭咸之所居」的說法。此處「望大河」四句,又請出申屠狄這位有記載的投水而死者來抒發真情。「望大河」就不大對,屈原怎麼跑到黃河去了?這當然是以楚代漢造成的漏洞。他悲傷申徒「自擁石赴河」。還說多次進諫,君王都不聽,就算背上更重的石頭投水,哪有任何一點用處呢(此句近《悲回風》之末尾)。王逸也言「終無益於萬分也」——毫無用處之後,隔了一句到全文末尾做總結時,還照樣在說「託游天地」後、屈原投水自沉跟子胥、申徒一樣嚴肅而有意義。對比之下,前後矛盾,令人感到滑稽。
13.「何彭咸之造思」,與「何樂之有」一樣的倒裝句型,意應是「造思彭咸者,何也?」謂構想出彭咸這個人物來,是為什麼(怎麼回事)呢?是不忘屈原其人和他的志節啊。這個例子,和前文所論《遠遊》「高陽邈以遠兮,吾將焉所程」句之針對「帝高陽之苗裔兮」設問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巧妙地利用《楚辭》本文,暗示另一部分文本的問題。王逸原注是在讒佞戕害忠良的上下文中,說屈原不忘彭咸的志節而自勵,就成了這種編輯目的之掩飾。
14.《思美人》數句,王逸注說,屈原之所以孤獨地向南方行走,是他想念彭咸之故。這裡的「屈原」已年老了,卻還「思得進用」,想念彭咸,孤獨南行。這越看越不像了。好像彭咸的典型在鼓勵他努力前行。這就把投水的彭咸和屈原的投水全都否定了。
綜上所言,可以這樣認為,在《楚辭》編輯過程中,由於被貶而死的「屈原」們中真有投水自殺例,甚至淮南小山也以「沉沒」(沉水而死)形容劉安尤蓼太子之死。編輯者們因此為「屈原」這個合成人物設計了效法彭咸「自沉沒」的情節來表其特別之忠誠;似專寫投水事的《懷沙》就是如此,見下文。但他們似沒忘記用各種方式暗示讀者:雖「沉江而死」成了「屈原」典型行為,「屈原」名字所代表的最重要人物,卻與此全然無關,以至與他似相關的投水描寫都成了虛筆或者贅疣。所以《楚辭》本文中,雖多拿彭咸擺樣,但同時也有很多曖昧、質疑甚至諷刺。至於「彭咸」,雖有時似是投水的楷模,卻是漢人「杜撰空間」之物,不見於漢以前的史料。
以上僅是發現「蓼太子」其前加其後的讀書之心得。以下試引金開誠《楚辭講話》(北大出版社)第三章,發現其引述的汪瑗《楚辭集解》考證之結論與以上筆者直接的讀書心得不謀而合。其詞提到「願依彭咸之遺則」「從彭咸之所居」「指彭咸以為儀」「思彭咸之故也」「何彭咸之造思|」「照彭咸之所聞」「託彭咸之所居」等,然後斷曰「詳玩此數語,亦未見彭咸為投水之人」。又曰「『思彭咸之水游,』不知劉向何所考據而云然也。蓋嘗聞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稽其姓而辨其名,則曰彭咸。……意者後世因其西逝流沙之語,故誤以為投水,見編內亟稱其人,遂附會其說焉」。汪瑗說屈原為了離楚隱遁,固然不對;但他看出《楚辭章句》中之本文乃至解釋,頗有模棱猶疑的例子,而否定「屈原真身」之水死說,應是有見。又嚴忌《哀時命》「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在全篇都是屈原第一人稱的上下文中,忽然冒出第三人稱的讚揚屈原,令人懷疑這個句子是不是生硬插入的。
班固在《漢書·賈誼傳》(卷四八)中說,「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云云,這裡所引《離騷》結尾便沒有「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之語。當然有人會說,班固可能只是引用其結尾表示一下,不必全引;但也有另一種可能,班固所引《離騷》本來就沒有彭咸語。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