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世才俊,娶妓為妻
(一)南國清源、有道生年
《舊唐書》本傳(卷六一)以溫大雅「太原祁人」,《新傳》(卷九一)則謂「並州祁人」。則溫氏籍貫,似應為太原祁縣。但對溫庭筠而言,似又不然。溫《上蔣侍郎啟二首》之一(劉學鍇《溫庭筠全集校注》(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7年7月第一版,卷十一;後文全部溫的啟文,亦引之,以下簡做《全集》)有「遂揚南紀之清源」句,頗有意趣。「南紀」,語出《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本指包羅和經緯南國的長江漢水,而代指南國。清源,本意清泉淵源,此處當喻族人聚居地,應指一個地方。「揚南紀之清源」,謂離棄南國之「清源」,則北國當有地名清源而為溫第一故鄉或籍貫。查《元和郡縣志圖》(卷十六),「太原」下有「祁縣,即春秋時晉大夫祁奚之邑也,《左傳》曰「晉殺祁盈,遂滅祁氏,分為七縣,以賈辛為祁大夫。」又有「清源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屬并州。因縣西清源水為名。……武德元年重置。……梗陽故縣城,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左傳》曰「晉殺祁盈,遂滅祁氏,分為七縣,魏戊為梗陽大夫是也。」可見祁縣和清源縣,皆滅祁氏分七縣之一,兩《唐書·溫大雅傳》謂「太原祁人」,是沿襲地望;至唐溫氏族人繁衍,已不止在祁也。
句中「清源」之字面本意,雙關地名「清源」;而動詞「揚」,對字面本意而言是揚棄之揚,對地名而言,則是揚棄之棄。庭筠稍運文心,不但表達了對溫氏開國功勳和忠正門風的自豪,而且巧妙地順便表達了籍貫所在。「揚南紀之清源」等於說了兩句話:離開南國的第二故鄉和發揚祖先本有的清正家風。二者都不是需要隱藏的深意,而其表達方式卻很少被人全看破。其出人意表、類似雙關的修辭手段,頗令人瞠乎其後,姑名之曰「複筆」。
作者文筆如此狡黠,什麼藝術手段他不能用呢?至於「南紀之清源」,即南國佔籍所在,從溫《百韻》詩「行役議秦吳」句看,應在吳地,具體何處,疑似之間,雖然有些猜測,仍尚難論定。因「南紀之清源」之語,我們找到了溫的「北國」籍貫所在。而「南國」之「清源」本身反而相當難猜,大概是個字面和「清源」意思有點相似的地名。安史之亂後,關中士人多南遷。如《舊唐書·權德輿傳》(卷一四八)有「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溫氏先祖很可能也是其時移居南國的。
在此重論溫之生年問題。當年筆者以《上裴相公啟》(《全集》卷十一)「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中的「有道之年」為郭有道郭泰的亡年四十二歲,並且考證《上裴相公啟》啟主是裴度,投啟時間是開成四年首春,而定溫生於公元七九八年(見《溫庭筠生年新證》載《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一期)。原文語境是:
某啟:聞效珍者先詣隋和,蠲養者必求倉扁。苟無懸解,難語奇功。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斯則沒為癘氣,來撓至平;敷作冤聲,將垂不極。此亦王公大人之所慷慨,義夫志士之所歔欷。
啟文開頭說明自己前來投啟的原委。獻寶者先去見隨侯、和氏這樣的識珠玉的人,治病的一定求倉公和扁鵲這樣的名醫。若無裴公之懸解的大力,很難完成不尋常的事功。我已交四十二歲郭有道(郭泰)之卒年,還無罪而蒙受奇恥大辱,這種情況真使我死了也會化為瘴癘之氣,來煩擾公之清政。此案也是朝廷王公大人為我慷慨不平,社會上義夫志士為我感嘆唏噓的。
此處的「有道之年」,就有人認為不是用典,而只是習慣性誇飾當時時代正當「有道」的年月,並認為以別人的亡年稱自己年齡屬於不倫。從溫為詩為文的習慣而言,他有時能造語而令人悟不盡。以上的「清源」就是一個很好的包藏意外內涵的例子。他也能用典而令人看不出。現在面對溫直接在字面上用典的例子,要說他不是用典,是需要證明的,不能只憑印象,而漠視作者本意。作者的本意很明白,他正處在幾乎被害死、至死也不能吞嚥的屈辱和誣陷中,作惡者簡直令人神共憤。作者的苦境已經無以復加,乃至於向自己仰慕的尊長毫無保留地傾訴了自己的冤情和憤怒,他還誇個什麼時代,還顧忌什麼用古人卒年稱自己年齡吉利與否?即使「有道之年」是虛與委蛇地走過場歌唱一下時代,用這個詞語同時兼自報年齡,也合乎溫的修辭習慣;而用「郭有道」的典故,不但表達了他的道德自信,而且強調了賢人受屈的奇冤,極大地增強了求懇的力度。是再恰當不過再自然不過的用典!不識者不為過也。
其實,溫詩文中確有一些特殊用語如「長者」「衡軛相逢」「祀親和氏璧,香近博山爐」「不霑渙汗之私」「楚國命官」「可異前朝」「牽軫」(均見後文)等,有的字面簡單,令人反而不知應如何求解;有的藏深意,卻又求解不成。得解之後,就不會以「有道之年」之用典為奇了。
(二)宗室姻親、公侯裔孫
我們從有關記載和溫的自述推斷他是溫彥博七世孫;且是溫西華的親孫。《新唐書·文苑傳下》(卷一二八)載庭筠為「彥博裔孫」。《東觀奏記》卷下亦云,溫為「彥博之裔孫」。從《新唐書·溫大雅傳》(卷九一),知大雅、彥博、大有兄弟三人,皆有唐開國之重臣。在李淵「肇基景命」的過程中,都曾卓有功勳而封侯拜爵。「高祖從容謂(溫彥博)曰『我起兵晉陽,為卿一門耳』」便是對溫家功名事業的肯定。溫氏和唐皇室之興息息相關,而忠於王事,也是溫家傳統。說到自己的家世,《百韻》詩第五韻自言「采地荒遺野,爰田失故都」。句下原注:「余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於并、汾也」。接下來第六韻「亡羊猶博塞,放馬倦呼盧」。承上由祖業說到自己,謂雖祖上後來以忠直失官,自己猶不改其道;現在只好退出科舉求仕的努力,表達方式不可不謂新奇。「亡羊」句,本《莊子》(外篇卷三)《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溫變用穀因博塞而亡羊之典,其義承第五韻之「失」,謂即使亡羊(即使「爰田失故都」),猶博塞不止;實以「亡羊」喻失去祿位,而「博塞」則喻其失祿位之因,當指溫氏傳家忠直之道也。「放馬」,原作「牧馬」,疑由「放馬」(意同「歸馬」)訛誤而致,用法出《尚書正義·武成》(卷十一):「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本言偃武息兵,此喻放棄競爭,故接「倦呼盧」,謂倦於「博塞」「呼盧」之賭勝,即厭倦於求仕之奔競也。
提到自家今昔變化,他曾說「梓柱雲楣,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臥牛衣」(《上宰相啟》二首之一),其中叫窮部分語帶誇張,誇富部分卻好像真是他幼年的記憶。「梓柱雲楣」,梓木做的柱子和有雲狀紋裝飾的橫梁,標志相當等級的官宦第宅。那麼,庭筠究竟是彥博第幾代孫?他父親狀況又何如?使他還能看到其家族如此繁華的景像呢?
據陸耀遹《金石續編》(202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卷十一《唐八》之《溫佶神道碑》及《元和姓纂》卷四,自溫君攸以下,接其子溫大雅、溫彥博兄弟,以下每代各舉嫡傳長子或唯一被記錄下來的一人,得如下溫氏簡譜二:
譜一:1.溫君攸;2.溫大雅(黎國公);3.溫無隱(工部侍郎);4.溫晉沖(范陽令);5.溫仁禮(長史);6.溫景倩(南鄭令);7.溫佶(太常丞);8.溫造(官終禮部尚書);9.溫璋(咸通八年為京兆尹)。此據近年新出土《唐故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府君神道碑》而定(《新唐書·溫造傳》「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為諫官」,是以溫景倩為一世祖而計算的,與一般將祖父計為二世祖不同)。
譜二:1.溫君攸;2.溫彥博(尚書右僕射);3.溫振(太子舍人,其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4.溫翁歸(庫部郎中);5.溫續(閬州刺史);6.溫曦(駙馬太僕卿,尚睿宗女涼國公主);7.溫西華(駙馬祕書監同正,尚玄宗女平昌公主);8.溫瑒(身世職務不詳);9.溫庭筠?
我們把溫庭筠(798-866?)放在溫瑒後面,是如下這樣推測的。把溫與溫造(765-835)溫璋(?-870)父子各方面做對比,可斷他與溫造父子同宗,應比溫造低一輩,與溫璋同輩。劉禹錫(772-842)有贈溫造《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全唐詩》卷三六五),對溫造剛毅果敢鎮定興元叛亂高度讚揚。劉與溫造應是同輩朋友;劉又與庭筠的業師李程(770-842)是同輩摯友,故李程、劉禹錫,乃至溫造都比庭筠長一輩。溫造則不但在社交意義上長一輩,而且在溫氏宗譜上也比庭筠長一輩,一般應成立。此證雖不嚴格,但結論應是準確的。溫有《上首座相公啟》,啟題有誤或有別解;但溫以宗侄投啟溫造,應可論定,此處為免支蔓不再詳解。
溫晚年作《寒食節日寄楚望》二首之二(《全集》卷九)末聯「獨有恩澤侯,歸來看楚舞」,竟戲自稱「恩澤侯」。據《漢書·外戚恩澤侯年表》(卷十八),所謂恩澤侯,主要指因受皇帝私恩而封侯的皇室親戚、包括駙馬都尉。而在以上二簡譜中,根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卷八三),唐高祖李淵女「安定公主,下嫁溫挺(彥博次子)」;睿宗女「涼國公主,先嫁薛稷之子薛伯陽,後降溫曦(彥博玄孫)」;玄宗女「宋國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溫西華(涼國公主與溫曦子),又嫁楊徽。薨元和時」。《涼國長公主神道碑》(《全唐文》卷八三)有「子西華扶杖而立,茹荼以泣」句。可見溫曦和溫西華,分別是睿宗和玄宗女婿。溫戲自稱恩澤侯,當因這層與唐宗室的關係。溫曦是庭筠的曾祖父,而溫西華則是其祖父。
這種關係,又見於《百韻》詩第94韻「何所託葭莩」句。葭莩,蘆葦中的薄膜,常喻帝王的遠親。《漢書·中山靖王劉勝傳》(卷五三)「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漢書·鮑宣傳》(卷七二):「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故本句謂與唐皇室沾一點遠親也無可依託。
還有一證,即《上裴相公啟》「暗處囚拘之列,不沾渙汗之私」兩句。囚拘,涉帝王變服而被困之典,與溫開成五年《百韻》第84韻「魚服自囚拘」中之「囚拘」同義而且同指,典出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文選》卷三),詳見劉向《說苑·正諫》(卷九),伍子胥諫吳王勿從民飲酒曰:
「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今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此處以「囚拒」代指「魚服」的皇帝,即「受制於家奴」的文宗。故「囚拘」句,不但指自己被列入黑名單而將被捉捕,還指暗中被宦官當成文宗密黨而欲加以囚禁。所以下一句「不沾渙汗之私」,非言霑不上文宗私恩(私恩還是霑了的),而是說霑不上「渙汗」的私恩。渙汗,語出《易·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朱熹《周易本義》「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渙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私,指以私恩受封;如此,「霑渙汗之私」就是以姻親受封而恩寵始終不衰;「不霑渙汗之私」,就是帝王恩渥不能「一出不復收」而(不得不)中斷。這種說法本身實暴露了此啟上於溫從遊莊恪太子之後(當然在「等第罷舉」之前)。溫能從遊太子,除受重臣裴度、尤李程推薦,更靠恩澤侯這層關係被文宗看中,成為莊恪太子侍從,《百韻》詩所謂「霜臺帝命俞」是也;只是在太子被害死後,文宗本人更「受制於家奴」,不如赧、獻,形同囚拘,再也顧不上溫了,故因私恩而發之任命不能貫徹到底,所以溫有「不沾渙汗之私」之嘆。此處所謂「私」恩之「私」,正指溫與唐王室的姻親關係。
(三)太學從師、少年喪父
溫《上裴相公啟》云「自頃爰田錫寵,鏤鼎傳芳。1占數遼西,2橫經稷下。3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思欲紐儒門之絕帷,恢常典之休烈。4俄屬羈孤牽軫,葵藿難虞。處默無衾,徒然夜嘆;修齡絕米,安事晨炊!」
這一段意思是:1.自昔日先祖封田傳位、卓立功勛以來,到自己這一代已是「占數遼西」了。2.其後是「橫經稷下」、即入太學的經歷。3.仰窮師法,入太學也是開始從師的經歷:因而自己能師從仰慕的名儒(李程),尊敬而努力仔細研究他的學問,致力於吟詩作文之道;立志補綴儒家絕學,發揚其美好偉大的常典。4.然後描述羈旅孤兒牽引著柩車、即父親亡故的事件,及其後生活陷於困頓。此四件事,以下依次解釋(但為了方便,把3.「仰窮師法」移後為(八)。
1.《晉書·趙至傳》(卷九二)「趙至……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後「年十六遊鄴,……隨康還山陽,……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趙至先「遊太學」後「占數遼西」;溫則先「占數遼西」而後「遊太學。」這算是變用典故了。自比嵇康忘年友趙至,與他在詩文中屢自比嵇紹可以相參。考慮溫入太學前的年齡,所謂「占數遼西」是否指溫先祖早已遷至的江南某地,即前文所謂「南國之清源」?亦難論定。
2.溫最終離開幽居的江南「清源」遊歷四方之前,曾至洛陽太學讀書而「橫經稷下」。稷下,借稷下學宮指當時的一官辦學校。《百韻》詩第47韻「泮水思芹味」句用《詩·泮水》「思樂泮水,薄採其芹」,也以自己曾在所謂「泮水」讀書,指自己的太學經歷。鑒於溫平生入讀官學應只有一次,所謂「稷下」與「泮水」應指同一官學。而由溫《投憲丞啟》「某洛水諸生,……曾遊太學」云云的直接敘述,知此「官學」即洛陽太學。少年能入太學其實也從一方面說明了溫的父祖輩官品之高。《新唐書·選舉志》(卷四四)「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元和二年,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東都太學生名額甚少,地位頗為優越;根據太學生的年齡限制,可證溫在太學就讀時的年齡當在十四至十九歲之間。更重要的是,他能入太學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當時尚有前輩餘蔭可霑,這就再次證明溫祖輩之官品必須至少是五品或以上(順便指出:溫曦,太僕卿,從三品;溫西華,祕書監同正,正三品)。
3.「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是說自己在太學有了機會,拜師學藝,極盡努力研究其詩文之道。這裡所涉及的老師,是名副其實的授業老師,而且為溫終身敬仰的業師,對溫畢生之為人和為文有重大影響。此人乃李程也。這就是《上襄陽李尚書(李程)啟》「此皆寵自升堂,榮因著錄」和《上紇干相公啟(紇干臮)》「此皆揚芳甄藻,發跡門牆。……丘門用賦之年,相如入室」等語中所指推薦溫侍從莊恪太子的李程。李是當時名儒,又是宗室丞相,仕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與柳宗元劉禹錫為同道摯友。《舊唐書·李程傳》(卷一六七)「程藝學優深,……而居師長之地」。溫的啟文中多次提到他。除上舉數例外,《上封尚書啟》「丘門託質」、《上蔣侍郎啟》其二「從師於洙泗之間」等都是例子。連溫早年由庭雲改名庭筠,後來開成四年應京兆府時改名溫歧,字在蒙,都是受老師的影響而取老師文章中的字眼。下文將專門討論李程在為人和為文上對溫庭筠的特別影響。
4.「俄屬羈孤牽軫」是說,在太學不久,自己便在羈旅中遭父亡之不幸,成為孤兒而牽引著柩車歸葬父親了。牽軫,就是(執紼)而牽引軫車。《禮記·深衣》「如孤子」注:「三十以下無父稱孤」。軫,軫車也,即柩車、喪車,本是一種無輤(喪車上用以裝飾的覆蓋物)之柳車(喪車)。宋聶崇義所纂輯漢鄭玄、晉阮諶、唐張鎰等人所傳之《三禮圖集註》卷十九「柳車名有四:殯謂之輤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輤則曰軫車。」「羈孤牽軫」一句話,包含著父親死難的重大消息,含蓄著多少悲哀淒涼!至此,溫所能直接享受的祖廕基本上斷了。他想「篡修祖業」,已很難了。順便說,此處詳解之,是因沒有注者提過「牽軫」之正解。
在溫陳述他至開成五年為止平生經歷的《百韻》中與此處「羈孤牽軫」等句相應的是第51韻「事迫離幽墅,貧牽犯畏途」;言其後(很可能是三年守喪之後)為事所迫、為貧所累,不得不離開所隱幽居,走上兇險仕途。而第52韻「愛憎防杜摯,悲嘆似楊朱」,謂踏上仕途之始,自己就受到宦官的迫害,而仿徨歧路,不知所之。可見溫與宦官的仇恨起自上一代,與其父死因有關。父亡之後,溫失去經濟上的依仗,連粗茶淡飯也吃不上了(遑論求學)。自己像吳隱之(字處默)冬日無被,夜晚受凍;如王胡之(字修齡)無米下鍋,難為早餐(吳、王事均見《世說新語》及《晉書》本傳)。父親逝世,如此重大之事,溫卻如此含混帶過,當因父被害,啟主裴相公知之,不煩多言也。其事發生在「羈齒侯門」之前;即踏上仕途漫遊四方之前,估計在元和末。
(四)自比嵇紹、痛恨「程曉」
在以上的基礎上,我們研究溫自比嵇紹之隱曲,以及鹽鐵院事件的冤結(詳見《文史》第三十八輯拙文《溫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並從這些間接涉及溫父親的文字,推出溫與宦官有殺父之仇。
只要涉及其父,溫文每隱約暗示,尤引人注意者,他常自比嵇紹。連魚玄機《冬夜寄飛卿》(《全唐詩》卷八○四)也說「嵇君懶書札,底物慰秋情」,居然直接稱溫為「嵇君」了。《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全集》卷六)首聯「嵇紹垂髫日,山濤筮仕年」,自比嵇紹,而將求託的對方李僕射(紳)比作嵇康託孤的山濤。《晉書·山濤傳》(卷四三)「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又《上令狐相公啟》「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語本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文選》卷四三)「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溫自比嵇紹,經常是一串連喻。他用此喻的頻度迫使我們考慮其用喻的深度:他的父親如嵇康一樣也是被害的,應是喻內之義。下引《上吏部韓郎中啟》各段不但重複強調地自比嵇紹,比對方為山濤,而且提到自己老大娶妻,求懇韓郎中,欲謀職揚子院為鹽鐵屬僚,而解決經濟上的拮据。其中頗用嵇康有關典實尤《絕交書》文意;由此不但可以肯定溫父是被害的,也可看出其被害與嵇康不同:是被宦官害的。
其一,「某識異旁通,才非上技。……郭翻無建業先疇(《晉書》卷九四),嵇紹有滎陽舊宅(《晉書》卷八九)」。旁通,博通融貫。嵇康《絕交書》「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這裡自稱如嵇康一樣,不是多方善變,其實是執著於自己的原則。上技,當作「上智」。《藝文類聚》卷三七沈約《七賢論》「嵇生(即嵇康)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莫容」。這裡也是自謂「才戾於時」(見溫《上杜舍人啟》),不為俗世所容。他說自己如高士郭翻(即「野人舟」主人)在京都居貧無業,又如嵇紹在滎陽有舊宅。這四句中三句用嵇康有關典故,而強調性地自比嵇紹。
其二,「仲宣之為客不休,諸葛之娶妻怕早。倘蒙一話姓名,試令區處。分鐵官之瑣吏,廁鹽醬之常僚。則亦不犯脂膏,免藏縑素」。脂膏,《禮記·內則》「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比喻富厚的地位。不犯脂膏,指用不著對方資財相助。免藏縑素,謂不埋沒我這粗陋之才。縑是微黃絹,素是白絹,其色皆織成時所帶二字合成一詞,應指人本來材質;《淮南子·齊俗訓》(卷十一)「縑之性黃」。又解,「縑素」或當作「簡素」,簡樸無華的材質。這裡提到自己多年漂泊如王粲,娶妻甚晚如諸葛。希望韓向上峰申報自己的姓名,加以識別和使用,讓自己成為鹽鐵院屬吏。使自己即可發揮才力,不敢煩對方破費。連諸葛、脂膏、縑素這樣的詞語,也容易被注解者弄錯。
其三,「然後幽獨有歸,永託山濤之分;赫曦無恥,免干程曉之門」。這裡也公然把韓郎中比成山濤,自言願如嵇紹長期依靠山濤的情分那樣,使湮沉無助的自己有了歸依,也就用不著為了生計公然厚顏去干求程曉(宦官)了。程曉,《三國志》(卷十四)本傳載,「嘉平中官黃門侍郎」;其職務雖非宦者所任,其中「黃門」字樣卻正好與嵇康《絕交書》中「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一句中的「黃門」相證,對《絕交書》也算是一種「暗引」。《文選》本文李周翰注「黃門,閹人也。」嵇康是被篡曹魏的司馬氏所害,非被宦官害;這一點與溫不同。溫父非李唐皇家所害,而是被宦官害的。在他多方面自比嵇紹的同時,用《絕交書》中的「黃門」語意,不但曲折表達自己對宦官的深刻仇恨,甚至可澄清人們對他自比嵇紹的可能誤會,當然,他是故意冤枉了程曉。
溫謀職揚子院,而不屑於干求盤踞在那裡的宦官勢力之代表人物。他不把「宦官」直接寫出,甚至不把可代指宦官的「黃門」直接寫出,卻拉了個與宦官無關的程曉來打掩護。只因程曉所任職稱有「黃門」字樣,乃以程曉的名字代指宦官,如此「冤枉」「程曉」,真是匪夷所思。但這正是我們解釋「程曉」這個「黃門(侍郎)」為宦官的文本證據。他干求韓郎中而求職,絕不肯厚顏無恥地干求也在位操權的宦官。當時宦官甚為得勢,士人攀附宦官者並不少,而溫獨以攀附宦官為厚顏無恥;其原因當是宦官為其殺父仇人,忘父仇而干求之,是之謂無恥也。另一方面,他提及宦官的隱晦程度,正可反映當時宦官的勢焰薰天和橫蠻猖獗,也表明溫與宦官勢力的殺父之仇,正十分緊張,而要格外防備。這就是溫自比嵇紹的真正原因。換句話說,庭筠父確實是宦官害死的。僅憑這一點,便可知宦官對溫何等忌恨,專權而害死忠良者永總是防範和忌恨忠良之後,有先輩被害便是便是被忌恨的理由,何況溫並不是一個馴順的被害者,何況其時正在甘露之變剛發生之後。
或許有人會懷疑,宦官多是淺學無德之輩,溫哪裏用得著費如許周折、用程曉這個曾官黃門侍郎的人代指黃門,而代指宦官,來瞞過他們?他們能看懂嗎?事實上恐遠非看不懂。且不說宣詔宦官要懂駢儷文字,所謂「宦官」勢力,也並不一定都是受過宮刑、未受多少教育的皇帝家奴,當宦官橫行之時,朝中乃至州府地方的關鍵位置,往往有宦官的文人代表。應注意的是,揚子院這種商業關鍵機構,是作為當時工商雜類代表的宦官勢力之麇集處,這裡諂事宦官的文人不會少。溫謀職揚子院的行動本身(何況是為了娶妓妻),等於染指揚州鹽鐵之利,難免與仇人宦官勢力狹路相逢。應知「宦官勢力」是包含依附宦官之文人的。
(五)杜蕢相傾,涉血有冤
讀《上韓啟》不問可知,結果是溫非但達不到目的,而且真的招致誣蔑迫害;啟文中提宦官再隱晦也沒有用。該啟提到的諸事,無論時間(開成元年)、地點(揚州揚子院)、事由(娶妻籌備資財而謀職鹽鐵院),已經構成了馬上就要發生的溫在江淮受辱於宦官勢力(所謂程曉)的鹽鐵院事件之諸要素。從上文我們看到溫的身世和個性,他是不羈之才,率性而任真,詩賦冠於一時。他是名相之後,皇室姻親,其父被宦官害死之後,一直「羈齒侯門」「旁徵義故」,周游四方,沉淪下僚。甚至未曾問津科舉之途。年已四十,老大未婚。就在他為婚事做準備,謀職揚子院,求為鹽鐵屬吏部之際,所謂「江淮受辱」事件發生了,簡直是命定地發生了。這是溫平生到當時為止遇到的針對他個人的第一次重大打擊;也是幾乎覆蓋他一生的謠言所自。這場災禍發生在溫庭筠成婚之際,我們也可稱之為婚姻之禍。
從他出生,家庭的顯赫變成朦朧的記憶,他自己奔走四方謀生,憑著文才做個小吏,用他自己的話「常恐澗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風末微姿,未卜栖身之所」(《投憲丞啟》)。他雖自知已在強風之末,卻不甘因此沉淪,與命運的逆鋒不斷抗爭。
「婚姻之禍」中,畢竟發生了什麼?下文我們將看到這個事件的多種文本敘述。前引《上吏部韓郎中啟》是「江淮受辱」原始文件,序號為1。下引《上裴相公啟》一段話也是正面表述婚姻之禍的重要文字,序號為2。然後我們把相關文字記錄,包括作者各種場合的表述和後代記錄,排序至10,互相比較,而求其真。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各種說法中,溫庭筠對受辱事本身及後果的敘述是最可信的。這不但說明他敢愛敢恨,也說明他敢作敢當。而這種個性自然影響他的仕途。
2(前接「安事晨炊」)既而羈齒侯門,旅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涉血有冤,叫天無路。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共興嗟,莫能昭雪。)
這是《上裴相公啟》第二段。先說「羈齒侯門」。羈齒,語出《左傳昭元年》(《十三經注疏》,頁2026)「鍼(秦公子名)懼選,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羈齒侯門」,說自己在父親亡故後,從此多年與羈客同列,開始了遊宦的生涯,謀食侯門。此與溫《上令狐相公啟》(約大中二三年上)言「旁徵義故,最歷星霜」意思可以對比地看:後者謂多方尋求父祖故舊,歷經多年艱難曲折。旁徵,廣泛訪求;義故:以恩義相結的故舊,正反映溫之父祖輩門生故舊頗多而有影響;星霜:星位隨季而移,霜則秋寒而降,故「星霜」謂艱難流年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時間,他一直沒有問津科舉之途;《上崔相公啟》所謂「矍圃彎弓,何能中鵠」也提到自己參加考試也不會考中;這又反映由於家世,他多年宦遊而不能參加考試。這裡的「羈齒侯門」時間很長,大致起於長慶初年(821),包括遊京洛、窺塞垣(約822或823)、入蜀(約827-832)、盤桓匡廬、遄行關內江南等等,直到「旅遊淮上」(開成元年)尚如此。溫的行蹤所及,在溫集中雖可找到一些有關線索,已很難考訂各段旅行的精確時間了。
「羈齒侯門」之末,「旅遊淮上」之時,溫「投書自達,懷刺求知」,指的就是《上韓郎中啟》本身。「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謂哪裏預料到自己就遭受了杜摯(蕢)臧倉者流(宦官勢力)的傾害(見《溫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及《溫庭筠百韻詩考注》前引)。其惡劣的結果是,地方官不管舊情而對自己多積惡念,操政柄者更承其意對自己誣蔑毀謗;都公然蔑視我孤危之人,毫無忌憚加以迫害;不但堵死我中進士的途徑(絕飛馳之路),連謀一個瑣吏位置而養家餬口的路也橫加阻斷(塞飲啄之塗)。親人有冤屈的命案他也無法上訴皇極,有喋血的冤枉啊。滿朝上下、朝野內外都同情他,為他嘆氣,但不能為他雪冤啊(這種情況,非因宦官專權而何,而且是牽連到甘露之變的冤枉)。這就是發生在開成元年的鹽鐵院事件、或謂婚姻之禍。其晦氣所被,不僅開成元年當時蒙受侮辱,也是他此後二十年「厄於一第」的苦因。由於謠言滿天飛,當時乃至後代雜說,對其事發生的時間、原因、結果和性質,捕風捉影、各有異說,連正史也不能免俗。
以上「涉血」,《文苑英華》卷六五七原文作「射血」,是因字音而誤改。不通,應改回。涉血,義同喋血,形容殺人眾多,血流遍地。丘遲《與陳伯之書》(《文選》卷四三)「朱鮪涉血於友於」李善注「﹝涉﹞與喋同。」《漢書·文帝紀》(卷四)「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顏師古注「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喋……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二句謂在所謂「杜摯」「臧倉」造成的血腥災難中,自己也牽連冤枉,而無法辯白和上訴皇極。按此實指甘露之變後形勢,溫所以自稱「有冤」者,除其父早為宦官所害,又因其「親表」當朝元老宰相王涯被殺。
溫本人對其事有忠實的交代,可惜往往因為場合不同,而只是隱晦或不全面的交代,容易造成誤解,我們可分析溫在不同場合的自白,對比各種誣蔑和猜度,仔細分辨對比之後,不但豐富事件的細節,也可看出,歸根結底,溫是忠誠面對其所作所為的。
(六)買妓為妻,積毀銷骨
3溫《百韻》詩第82、83兩韻「客來斟綠蟻,妻試踏青蚨。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就提到「江淮受辱」的因果。其中「客來斟綠蟻」者,說自己乘興而飲酒(很可能是在娶妻之宴上);「妻試踏青蚨」者,其實是「試妻踏青蚨」的倒裝;「踏青蚨」就是不惜錢財;全句解作為了娶(妓為)妻而不惜錢財;其中的「試」有嘗試、犯難、冒險的意思。用五個字概括溫之不惜千金娶妓為妻之事,嫌刻琢而近晦,所以後代文人鮮見得其正解者。此二句其實是說下一韻自己遭致「積毀銷骨」的根本事因,即在江淮買妓為妻的事端。下一韻謂自己害怕這個「微瑕」導致的無窮毀謗簡直要把自己吞噬而否定其全人。買妓為妻就好比是「掩瑜」之「微瑕」。這兩句話是溫開成五年冬對事件的反思和總結。在唐代,士人出入青樓,甚至駿馬換小妾,沒什麼錯失,反而是意興豪邁的表現;但是如果認起真來,要買妓為妻,還是觸犯一點律法的;所以溫承認自己有「微瑕」。如此「微瑕」,官方都很少過問,卻被最為道統所不容的宦官勢力拿來做文章,頗有點諷刺性。
4溫會昌二年所寫《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全集》卷六)也提到此事。「旅食逢春盡,羈遊為事牽。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這裡前二句說自己當此春末之時,羈旅在外,是因有很多政治上脫不開的瓜葛和牽累;接下來,他描述自己做官不像毛義那樣能接到官方任命的檄文,結婚而沒有阮修那樣有名流為之斂錢為婚的排場,與3不謀而合,其言也不過是向李僕射(紳)訴說自己在江淮受辱的原委:因為結婚缺錢,求告揚子院故交才導致無數誣蔑、中傷。
5溫《上鹽鐵侍郎(裴休)啟》「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諑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折之路斷」我硬是把狂放不羈、縱其所欲、尋花問柳的麋鹿野情,來效法琴瑟和鳴、夫妻恩愛、雙飛雙宿的鴛鴦馴性。這就使得九畹幽蘭,傷心於無窮謠諑的毀謗;而那一枝丹桂,竟然斷絕了我攀它的道路。這裡的意思是把狎妓之情變成婚姻之樂,說的似乎含蓄而非常真實,其事就是為妓女贖身、買妓為妻,而橫遭誣蔑的情事:這是溫庭筠坦率真誠的自我表白。他因此竟像屈原好修那樣遭到群小的攻擊,被誣為「善淫」,竟因此長期不能中第而落魄窮途。娶妓為妻,這唐人小說一樣的情節,真實地發生在溫庭筠身上。而對裴休的訴說方式也甚為別致,可謂誠心為知己者言,敢於說明自己的情和性,而且終身不為自己的選擇後悔。
6溫《偶遊》(《全集》卷四)詩有句「與君便是鴛鴦侶,休向人間覓往還」;《懊惱曲》(《全集》卷二)說到「玉白蘭芳不相顧,青樓一笑值千金。」在這兩首愛情頌歌中,溫也表達了確實對此女有「鴛鴦之性」,並且為了這位青樓女子的「一笑」,傾其所有,不惜千金為之贖身,確實花掉了求懇韓郎中所得。這些證據能若合符契地證明溫買妓為妻事的各個細節,應非偶然。
(七)婚姻之禍,謠言不極
當時社會上的傳言和別人的看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前文引述《上裴相公啟》「敷作冤聲,將垂不極」時,筆者故意將其現代漢語翻譯和說明留到現在。不極,本言無限度、沒有窮盡。語本《禮記·儒行》(《禮記正義》卷五九):「流言不極」,鄭玄注之曰:「不問所從出也。」《孔子家語·儒行解》王肅則注之曰:「流言相毀不窮極也。」「垂不極」,意思是不但謠言無窮,而且在謠言上定格,傳之無盡後世,被長期誤會下去,飛卿不幸自言而中也,慘哉。我們也得把本來發生之事和後來的謠傳都加以說明,盡可能指出種種不實之說形成或惡意發酵的歷史過程。
7《玉泉子》曰:「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勖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姚勖其時官位遠非揚子留後,當是位在韓郎中之下的吏員。「厚遺」溫錢帛者,也不是姚,而是韓郎中。至於把溫「笞而逐之」,姚勖只是被傳說成這樣的角色。「多為狹邪所費」與《百韻》「妻試踏青蚨」,只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前者太簡嗇而近晦,後者含輕蔑而失真,把溫寫得像個花花公子。溫姊執姚勖袖不放、使姚因此「得疾而卒」之情節,令人很難置信;託之於其姊,是為增加其可信度;我們連溫是否有此姊也持懷疑態度;因為溫買妓為妻時已非年少(39歲),其姊安能不知,還說什麼「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的話?如此為溫辯護等於借此肯定溫狂游狹邪的謠言。溫為妓女贖身而向揚子院故交求助的行為在《玉泉子》成書時已被誤傳成此等模樣,難怪後代有人發揮想像解之為向妓女乞討、或溫把所得錢財全用來嫖娼,越傳離事實越遠了。另外,溫因與宦官的仇恨而在江淮受辱,受辱之後因不甘受辱而到處訴冤,而加深了宦官對他的仇恨,乃至對他加倍報復,使他幾十年厄於一第;歸根結底,溫長期不能中第,是因宦官對他持續的仇恨。
8《舊傳》「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為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為虞侯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跡,乃兩釋之。自是污行聞於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這個記述竟誤把江淮受辱的時間定為咸通(860-874)中而無端錯怪令狐綯,又把《上吏部韓郎中啟》投啟韓郎中求助這樣的事誤解為「乞索於揚子院」,而無端誣蔑溫(當時已經垂垂老矣)「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無中生有地硬編了他和令狐綯的故事,把他大中不得志歸罪令狐綯。這種時間的錯位,極大地誤導了後世學者對溫庭筠生平的考證。所謂「自是污行聞於京師」也很滑稽。溫咸通七年(866)去世,離「咸通中」(咸通共十四年)有幾年?難道臨死之前還有此等經歷?可見《舊傳》之荒唐和不負責任。這段話唯一的價值是表明庭筠有冤要雪。其中把虞候和溫「兩釋之」的說法,如果合乎事實,倒可能是開成元年(836)溫受辱時,當時的鹽鐵轉運使令狐楚所為,但此事已完全不可考。
9《新傳》「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為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遍見公卿,言為吏誣染」。對《舊傳》多沿襲,唯改成「為吏誣染」近是。所謂「吏」者,應是宦官勢力的代表人,即屈從宦官勢力的吏員。
10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吳興沈徽曰:溫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這話也是溫「江淮受辱」事件的一種簡化和歪曲;雖然話很短,梳理清楚卻很費時。
為弄明白這幾句話的本來意思,我們需要介紹前文《上吏部韓郎中啟》所列舉的原文「其三」句子之前的一段話「升平相公,簡翰為榮;巾箱永秘。頗垂敦獎,未至陵夷。」這段話有闕文。能看出的大概意思是感激「升平相公」為自己寫信,希望他對自己的誇獎和推薦仍然有效。筆者曾推證「升平相公」應是王涯,並且根據王涯封清源縣男,認為王是溫的「清源」同鄉長輩。只是上啟當時王已在此前的甘露之變中被害。溫開成四年《上裴相公啟》「涉血有冤,叫天無路」之言,說到自己在甘露變中有喋血的冤情(有親人冤死於甘露之變)而求救無門,指的就是王涯被害事。此事也在《百韻》詩「威容尊大樹,刑法避秋荼」提到:那本來要尊崇依賴的大樹已經倒下(指王涯之死),所以作者才不得不逃避繁如秋荼的刑法,而「遠目窮千里,歸心寄九衢」;(此即《舊傳》所謂「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也)。又,溫在《經故翰林袁學士居》詩中,自比謝安的外甥羊曇,而實以謝安比王涯,可見王涯可謂溫的長輩「親表」。
由此我們可玩味「吳興沈徽曰」的話了。研究溫在鹽鐵院事件受辱的程度,畢竟是「笞且逐之」(《玉泉子》),還是「為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舊傳》),或「為邏卒擊折其齒」(《新傳》),或「為親表檟楚」(《北夢》)?這幾種說法有差別。兩《唐書》只說因「犯夜」而被傷害的程度。《玉泉子》以「笞且逐」溫的人就是「厚遺」他錢財的官方代表姚勖,就把溫說的很不堪了。而最惡毒的是《北夢瑣言》所記的「為親表檟楚」,就是被自己的長輩親表痛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溫在江淮之所以受到宦官勢力的迫害,因為他是宦官的仇人、宦官久欲教訓他。當時正值甘露之變後,溫卻貿然拿著王涯的推薦信,前來謀職,自然會遭到宦官的打擊,也太不小心了。「為親表檟楚」,原應作「為親表遭檟楚」,即因為親表王涯的緣故遭到鞭打;但刪掉「遭」字後,「檟楚」者不再是姚勖,倒成了溫的「親表」。這已經夠滑稽。不知何人又在「溫」後加上「舅」字,於是傳謠者沈徽成了溫的外甥。《太平廣記》(卷一九九)所引《北夢瑣言》就沒有這個「舅」字。蓋「曾」字模糊,容易被誤認為「舅」,誤認成「舅」後,再參舊本,就成了「舅曾」皆有的版本。以上所說的刪「遭」、加「舅」而造成新情節的情況,是由於宦官勢力散佈的謠言占了上風,而使文人社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溫頗有偏見。
至於溫因江淮受辱而「由是改名焉」,說法近是而不確。溫與宦官早為仇敵,受辱前多年未能應進士;開成四年應京兆府試,經由有司同意,不得不改名就試。所以應改成「由是改名應京兆府試焉。」
在此應順便說明,溫對於婚姻的態度是很嚴肅的。以上開成五年《百韻》「妻試踏青蚨」、會昌二年《五十韻》「婚乏阮修錢」涉及的「妻」都是一人。
這人也是溫大中六年《上鹽鐵侍郎啟》所言與共遂「鴛鴦之性」的「鴛鴦侶」、為之一揮千金的妻子。他在約大中二年(848)《上令狐相公啟》中說「戴經稱女子十年,留於外族;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見後)。這句話的一層意思是自己的女兒已十歲,兒子才八歲。皆與他在江淮買妓為妻而結婚的開成元年(836)相符合。這個兒子就是溫憲,女兒就是嫁給段成式之子段安節者 (見《南楚新聞》)。這位女主人公,其後便是溫終生之妻,溫不顧社會偏見和律法,敢於娶地位遠低於自己的妓女為妻,這本是唐代傳奇一樣的情節。溫對淪為為妓女的這位女士的身心的兼愛,對於女性美的高度的審美鑒賞,確實高於許多薄倖多情的文人,其實是可圈可點的,而且值得深究。但他特別的文學表達、離奇的遭遇和根深蒂固的被誤會,都令人為之浩嘆。溫以名相之後、超群之才、不羈之性和宦官之仇的身份,娶青樓女子為妻,又謀職揚子院以為女贖身。結果招來他生前死後揮之不去的無窮誹謗和誣蔑。這算是命運悲劇,也可看作性格悲劇。但他始終沒有屈服於命運,他到死都一直在積極抗爭。
(八)前修長者,文風所自
溫出生在如此一個家庭,自幼又有這樣的經歷。加上從師的經歷,使他很早就有一種文學的自覺,而刻意地描繪他近乎是命定的、帶有悲劇意味的人生。我們故意把他對自己詩文風格的總結,當成他的「夫子自道」,放在此處特別研究,以便於由此鳥瞰他的藝術人生。
李程對溫為人為文影響可謂至巨。這種影響,尤見以下《上蔣侍郎啟》(二首之一)的話「頗識前修之懿圖,蓋聞長者之餘論。顓愚自任,并介相忘。質文異變之方,驪翰殊風之旨。粗承師法,敢墜緹緗」。其中首二句含一般和特殊的雙重解釋而特別有趣。
初讀此「頗識」二句,如汎汎而言;但細味之,所謂前修懿圖、長者餘論云云,必有所專指。因作者所「頗識」與「蓋聞」者,引導溫達到了深化的人生認識和獨特的文學造詣,明顯含具體而與眾不同的內容,只用泛指解釋不夠。試詳解之:前修,泛指前代有修為者,出《楚辭·離騷》「謇吾法夫前修兮」;又因屈原取法前修,而專謂屈原為人們共仰之前修也。長者,泛指年高德劭者,特指溫之業師李程。前者如《漢書·陳平傳》(卷四十)「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後者則見《新唐書·李程傳》「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侻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讀若常)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原來溫師李程還有這樣一個外號。懿圖,美好的謀劃。餘論,高論、宏論,激揚之論。《史記·太史公自序》「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此即「前修之懿圖」,也是李程詩文創作之旨趣所在,飛卿詩文諷諫之旨所祖也。至於「長者之餘論」,指飛卿為人為學多有所聞於李而為李所褒揚也。一言以釋之,飛卿遠師屈原,近師李程也。此種藝術表達手法,如前文提到的「清源」,可稱之為「複筆」。是溫所特有的一種祖於民歌而有所創新的藝術手段。
正因「前修之懿圖」「長者之餘論」在為人為文上的影響,溫才達到以下境界。一是為人之「顓愚自任,并介相忘」的作風,謂不管出處仕隱,總堅持自己的愚昧(實際上是原則)。顓愚,蒙昧愚蠢也,是謙稱自己偏執不知變通。并介,能獨善兼濟也,語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劉良注「并,謂兼利天下;介,謂孤介自守」。并介相忘,指超越了出處得失的精神狀態。
二是為文之道,或者說是溫「夫子自道」式地總結得自其師的詩文特點,即他的「質文異變之方,驪翰殊風之旨」。這裡首先是「質文」風格的互相變化,乃至相反相成,達到質文貫通。然後是「驪翰」習氣的與時推移,而兼善古今各種體式,達到古今貫通,包括對古今民歌和廟堂文學的得心應手。「質文」,此專指文風的質樸和華美、或質直和藻飾。《文心雕龍·時序》「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又《通變》「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驪翰(黑馬和白馬)殊風,代表不同時代的不同文風。《全唐文》(卷十三)李冶《敕建明堂詔》「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文選》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文選》卷三十六)「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李善注引《禮記·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鄭玄注「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粗承師法,敢墜緹緗」八字承上,說自己在「質文異變」和「驪翰殊風」的理解和運用上大致得其業師李程之學,不敢荒棄師傳之秘。所謂「師法」,乃本師所傳、能成一家之言的學問淵源,此照應上文「長者」,還是指李程之教。緹緗,丹黃或淺黃書帙,因代指學問。
在「質文異變」與「驪翰殊風」理解的基礎上,在古今質文、雅俗融會貫通的基礎上,作者在《上蔣侍郎啟二首之二》中評價了自己的作品「味謝氏之膏腴,弄顏生之組繡。勞神焦慮,消日忘年。雖天分不多,尚慚於風雅;而人功斯極,劣近於謳歌。」這幾句自謂涵泳顏、謝之間,經過長期日夜苦思,形成自己豐腴華麗的風格。雖然自己天生的悟性不夠,所作詩還趕不上《詩經》風雅的自然真趣,但因費盡了個人功力,只能接近以《楚辭》為大宗的文人辭賦的風骨格調。膏腴,本指土地肥沃;喻繁富生動的詞彩。組繡,本謂華麗的絲繡服飾,喻繁富炫麗的文藻。鍾嶸《詩品上》謂謝靈運「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耳!」又評顏延之曰「體裁綺密,情喻淵深」,且引湯沐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又《南史顏延之傳》(卷三四)載「顏延之問鮑照己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公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謳歌,語本《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當指楚辭。可見,在艷和素、濃和淡的風格選擇上,作者顯然偏好濃艷。
另外,溫在要求作史官的《上杜舍人(審權)啟》中自表其才具志尚也說「亦曾臨鉛信史,鼓篋遺文。頗知甄藻之規,粗達顯微之趣。」他說自己也曾寫信史,拜讀前朝遺文。所以很懂為文作詩選擇詞藻的方法,也大致知道使文旨顯現呈露或幽深隱蔽的旨趣。尤其後者,關於其記實文字的寫作原則,其實類似「春秋之筆」,值得特別注意。臨鉛,《佩文韻府》所引作「懷鉛」。《西京雜記》「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懷鉛」,懷藏鉛粉,「書寫」的意思(臨鉛,猶臨文);懷鉛信史,就是寫信史。「鼓篋」與「懷鉛」一樣是動賓詞組,但作為古文一種特殊句法,仍可帶上賓語。鼓篋,本謂擊鼓開篋;《禮記·學記》(卷十八)「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玄注「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此處用如動詞,意謂開始拜讀、學習,而學習的對象是「遺文」,應是前代史家典範之文。甄藻,選擇辭藻;此處「甄藻之規」接上「鼓篋遺文」,正指為文作詩選擇詞藻遵循的方法。顯微之趣,《易繫辭下》:「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這裡說到《易經》對於文學藝術的一種特別的影響:要彰顯過往的歷史和成敗得失,體察預見事務於未然;所以就能使玄微者被顯示,使幽深者被闡釋。從作品主旨的角度看,是顯露還是隱蔽、直言還是曲言之,當然都在作者有意識的控制之中。所以,文章主旨顯微、直曲也總在詩人的控制之中。
綜上言之,我們大體上可以這樣理解溫「夫子自道」的詩文風格。他有些詩文偏於艷麗,其實是有意如此的。無論是率意之作,刻意之作(如《百韻》詩),或得意之作(如《洞戶二十二韻》),古今、質文、雅俗、濃淡、艷素、顯微、直曲諸因素,總在藝術把握之中。他把詩文寫成什麼樣的風格,常常是自覺而為之。因為他能質能文,能古能今。能歌齊梁體,能唱盛唐音。能直能曲,能顯能隱,能賦忠臣志,能訴兒女心。能濃能淡,能淺能深。能囀黃鶯喉,能弄廣陵琴。能剛能柔,能屈能伸,能為別鶴操,能為臥龍吟。只是由於他平生遭際多為人曲解而處於險惡濁穢中,有時極力深藏其意,而使自表深心之文,反而被誤解。豈不憾哉。他的率意之作,一些一揮而就者,雖然酣暢淋漓,有時會落人詬病;刻意之作,則字斟句酌,往往用力過猛或藏意太深,常常會誤導讀者。而得意之作,則悠然得其中,洋洋乎美哉。但也是為知者言,非如白傅之令婦孺皆能會心者也。他色彩斑斕、變幻出奇的詩文,和他多難浮沉、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也是一種自然的搭配。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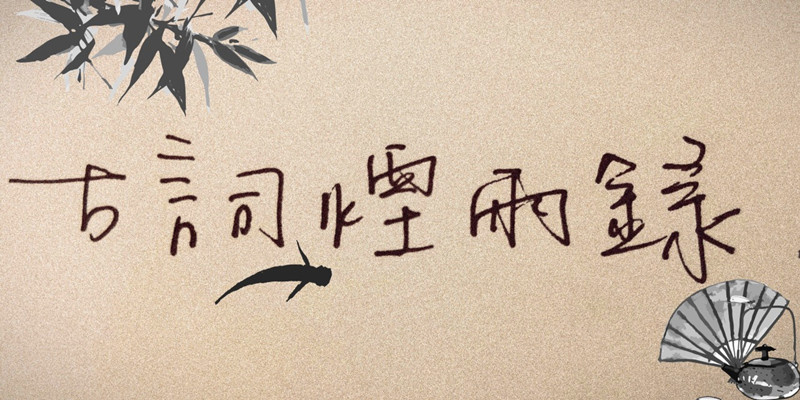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