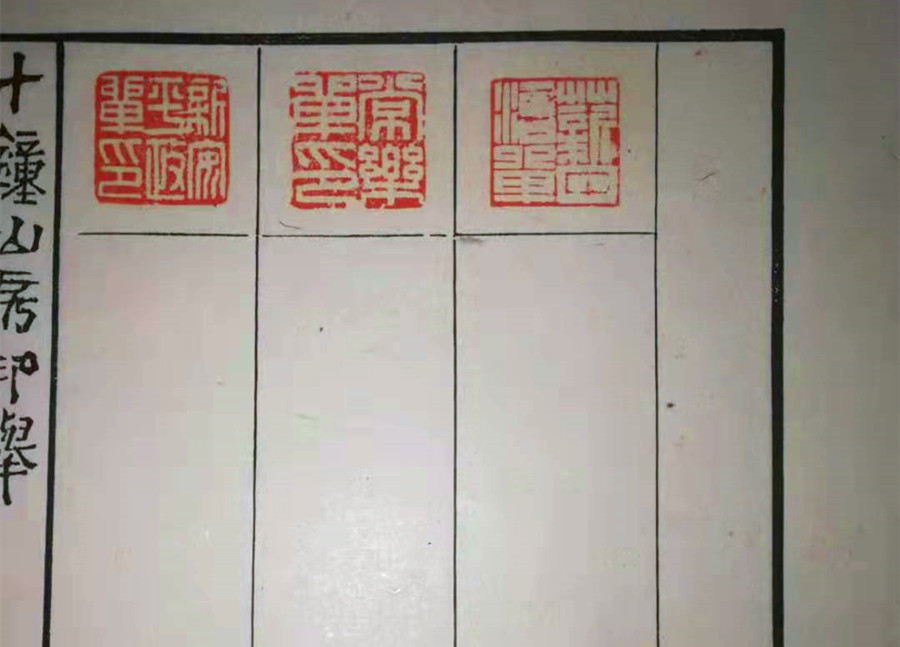做一个记者,是这一辈子的梦,但最终未能圆梦。
除了上述去《青年园地》未能实现,还有三次做记者的机会,其中一次是我“放弃”,另外两次是机缘不够。
大约1990年前后,那时已开始想着“转业”(团的专职干部转岗被戏称为“转业”),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除了组织安排,当事人本人也可以自行联系接收单位。在诸多选项中,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去报社做一名记者,这个似乎与祖父曾在上海滩做过自由记者无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编了十年的机关刊物《青岛团讯》,因工作的缘故,与新闻媒体的记者们频繁接触,羡慕那种工作方式,自信能胜任这一职业。
于是想“走后门”,到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临时办公地点纺织疗养院(当时市级机关正在准备东迁,各部门都在临时地点办公)院内,找当时早已“转业”进入市委宣传部任领导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永章,自忖与他很熟,想请他给下属的青岛日报打个招呼,当时我是副处级,放弃身份,去做记者,不存在不好安排的情况,应不是难事。
但王部长拒绝了,他一再说,已经是副处级了,放弃了可惜,尽管我再三表示不在乎,他还是以此为借口不同意。只能感到遗憾了。后来一再想,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不给我办呢?无法理解。
大约1996-1999年前后,我接触到民革青岛市委宣传处的葛陆处长(已故),当时他们那里有一个中山书画院,围绕香港回归,我给他们组织了一些书画活动,还从北京请来一些书画名家,在大学路美术馆(当时不叫美术馆)举办了'97书画展。借此机会,与民革市委会的领导们有接触。这时,我获悉,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有在青岛设立记者站的想法。通过葛处长引荐,在市府后楼府新大厦,民革中央的工作人员借在青开会期间,召见了我,与我谈话,对我加以肯定,于是我抱着希望一直在等待。但没了下文。据说民革青岛市委会派人到我原单位外调,原单位组织部门对我加以否定,并不认可。究竟是哪个“原单位”(因我这时有好几个“原单位”),语焉不详,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原《青岛日报》记者,姓名一时想不起来,他调到京城某媒体,奉命在青岛做记者站,想招募记者,在报上发了招聘启事。那时我在家赋闲,看到消息,便去应聘,他认识我,见我笑笑,开玩笑说,你还用来应聘,关系调过来就是。后续如何,已记不清,算是一段插曲吧。
在此之前,其实我还“主动放弃”了一次机会,即将离开团岗位时,有说法让我到报社政工处做副处长,算是平调。但我“不想”做政工。诡异的是,这次的机会,究竟是否像我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真实存在,不得而知。也许是误听臆想?也算一次吧。
机会就是这样,放弃了,错过了,再也没有可能重续。这就是人生吧。
这辈子,一直都在专业新闻出版体制的边缘游离——没有进入报社,成为在编记者、编辑;进入了出版社,又没成为专业编辑,只做一些行政辅助工作。
后来,有机会频繁接触到编辑业务,编校了上百种出版物,又两次进入报社做夜班审校,看着版权页和报眉上自己的名字,多少满足一点虚荣心。
神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赛48:10)我希望自己能对得起这一拣选,不辜负这份信任,以余生侍奉万能的神。而40年的从业经历,以编校上亿字读物的工作实绩,聊以自慰,也消淡了未能成为专业记者的遗憾。
找到一张老照片,与本文无关,贴在这里做题图吧。这是1980年代初期,刚进机关不久,被安排去浙江建德千岛湖边参加上海《青年报》的一个全国发行联络会议,何以让我去,而不让宣传部的人去,应该是当时我负责编辑机关刊物,与媒体多少有联系吧。其实这个会,去了才发现,与我的本职工作并无关系。就那么公款旅游了一圈,后来想想也真是不值。这次会议,我是去晚了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我初出茅庐,毕业不久,那时几乎没独自出过远门,火车在杭州下车,不知道建德在什么地方,一路打听着,乘坐很简陋的长途汽车到了山区,那时的建德县还很落后。会议期间,与会者游览了瑶池(地下溶洞)和千岛湖,当时千岛湖(即新安江水库)刚刚蓄水完毕,还没对外开放,据说我们前面,西哈努克先生刚刚游览过。会后,与会者沿富春江一路向下游赶去。中间在桐庐县逗留。最后在杭州开总结会,散会。
大家在富春江的游船上,听上海《青年报》总编辑施惠群老师讲富春江的故事,讲《春江花月夜》轶事,拍下了这张照片。
图中,我在后左二,左一是安徽团省委研究室梁晓莹,后转业进安徽省旅游局,保持联系多年。后排左四是济南团市委秘书长,有语言天赋,模仿各地方言,惟妙惟肖,据说后来东渡扶桑。前排右二是施惠群老师。其中有一位是上海团市委的毛国云,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位。后来也多年保持联系。
周晓方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