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衝霄一瞬,折桂事迷
溫在侍從莊恪太子之後,經多方(裴度,崔珙等)援引,得到有司的許可,改名溫岐,字在蒙,參加京兆府試,而得「等第」。改名,是為避開宦官仇敵的阻撓。只是改名事終於泄露,溫集誣蔑與讚譽於一身而功敗垂成,雖經多方訴求,終於無人能助,而慘遭「罷舉」,不得不「南遁」而暫時離開長安這個政治和是非的中心。溫雖只在應京兆府試時以溫岐為名,此名卻從此留在「等第罷舉」名單上。
(一)搏躍雲衢,等第罷舉
溫《百韻》詩詳細地陳說了自己改名參加京兆試,得「等第」的榮耀和其後遭「罷舉」的委曲(為宦官勢力所忌)。詳見筆者《百韻詩考注》(1-29韻)及《溫庭筠改名補考》。
「等第」是一種特殊的、由京兆府解送的鄉貢進士。唐朝和後世很多王朝一樣,經常優惠京兆府所貢士,京兆府解送不但名額甚多,而且一度幾乎等於及第。《唐摭言》(卷二)記其事:「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知貢舉)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茍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又「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曰:「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為名,等列以十人為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沖宵之漸也。今所傳者始於元和景戌歲,次敘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可見,得京兆府解送者,簡十分榮光,有時就全部中第了,至少十有七八成中第。如果有不中第者,京兆府還要「牒貢院請落由」,即向有司詢問不中第的理由。罕見的「等第」而「罷舉」者,《唐摭言》都有記錄,自元和七年至乾符三年(812-876)共三十三人。溫在其例。
「等第」既是一種特殊鄉貢進士。得「等第」者,要不要再次被(京兆府)薦名而參加進士試?換言之,「等第」而「罷舉」者再應考,是否必須再次取解?愚以為,是不必的,他願應考多少次都可。我們在研究溫的啟文時,始終未見「求解(送)」文字,而只見要求推薦中舉之意,可見他能參考是肯定的。直到大中十三年貶尉隨縣之時,官方還說他「夙著雄文,早隨計吏」;仍然把他當成「早隨計吏」的「等第」者。《唐摭言》卷二也說他「為等第久方及第」;說明他多年之後,仍是以當年「等第」身份終於中第;可見一旦得到京兆府薦名,就不需要再次薦名,或從別處取解;因京兆薦名而未中第已是特例,得薦名者有資格再考是理所當然的。
以上是對「等第」的介紹,以下是溫對自己得等第的描寫,其詳盡僅次於《百韻》。
《上崔相公啟》云:「矍圃彎弓,何能中鵠;邱門用賦,尋恥雕蟲。……豈謂不遺孤拙,曲假生成。拔於泥滓之中,致在烟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鶯谷翩翻,終陪逸翰。此則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乘變律之機,未得捐軀之兆。豈可猶希鼓鑄,更露情誠。」
其中「矍圃」,古地名,即矍相之圃,在曲阜;後借指學宮中習射之所,此處喻考場。中鵠,射中靶的,比喻考中進士。《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者各射己之鵠」。所以「矍圃」二句,是說自己舊日(鹽鐵院事件前)若參加科舉考試,哪能考中。而「邱門用賦」二句,前已論及,比喻通過師門使當道者用己所長,指自己因李程之薦而為莊恪太子東宮屬官的經歷;這時溫一心侍奉太子,自放下應試文章的雕蟲小技了。「豈謂不遺孤拙」以下,則敘及「等第罷舉」之事。他說想不到對方不肯遺漏自己這個不善應對的孤兒,想方設法栽培自己,把自己從泥涂中救拔出來,而直上九霄。乃使龍門之魚,不再受困;新鶯出谷,和高飛鳥兒作伴。這真是如父如師如君的恩典,吹潤萬物的春風。但是我徒有你登庸為相的機遇,卻沒有得到為朝廷效命的徵兆。我怎麼可以還希望你栽培提拔、在此又誠心哀求呢?此處應特別注意的是,溫極力感謝對方促成自己取得「等第」的恩德後,話鋒一轉,說到自己徒然當此對方入相的「變律」之時,卻沒有得到真正實惠的擢拔,這正說明溫空有「等第」之名,馬上就要被「罷舉」了,所以他還是抱著最後一絲希望「猶希鼓鑄,更露情誠」。可見本啟上於開成四年秋「等第」後、開成五年對方入相後、尚在開成五年溫最後被「罷舉」之前。《舊唐書》本傳(卷一七七),崔珙「(開成二年)六月遷京兆尹。與其兄崔琯『兄弟並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崔珙判吏部東銓時,當對溫成莊恪太子東宮屬僚有所助力,而為京兆尹,也正是可以促成溫得「等第」(京兆薦名)之職。可見在崔「開成五年夏五月,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通鑑》卷二四六)之前,溫已得到崔的賞拔推薦,則本啟溫之求崔在自己「等第」後再施援手,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崔應是執行裴度既定政策的人物,曾幫溫改名應試得等第。可惜這次崔已無能為助,他就是《百韻》詩中「市義虛焚卷」所指的人物。本啟當作於開成五年五月之後。
不研究溫「等第罷舉」事,則無法校訂其文。請看《上學士舍人啟》(二首之二)之例:今乃受薦神州,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4)。既而臨汝運租,先逢謝尚;丹陽傳教,取覓張憑(1)。輝華居何准之前,名第在冉耕之列(3)。俄生藻繡,便出泥沙(2)。
按照這個原文順序,譯成現代漢語是:我如今受薦應京兆試,和文人墨客一決雌雄高下;但是手徒持硯臺和坐席,而毫不知如何走下去。過後就像臨汝令袁勖之子袁宏「以運租為業」、在江上吟詩而遇到謝尚一樣;又像丹陽尹劉惔「遣傳教覓」之而給以薦舉的張憑一樣。我的榮耀就居於有個驃騎哥哥何充的何准之前,我的名聲就達到以德行著稱的大儒弟子冉耕之列。剛剛有了被獎掖的榮光,就脫離了被埋沒於污垢泥沙之中的厄運。
以上的句子,無論原文,還是現代漢語的詳細翻譯,都念不大通。關鍵在於「今乃」引起的四句說的是現在的處境:受薦神州而彷徨歧路,這是已達到「等第」之殊榮,而面臨遭「罷舉」的窘境。下接「既而」云云,是在「今乃」之後,也就是現在之後!你看他「現在」以後,居然有所遇而有所榮,結果是名聲高揚,可比大儒弟子;繼之而來的就是脫離污垢了。我們要問:既受薦京兆薦名而面臨罷舉,正在難處,還說甚知遇、輝華、出泥沙等虛浮話?但是我們如果依照以下的順序讀,意思就全捋順了:「既而臨汝運租,先逢謝尚;丹陽傳教,取覓張憑(1)。俄生藻繡,便出泥沙(2)。輝華居何准之前,名第在冉耕之列(3)。今乃受薦神州,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4)。」這裡的「既而」是接前文的「潛虞末路,未有良期」等語而言,他說那以後,自己就像袁宏遇上謝尚、張憑遇上劉惔一樣被知遇,剛有了榮光,就脫離了污濁,我的寵榮超過了有個驃騎哥哥的何准,我的名聲也達到如大儒弟子冉耕。(所以)得京兆薦名,一時甚為榮耀,參加京兆試。可惜的是,我現在手中空持硯臺和坐席,而毫不知如何走下去。所以我們認為,原文的句子順序是在文章流傳過程中被顛倒了。這樣,根據對「等第」和「罷舉」的理解,我們校定了原文的顛倒。
投啟時間由「今乃受薦神州,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一語而定,即在開成四年已得「等第」和開成五年最終被「罷舉」之間。觀啟中語,啟主一度對溫相當賞識而力加推薦,在幫助溫得「等第」一事上曾予幫助。
如果不把「侍從太子」和「等第罷舉」研究透徹,溫有些話簡直是一種隱語。例如《上令狐相公啟》「自頃藩床撫鏡,校府招弓」,用了兩個相當生僻的典故說自己昔日侍從莊恪和等第罷舉兩個經歷,要費不少力氣才能大致解開。藩床,當指皇親藩王居所;藩床撫鏡,是皇子悲念母親的典故;此以莊恪太子悼傷其母王德妃(開成三年八月死)實事,指溫為太子東宮屬官時(開成二三年間)所見,而指代其時其事。從下引有關文字可窺見其典源。《文選》卷五八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云「慕方纏於賜衣·悲日隆於撫鏡。」李善注前句引《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則「賜衣」(及「視篋」)是皇子思念母后之典。李善注後句引《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漢宣帝祖母,戾太子之母)合採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緘以戚里織成錦。」則「撫鏡」(持鏡)亦皇子軫念已故皇妣典。唐丘說《郊廟歌辭·儀坤廟樂章·太和》詩「孝哉我后,沖乎乃聖。道映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篋,情殷撫鏡」(《全唐詩》卷十四及卷九四),當用相同的一組典故,亦代表皇族乃至臣僚懷念皇妣深情。儀坤廟本為皇后而設:《唐會要》(卷十九)「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廟在親仁里。」另外,《全唐文》卷九載唐太宗《造興聖寺詔》(又見《廣弘明集》卷二八):「思園之禮既弘(衛子夫冤死,其孫漢宣帝追諡思皇后,其陵園為思后園,簡稱思園),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從中亦清楚可見「撫鏡之情」的思母含義。
「校府招弓」應解作「京兆府招攬人才」,指溫的下一段人生經歷,即開成四五年間先「等第」而後「罷舉」事。校府,當以負責比試騎射術的兵部有司代指皇家或京兆府。招弓,語出《左傳·昭公二十年》(卷四九)「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孟子·萬章下》(卷十)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弓)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後遂以「弓旌」指招聘賢者的信物,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古文苑》卷十九)「四府併辭,弓旌交至。」章樵注:「弓旌,所以招聘賢者。」而由上「弓以招士」及「(招)大夫以(弓)旌」衍生「招弓」(亦作「弓招」)一詞,謂延攬招聘賢人德士。例如裴度《劉府君神道碑銘(並序)》(《全唐文》卷五三八)「初感招弓之遇,猶懷捧檄之惠」。
能夠侍從莊恪太子及在太子死後第二年得「等第」,溫主要是得到了李黨關鍵人物的支持。而在開成後期,牛黨執政,楊賢妃得寵,譖死太子母王德妃後,又欲加害太子,這卻正好被宦官利用。仇士良等與楊賢妃合謀害死太子之後,唐文宗又立唐敬宗之子陳王成美為太子,得到牛黨宰相李鈺支持;楊賢妃陰請以(安)王為嗣,未被認可,而得到同族牛黨宰相楊嗣復的支持。其後溫等第而罷舉,多因李而成,而未必因牛而敗也,因宦官而敗也。及文宗死,仇士良欲重己功,乃立武宗,並向武宗建議殺掉李鈺、楊嗣復、楊賢妃、樞密使劉弘逸(支持安王溶)、薛季棱(支持陳王成美)。只是由於李德裕的進諫,才保住了李鈺、楊嗣復的生命(其他三人皆賜死)。會昌初李德裕執政,也借重了宦官楊欽義的力量。他為了迎合新君唐武宗的自衛心理,更為了掃平叛鎮的國家大局,不得不與專權的宦官仇士良等達成一種妥協,而全然不用文宗所選侍從莊恪的舊臣、又與宦官有宿仇如溫者。所以經過了開成年間的幾度大起大落,溫即使在侍從太子過程中頗有美聲,在會昌一朝,仍被完全摒棄不用,不得不賦閒林下或恢復「羈齒侯門」的生涯。實際上是成了常被南北司之爭所左右的牛李黨爭的犧牲品。這一點,溫是完全看清楚了的。他明白自己「依劉薦彌,素乏梯航;慕呂攀嵇,全無等級」(《上崔相公啟》),令黨人不喜歡;一直到大中五六年間的《上鹽鐵侍郎啟》中他還說「觳觫齊牛,釁鐘未遠」。「觳觫」句,典出《孟子·梁惠王上》「王見之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見其觳觫。」齊牛,供祭祀用的牛。齊,讀如齋;釁鐘,新鑄鐘,殺牲以其血塗其釁隙,因以祭之也。此句意謂但愿戰戰兢兢的自己不像齊牛那樣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而能遠離「釁鐘」的命運。可見,直到大中時,他坎壈多難而一直未找到政治出路,像「齋牛」一樣。
(二)求官求第,徙倚何依
到了大中時,唐宣宗一反會昌之政,他才有了再試登龍門的機會。他在開成年間侍從太子和「等第」的經歷,使他在大中初之後,有了求官和求第兩個努力方向。有時似乎是二者並行。《舊傳》謂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新傳》也說「數舉進士不中第。」我們可在一定程度上證明這種說法。但從溫現存的寫於大中朝的啟文中,很難看出他畢竟真有多少次應舉而不得第,倒有更多的場合是在求官。其實,求官必須有進士身份,求第則為得到這種身份;對溫而言,他已得「等第」,離「等第」照常理而言應只差一點,溫卻為此費了近二十年時間。這就是《唐摭言》卷二所言「為等等後久方及第」。先研究《上蔣侍郎啟》二首。其中第一首透露的時間線索很清楚,一是「遂揚南紀之清源」句,考其時,應是應是開成末「南遁」之後,從自己南方的「清源」故鄉又重回長安了,所以應在會昌末或大中初。二是「三歲而行,士人之常準」。其中「三歲而行」,原作「三月而行」,多方尋求,不能解其何以為「士人之常準」,但改為「三歲而行」則暢然得其解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禮記·檀弓上》「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吾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玄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摯虞《師服議》:
「自古弟子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是為「士人之常準」。按溫師李程(766-842)卒於會昌二年;此處說,其師已去世不止三年,心喪已畢,自己應仕進了。可見上啟時間也至少在會昌末或大中初。而從第二首看,「從師於洙泗之間,擢跡於湘江之表」,前句以「從師洙泗」比喻從師李程,後句乃以「擢跡湘江」比喻自己事莊恪太子。「既而文圃求知,神州就選。遂得生芻表意,腐帚生姿」則指開成四年間溫得「等第」事。對溫這些重要經歷,蔣都很熟悉。其時當然在會昌初以後,是在大中初。
第一首末尾「輒以常所為文若干首上獻」,第二首末尾「謹以新詩若干首上獻」。兩首分別獻詩、獻文,應該同屬於一次投卷的行為。兩首啟文除分別解釋自己得自業師的為詩為文風格外,第一首「伏以侍郎宏繼濟之機謀,運搜羅之默識。思將菲質,來掛平衡」和第二首「伏惟侍郎稟生成之秀,窮先哲之姿。言成訓謨,信比暄燠」,似都說前來投奔依靠,未必是為應試。
再看《上鹽鐵侍郎(裴休)啟》。其中「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鶯谷之春」,是說在啟主裴休知貢舉的大中四年,自己仍然落第,是年當然必曾應第。此啟上於裴休大中五年二月為鹽鐵轉運使之後,大中六年八月入相之前,啟中語「俯及陶甄,將裁品物」說明其時已近裴入相之時。啟中「倘一顧之榮,將迴於咳唾,則陸沉之質,庶望於騫翔」之句,則可見溫所求於裴者,並不專指中第而高升也。
還有《上封尚書啟》「伏遇尚書秉甄藻之權,盡搜羅之道。誰言凡拙,獲預恩知。華省崇嚴,廣庭稱獎。自此鄉閭改觀,瓦礫生姿。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跡;而丘門託質,不負心期。一旦推轂貞師,渠門錫祉。顧惟孤拙,頓有依投。」
大意:這一段說,當年封尚書「秉甄藻之權」、搜羅人才時,庭筠以「凡拙」之資,在其寵遇之列,而被「稱獎」於「廣庭」,從此提高了聲名和身價。按溫《上紇干相公啟》亦有「此皆揚芳甄藻」之語,實指紇干臮以刑部員外郎身份任吏部書判考官,受李程等之託,錄用溫庭筠為莊恪太子侍從文人。此處的「秉甄藻之權」應也指參與開成二年吏部銓選。兩《唐書》本傳都記封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趙璘《因話錄》卷三謂紇干「崔相國群門生也」;而「崔群,元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出院,拜禮部侍郎」(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八引丁居晦《翰林學士壁記》。所以封敖和紇干臮都是元和十年進士、崔群門生。他們都碰巧在開成二三年間任吏部東銓的考官,也很自然地都在錄用溫庭筠侍從莊恪太子之事上起過或多或少的積極作用。所以下文接著說,只因自己從遊莊恪太子,不能陪伴隨侍封敖左右;但是他畢竟未辜負本師(李程)希望,在侍從太子之事上有所建樹。而己一旦以其資質為正人獎譽,就被官家賜福,使他這孤苦愚拙之人,馬上有了投身之所。
解釋:鄉間,應從《文苑英華》卷六六二作「鄉閭」;本指鄉閭弟子,此謂文人社會。《後漢書·樓望傳》(卷七九上)「操節清白,有稱鄉閭。」瓦礫生姿,自謂不才得提拔,有了身價。丘門託質,謂託靠本師奧援;不負心期,沒有辜負老師心中對自己期許的美意;換句話說,溫侍從莊恪太子、表現良好。推轂:本義推進車轂,引申為引薦助成之意。《史記·魏其武安列傳》(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貞師,語出《易·師》「師,貞,丈人吉,無咎。」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孔潁達《正義》曰:「丈人謂嚴莊尊重之人,言為師之正,唯得嚴莊丈人監臨主領,乃得吉無咎」。故「貞師」就字面講,本意為「正眾」,此處指公平擢拔眾賢人。渠門,《國語·周語》「渠門赤旗」。韋昭注:「渠門,旗名。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牙門本謂營門,後漸移用於官署,封演《封氏見聞記》:「軍前旗曰牙旗,近俗尚武,遂通呼公府曰牙門。」牙門即衙門、官府之意,此處猶言王府。朱起鳳《辭通》按曰:「衙牙同音通假」。錫社,賜土,即分茅裂土之意。或以此指封尚書之被封。揆諸此處上下文,於義不通。疑「社」字當作「祉」。「錫祉」即賜福。語本《詩經·大雅·江漢》:「用錫爾祉」,乃天子賜惠下臣之語(非一般官僚擢拔幕賓可用),在此處仍指經由皇帝(王府)詔命自己得以為莊恪太子侍從文人。頻,應從《文苑英華》作「頓」。顧,轉折連詞,反而;惟,無義。孤拙,自指。依投,指依靠和投奔的對象。
下文接言:今者正在窮途,將臨獻歲。曾無勺水,以化窮鱗。伏念歸荑,猶憐棄席。假劉公之一紙,達彼春卿;成季布之千金,沾於下士。微迴咳唾,即變升沉。羈旅多虞,窮愁少暇。不獲親承師席,恭拜行臺。輕冒尊嚴,伏增惶懼。大意:現在又值春試將臨之際,竟無脫厄之方。希望對方還有憐舊之心,體恤自己始終一心報國之志。他含蓄尊敬地希封兌現其諾言,也就是寫一封信給當年的禮部侍郎,稍稍美言幾句,自己的命運也就大變了。自己則羈旅愁多無暇,所以「不獲親承師席,恭拜行臺」。也就是沒有機會到封尚書任官的「行臺」拜見聆教。自己只能這樣輕率地冒犯對方之尊嚴高峻的地位,伏在庭除,更是惶恐懼怕。
歸荑:歧解甚多;《邶風·靜女》「自牧歸荑」(牧,郊外。歸,通饋)鄭玄箋「荑,茅之初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也。」似即溫取義處。以意度之,上句從溫本人角度言,言其志有始有終;下句從對面著筆,懸想對方憐恤舊交。故「俯」當作「伏」。《晉書劉弘傳》(卷三六)曰:「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春卿,指春官,《周禮·春官·大宗伯》載大宗伯掌國之大禮, (即後世禮部尚書);小宗伯為其佐(禮部侍郎);在唐尤指負責選士的「知貢舉」。成季布之千金,《史記·季布傳》(《史記》卷一百)「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行臺,又稱「行尚書臺」。是魏晉時在地方代朝廷行尚書省事的機構,至唐初已廢,此用以代指節度使官署。
以上「不獲恭拜行臺」之言,說明上啟當時封敖猶在節度使外任。封自大中四年至大中八年(850-854)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引《通鑑》卷二四九「大中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及《新唐書封敖傳》(卷一七七)「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推定封在大中六年二月之後稱封尚書。但封遠在外任,應知溫在京日久,京城賢達尚且無奈。自己鞭長莫及;所以恐未及為溫寫信求援也。
後來大中九年沈詢知貢舉,溫又應了考。而且還因做槍手因此出了名。見後。加上大中四年裴休知貢舉時那次應考(?)。有文本為證的溫之應考次數,似乎最多兩次。
(三)大中之末,終得一第
以為溫「終身未登第」,是受許多負面記載影響所致。事實上,經過多年種種努力,溫在大中九年「攪擾場屋」後,是登第了的。試看以下《東觀奏記》卷三(大中十二年)的記載:「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豈以文學為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東觀奏記》所引制文,以及後面作者評論「竟不中第」及「至是,謫為九品吏」云云,多有問題,後文將逐一辯證。茲先證明溫實際上是中第了的。《投憲丞啟》就是最重要的證據。
溫中第的證據之一是《唐摭言》卷二有「為等後久方及第」的記載,該條下「溫岐濫竄於白衣」的文字正說明溫經過「濫竄於白衣」後,畢竟最終算作及第了,故其名被記在「為等第後久方及第」條下;只是其記事方式易被人忽視而已。溫之「等第」而「罷舉」已是特例,當然也有特殊原因。溫在大中十三年實授縣尉之職務,則是跨過一般的「及第」成為前進士階段,由鄉貢進士(雖然是機器特別的等第獲得者)直接釋褐而「沾祿賜」,也就是「鳳凰詔下雖沾命」之「沾命」。這等於承認他有了前進士的資格,所以他才能釋褐被授官。當然溫從開成四年(839)的一介「等第」而「罷舉」(不能參加和通過禮部試)的鄉貢進士「濫竄於白衣」多年,直到大中十三年(?)最後及第而授隨縣尉,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案例確實特殊。其特殊性首先在於,他長期的潦倒不是以前進士的資格等待通過吏部釋褐試,而竟是以特殊鄉貢進士的資格在「濫竄」中等待和爭取有前進士的資格,從而釋褐、授官,而他最終跳過前進士直接被授官是兩步併作一步走了的。無論如何特殊,這仍是及第而授官之例。溫中第的證據之二見《唐摭言》卷十,「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條,該條先分別列舉十九位詩人的傳記材料,他們依次是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溫庭皓、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沈佩、顧蒙、羅鄴、方干等,然後說:「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遍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皆沾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韋莊同情中晚唐以降那些掙扎一生而被埋沒,連一第也未能得到的詩人文士,要求末代皇帝追贈他們及第。值得注意的是,韋莊所列十九人中有溫庭筠的胞弟溫庭皓,並且特別說明曰「溫庭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卻沒有溫庭筠。可見《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870-940)相信溫是如他所記載的「為等第久方及第」了的,當然就不在韋莊的人名表中。至宋代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三筆》,記載至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沾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溫庭筠……」云云,比以上《唐摭言》所記,少了孟郊、顧邵孫、沈佩、顧蒙、李甘、溫庭皓六人,而多了溫庭筠一人。接「俱無顯遇」以下,較《唐摭言》文字略有異同。《全唐文》卷八八九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大抵錄《容齋隨筆》。竊以王定保生當韋莊上書之時,又專敘科舉,應比宋代洪邁廣博而未免失考之書更為可信。溫中進士的證據之三是溫《上憲丞啟》自敘「遂竊科名,才沾祿賜」。他自己都說自己「竊科名」而「沾祿賜」了,我們還不承認麼?更有甚者,還有人因這句話竟然不承認《上憲丞啟》是溫庭筠之作了。
又《唐語林》卷二「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潯、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系,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淘、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此表與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大部分不同,溫庭筠亦在表中。未能辨其正誤,且存此備參。
(四)為人假手,詩中有謎
溫庭筠高才而多年不第,大概形成一種心理上的反彈:他索性為人捉刀,而且是「每歲(誇張!)舉場多為舉人假手」,以表達對考場不公的抗議。這是一種帶點抗議性質的惡作劇,作者在其中似乎自得其樂,這種行為至大中九年沈詢知貢舉時達到高潮。據說「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簾視尤謹」云云,然溫私下已經救八人。不用說進士科,就算以宏詞科的題目為人代筆,也能使被代者立中高第,簡直是文章聖手,也是作弊高手,尤其作弊之事,頗帶點傳奇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本人偏多少年厄於區區進士一第。這真有點無奈啊。下面提一個有點奇怪的問題:溫考場作弊,或者「攪擾場屋」的行為會不會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呢?這本不是多麼光彩的事,即使有所作,大概也是比較曖昧隱晦,令人不容易直達結論吧?我們研究以下頗有嫌疑的詩,看看能否下結論。
孔雀眠高樹,櫻桃拂短檐。畫明金冉冉,箏語玉纖纖。細雨無妨燭,輕寒不隔簾。欲將紅錦段,因夢寄江淹。
本詩見《才調集》卷二、《文苑英華》卷二一六《人事三·宴集》題作《夜宴》、《溫飛卿集》卷七。本詩內容,與「夜宴」無關。主題甚為隱晦,是一種無題詩,題為《偶題》,顯然更恰當;是一種無題詩,則其表達的實質內容總是有點曖昧的。
為解此詩,我們先從尾聯的典故說起。江淹才盡之典見鍾嶸《詩品》「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之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郎才盡。」又《南史·江淹傳》(卷一一四)說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下接與《詩品》相同故事,結語略異:「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溫引用這個典故,其意當然不在辨別江郎才盡的歷史真偽,而在藉典故本身表達一個願望。為什麼要寄紅錦段給江淹呢?按照原典含義,江淹夢中失去了別人舊日送他的那匹錦段,從此就毫無文采和清詞麗句了;現在作者則是想要寄給「江淹」鮮紅的錦段,顯然是要增加他的文采,幫助缺乏文采的「江淹」們把文章寫好。這種願望是不是意味著(考場)作弊「救人」呢?果如此,按溫經常用的篇終奏雅手法,詩中別處似應另設玄機,與之呼應,表達考場救人的完全意思。我們再往回看頸聯:窗外霏霏的細雨,妨礙不了室內的蠟燭之明;而薄薄的竹簾,隔不住簾外的輕寒。這好像是「簾內人」或者考生的感受。尤其有「燭」有「簾」,頗使人聯想到唐代的考場。《唐摭言》(卷十三)「溫庭筠灯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溫八吟。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其中「燭」字容易被溫用作諧音雙關,如「井底點燈深燭伊」(《新添聲楊柳枝詞二首之二》,《全集》卷九)、「娟娟照棋燭」(《湘宮人歌》,《全集》卷一),都是諧「囑咐」之「囑」。我們由這個啟示把頸聯前句寫成「細語無妨囑」,而後句則變為「輕函不隔簾」,意思就是不妨輕聲細語告訴所救舉子、所謂「江淹」們有關問題妙答,而徒然擺設的隔開考生的竹簾也擋不住小小紙片(輕函)的傳遞。這是不是溫庭筠作弊的一個證據呢?不用諧音解釋,這無題詩如何解釋呢?
溫相當擅長用諧音雙關。這裡我們面對的很可能是又一個例子。也許有人會問:就算你亂蒙得有點好像真的,那為什麼頸聯用了諧音雙關而頷聯不用呢?這種諧音雙關,屬於高難度的文字技巧,有一足矣,四聯中兩聯用諧音雙關太難了。不管怎樣講,我們至少得把全詩講通。
首聯以孔雀自比,它安眠高樹,對誘惑眾鳥的拂檐之櫻桃,表達了一種超然漠然的態度。前引溫《洞戶二十二韻》(《全集》卷六)有「書帖得來禽」句,曾注引唐李綽《尚書故實》王右軍書帖中有《與蜀郡太守書》「求(青李)、櫻桃、來禽、日給藤子。皆囊盛為佳」。注「言味好來眾禽也。俗作林檎」。櫻桃當然如來禽一樣以其「味好來眾禽」,它就在那「短檐」觸手可及處。又「短檐」之造語,溫頗喜愛;《百韻》詩有「短檐(喧語燕)」句,其中「短檐」比喻擁擠狹窄的官場;在此處,它比喻考場也是順手拈來、很自然的。
頷聯描寫,有聲有色。分別寫賞畫和聽彈箏,似皆考場環境中物。前句,使畫面明亮者,只是冉冉泥金,暗諷那畫面並非真正光鮮而徒然炫麗。後句,彈出婉轉「箏(諍)」語者,纖纖玉指而已;這也好像說朝中雖有美議,其聲音卻微不足道、不過裝裝樣子。所以這兩句其實可勉強解為批評當時科舉,雖標榜公平,卻徒有閃亮的外表,而代表公義的聲音是非常微弱的。這一聯之切題解釋最難。也許它只是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令讀者就無法追究了。
我們的結論是,《偶題》詩可能是溫對自己考場作弊行為的一種隱秘記錄。也許流傳過程中有所漫漶,更難辨認了。今捕風捉影,如解詩謎,深望能就正於通者。
(五)攪擾場屋,溫獨無罪
《東觀奏記》卷下載載杜審權對溫庭筠「攪擾場屋」案相關人員的處理。「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紳)(《東觀奏記》作者裴庭裕之父)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覆,而臨事或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並分等符,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技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按即杜審權,《舊傳》卒,贈太師,諡曰德)之詞也。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郎中周敬復罰二月俸,監察御史馮顓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拔兩科。其年(大中八年),爭名者眾,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岩、薛欣、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憙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選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溫庭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宏詞趙秬,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遂逐之,盡覆去。初,日官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這裡記載了溫庭筠「攪擾場屋」的故事,根據現有確實記載,其事集中發生在大中八、九年。因為大中八年主試宏詞、拔萃二科的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由於不小心,把題目泄露了。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熹之子)託溫庭筠為他作文,而高中宏詞科之選(只錄取三人),沒考中者就大鬧得連皇帝都知道了,也牽涉到了令狐綯。事情的結果,一是有關考官都被貶黜,唐技貶虔州刺史、裴紳貶申州刺史、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周敬復罰二月俸、馮顓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二是「三科(進士、宏詞、拔萃)盡覆」,「考院所送博學宏詞科趙秬等十人,並宜覆落」,考取的都不算了。而且作者記錄,這種結果都是天意,「日官之言」「方驗」而已。
而杜審權作為貶制的起草者,和整個事件的見證人和參與者,應該是處理這個考場風波的官方代理人之一。「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 (沈詢知貢舉的下一年),權知禮部貢舉」(《舊傳》卷卷一七七)。他掌握的權力,他任中書舍人的時間、知貢舉的時間,他對事情的處理,都表明他正是《上杜舍人啟》的啟主(見下)。從該啟看,他對溫的詩賦之才頗為賞識;而溫則特別介紹和強調了自己有關史才史識的「甄藻之規」和「顯微之趣」,希杜舍人推薦自己進史館,任修撰,正好乘著史館改變編制的時機。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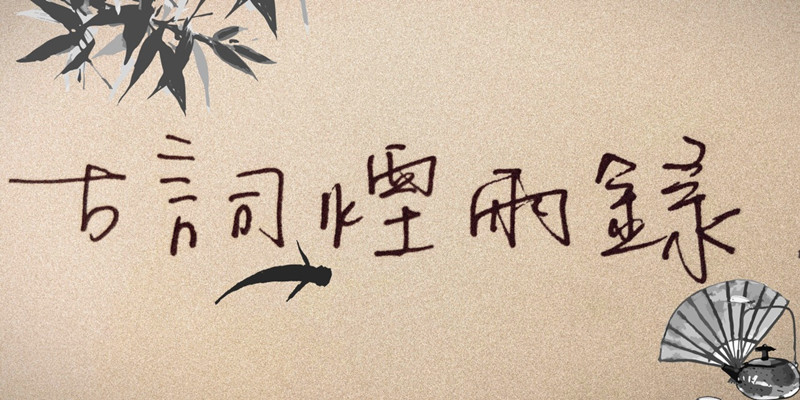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