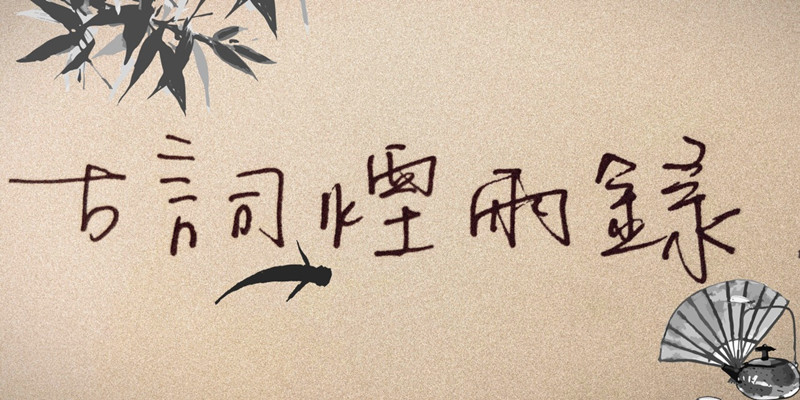我们大概有两年多没见面了。老人还是一身清雅的蓝色蜡染中式棉袄,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健谈、记忆力超强。
老人送我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青者忆》——牛皮纸色的封面,书名是著名诗人辛笛苍劲有力的毛笔题字,暗红色腰封上印着乐府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如此典雅朴素,又意味深长的封面,令我十分喜爱。不由得想起近日光顾书店时那些博人眼球的封面,个个竭尽炫耀之能事,常常是作者仪态万方的大照片统领封面,宛如时装杂志或八卦新闻,让我大倒胃口,只想远离。
截然不同的两种封面,是否折射出了杨苡先生那代人和今人的不同价值观?“出镜率”“点击率”“粉丝”“颜值”等日新月异的词汇不断撩拨着人们肤浅的追求,催促着人们追逐的脚步。杨先生那代人的优雅与深沉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优雅。它来自于文学的熏陶、知识的滋养、理想的激励以及那个社会与家庭的教养;那种优雅永远不屑点击率、粉丝圈等当代“价值”;它不经意、不刻意,自然而然,日月同光。
于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断代,继而又被改革开放的列车迅速带进利欲滔滔的时代洪流,由于缺乏文化根基而在激流中摇摇晃晃,甚至坠入欲望的深渊——他们那一代的优雅与深沉,学识与修养,已属于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年代。
《青青者忆》,顾名思义,是一本回忆往事的书。作者回忆了一个年轻读者与一位大家敬仰的著名作家之间通信的往事及两人持续了近七十年的友谊。年轻读者是十七岁的少女杨静如(杨苡原名);著名作家是以《家》《爱情三部曲》等作品在1930年代蜚声文坛,成为众多青年人偶像的巴金。
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杨静如,常常受困于莫名的惆怅、迷茫和对大家族清规戒律反叛的冲动;十六岁时因为被家中禁止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更加苦闷。她从巴金的《家》中找到了希望、方向和向往自由、追求独立的决心。十七岁时开始给巴金写信,不仅倾吐自己的苦闷,也从一个长者、智者身上寻求理解与指引。
于是,一个小读者与名作家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它传递着爱与理解,信念与支持。
它在最黑暗的长夜、最严酷的寒冬依然释放着希望的光芒和人性的温暖。
它“延续至今永不熄灭”。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且不论这样的一种友谊——它的开始,它的发展,它的日久弥坚——在当今是否可能;仅以杨苡先生的写作风格——真挚、真诚、真切,在当今多如牛毛的出版物中已是凤毛麟角;她淳朴的语言,娓娓道来的往事,一次又一次地触动着我。比如,他们的通信“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不掺杂任何杂念”;他们“绝无顾忌,也不必设防”;他们坚持说真话,宁可沉默也绝不说假话;它使杨先生从年轻到年老都能“任凭我的笔流出我的欢乐和哀思”——“这个习惯是巴金先生给我的” 。这些貌似平凡的事情在当今社会已经实属难得;说真话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说假话却成了许多人的第二天性;“顾忌”“设防”在自媒体时代的人际交往中已经必不可少。
“我们年轻时喜欢把巴金称为心灵医生,”杨先生写道;“他能医治心灵上的创伤”。
这就是文学的神奇!
这是作家与读者的心灵碰撞所产生的能量;二者的互动成就了文学的伟大与奇妙。我不由得想起了重商轻文的社会潮流,也想起了陈乐民先生的一句深得我心的话:“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
作者在书中追忆了“喜欢做梦的绿色年华”、盼望“天亮”的难捱岁月,也有不堪回首的“红色恐怖中耗尽了我们金色的哀乐中年,我们原本在事业上可以丰收的收获季节到后来却颗粒无收”。
我的心头一紧,对“十年浩劫”突然有了新的视角。
我自己在人生成长的最重要时期、性格塑造的关键年代,最应该如饥似渴地读书、海绵吸水般汲取的年华中被洗脑、被愚昧、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却浑然不知;还以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辈去解放;还以为我们向其早请示、晚汇报的伟大领袖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神;还以为半夜三更走上街头加入庆祝伟大领袖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欢呼雀跃是无比幸福的事;还以为为了某个主义抛头颅、洒热血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从愚昧中猛醒之后,时不我待的紧迫、对荒废的青春铭心刻骨的痛惜、对错过的人生路无法释怀的遗憾都在心头留下慢性的隐痛:比如看到上小学的女儿读代达罗斯的神话故事,意识到我竟对代达罗斯一无所知;比如读到杨宪益先生幼时学习作诗,辨平仄,对对子,“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却想起自己只会高唱火药味十足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比如刚读完一年级的女儿就在《芝加哥论坛报》暑期读书栏目发表了《皮皮长袜子》的书评,而我从小学起就 “拿起笔做刀枪”,批刘、邓、陶,批“三家村”,直至高中还在批林、批孔、批宋江…… 新生活时时处处都会针刺般地提醒着我在愚昧、无知、狂热中耗尽的青春年华,使我常常感慨我们是最不幸的一代,直到我读到杨先生的文字——“原本在事业上可以丰收的收获季节到后来却颗粒无收!”——我才恍然明白了每个人的十年, 每个人生阶段的十年,都是重要的十年,珍贵的十年,无法取代的十年!
巴金先生也同样在本该丰收的金秋岁月“颗粒无收”,还受尽屈辱,甚至失去爱妻。作者记录了沈从文先生感叹“开朗天真”的萧珊(巴金夫人)竟过早地抑郁而终,痛心地说道:“死了这么多人,这笔账怎么算?”
字字句句今天仍然令人锥心似的痛,因为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直面“十年浩劫”,遑论清算。巴金劫后余生后痛定思痛,不断追思、反省、忏悔,写下了几十万字的《随想录》;他大声呼吁“讲真话”,“建‘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
然而,“‘文革’博物馆在哪里?”作者在书中一再追问。
“我现在只能说…… 它矗立在巴金老人的心里,在他的亲朋好友心里,在他的读者们心里,在所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受难者们的心里!” 作者铿锵有力的词语,正是建造这座博物馆的砖瓦。
“历史终归是历史,它不像日历、月历或年历,想撕掉就撕掉,而岁月留下的历史踪迹却还能在记忆中永存!”
我们只能以个人记忆抗争集体失忆。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忘却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杨苡先生在书中一再引用她和巴金经常用来相互勉励的赫尔岑的名言: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
我多么希望看到更多坚强的人在祖国大地上站起来,为“文革博物馆”添砖加瓦!
这是一本100多页的薄书,却沉甸甸地承载了厚重的记忆与历史。
杨苡先生在书的扉页工工整整地为我题了字;略有所思之后,又用英文写下:Remembrance is the golden chain that links our hearts together(回忆是一条金链,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确信,记忆的金链将永远把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正如记忆的金链在巴金和杨苡之间永恒地连接了两颗心——爱永不止息!
2015/5/25
Memorial Day
Mission Vie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