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蒙飛卿,末路傳奇
(一)鳴冤文楚,惺惺相惜
《百韻》詩「時輩推良友,家聲繼令圖」,非虛言也。大約比《投憲丞啟》略早幾個月,溫有《為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啟》(以下簡稱《為段》),是他本人憂患終老之時,幫助落拓漂泊的忠臣良將段文楚而寫。段文楚是唐德宗時罵叛賊朱泚而死的名臣段秀實之後,溫幫助他可謂惺惺相惜。溫這篇文章在流傳印刷過程中,可能因版面毀壞而經重新排列,至有闕文、尤其文字顛倒錯亂的情況,謹先作整理,為溫庭筠之文,也為段文楚之人,以除疑慮,以杜讒孽。
某聞欒氏垂恩,延於十世;屈生罹譴,不過三年。雖行一切之科,宜聽九刑之訴。某謬因門廕,獲忝朝私。雖位以恩遷,而官由政舉。累經重事,皆立微勞。頃年初忝邕南,頗常釐弊,事皆條奏,不敢曠官。水蘗自居,膏腴不染。南蠻俶擾,邊徼先聞。始事詳觀,飛章備述。黃伯選根基深固,溪洞酋豪,准詔懷來,署之軍職。李蒙妄因非罪,忽使誅鋤。
(以上第一段,除末二句寫在任時對酋豪黃伯選懷柔,而其後任李蒙妄造罪名殺黃,可能因有闕文,略顯突兀不接外,其他語序無問題)。
1某離任之初,濫稱遺愛,伍營校隊,千里農商;叫譟盈途,牽留截鐙。2爰從初任,以至罷還,不戮一夫,聞於眾聽。3其後既經焚蕩,又遣統臨。4糠籺不充,菅蓬自覆。5曾無祿賜,惟抱憂危。6至無尺絹貫緍,以為歸費。7及掌罪狀,煥在絲綸。8以為徒忝官常,曾無制置。9且經營甫爾,物力未周。10拜疏將行,替人俄至。11仰恩波而不浹,駐官局以何由。12懦怯請兵,才非將帥。
(以上第二段。今將《文苑英華》卷六六六所載原文12個句子之順序按阿拉伯數字從1到12排號。除前三句外,其他語序都有問題。尤其末二句11和12,接不上)。
與3「其後既經焚蕩,又遣統臨」下相接,應是5「曾無祿賜,惟抱憂危」和9「且經營甫爾,物力未周」。5和9二句構成遞進關係,即自己再任邕管後,面臨的艱難形勢:不但朝廷對己毫無祿賜,自己則以國家安危為唯一關切;而且剛剛開始經營,也缺乏財力物力。以下再接7「及?罪狀,煥在絲綸」,說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自己蒙朝廷授以貶詔,罪狀都在詔文上明白展示(或以此句承上謂李蒙,李蒙其時已死;不會在此又提)。而所謂「罪狀」,是8和12。8認為段徒然占據官位,竟然毫無建樹;12說他為人怯懦,不敢向上求救兵,不是將帥之才。接到貶詔,下文當然是如10所言「拜疏將行,替人俄至」(要辭任告別,而接替官員很快就到了)。所以11感嘆說,「仰恩波而不浹,駐官局以何由?」謂仰望皇恩,恩波不能遍及,還有什麼理由在邕管官邸住下去呢?(只能離開了)。但自己再任邕管以來,如4所言「糠籺不充,菅蓬自覆」,連糠麩粗糧都吃不飽,且只有些菅蓬乾草作床作被。所以如6所言,以致於連一尺絹一貫錢的歸京路費都湊不出來。
因此,1,2,3之後的正確順序是如下:5,9,7,8,12,10,11,4,6:
5曾無祿賜,惟抱憂危。9且經營甫爾,物力未周。7及掌罪狀,煥在絲綸。8以為徒忝官常,曾無制置。12懦怯請兵,才非將帥。10拜疏將行,替人俄至。11仰恩波而不浹,駐官局以何由。4糠籺不充,菅蓬自覆。6至無尺絹貫婚,以為歸費。
以下第三段,除「業開伊呂,朗鏡臨人;運值堯湯,平衡宰物」依一般對仗習慣,似當作「業開伊呂,運值堯湯;朗鏡臨人,平衡宰物」外,亦無問題。
今者九州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鋒,已至城下。則以三千土著,眾寡如何。兩任經年,曾無掩襲。雖有烟塵之候,不踰朝貢之州。無勞北軍,已自抽退。伏念至德建中之際,長蛇犬豕之間,願報國恩,盡縻家族。松楸未拱,帶礪猶存。顧慙無用之軀,旋漏不私之貸。僑居乞食,蓬轉萍飄。生作窮人,死為醜鬼。伏惟相公,業開伊呂,朗鏡臨人;運值堯湯,平衡宰物。伏乞錄其勳舊,假以生成。免令家廟豐碑,尚垂蟲篆。私庭陋巷,長設雀羅。戀闕傷魂,臨途結欷。無任懇廹。
(二)有功之臣,僑居乞食
段大夫,當指段文楚,根據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七,段文楚第一次任邕管經略使始在大中九年;終在「(大中十二年)二月,「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為昭武校尉、右金吾將軍」(《舊唐書》卷十八下)。這期間段文楚仕途尚順。當他離開邕管,《為段》文說,「某離任之初,濫稱遺愛,伍營校隊,千里農商;呌譟盈途,牽留截鐙。」段第二次任邕管在咸通二年七月至咸通三年二月左遷之間。
咸通二年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才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參上:在大中十二年二月),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才十日,無兵以御之,城陷,(繼任李)弘源與監軍脫身奔蠻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
「文楚,秀實之孫也」。……三年,二月,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圮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焉。』《新傳》『文楚數改條約,眾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因《補國史》
『改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以上兩段引文均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及注引《通鑒考異》)。
可見,《通鑒考異》認為,段文楚因「變更舊制」而被貶的說法,是「相承致誤也」。其實,所謂段文楚「變更舊制」,不是他再至邕州做的事,更不是什麼「數改條約」,而指他初任邕管時「自募土軍」;其事不但不是罪狀,而且是改革弊政有功國家之舉。「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此前的「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的成例,就是《為段》所言「頃年初忝邕南,頗常釐弊」。自募土軍的作用和結果,後文「今者九州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鋒,已至城下」的形勢下也提到:「則以三千土著,眾寡如何。兩任經年,曾無掩襲。雖有烟塵之候,不踰朝貢之州。無勞北軍,已自抽退。」而所謂「所募才得五百許人」,是段文楚第一次任邕管之末,當時「所募才得五百許人」,來不及招滿,段就入京了。
段文楚升任入京後,其後任經略使李蒙不但殺了酋豪黃伯選(「妄因非罪,忽使誅鋤」,羅織罪殺之;段文楚對黃「准詔懷來,署之軍職」);而且把招兵缺額多出的錢財貪為己有,停止調遣三州之兵、只用所募的不足原數二三成的兵員守地。這既破壞了段文楚對南詔的懷柔政策,又很大程度上減弱了國防力量,致使「蠻人乘虛入寇」。李蒙死後,其繼任經略使李弘源遇敵脫身敗逃,所以朝廷又一次以段文楚為邕管經略使。對段到任敘職之後的情狀,《為段》說,「曾無祿賜,惟抱憂危。且經營甫爾,物力未周」(我何嘗沾一點祿賜,仍以社稷安危為唯一關切。因剛到任經營才開始,物力不足)。但是,段文楚馬上就因所謂「變更舊制」的莫名其妙的罪名而遭黜貶,上引《補國史》云「朝廷責其更改舊制」,《實錄》亦云「頗更舊制」,《新傳》乃云「文楚數改條約」。總之,罪名就這樣定下來。《為段》說,「及蒙罪狀,煥在絲綸。以為徒忝官常,曾無制置。懦怯請兵,才非將帥」。這幾句話說,蒙朝廷加我罪狀,都明寫在詔書上。第一個罪狀是徒然為官,竟無創造性的建制,這是無中生有的罪名;事實正與此相反;段自募土軍,對南蠻的懷柔和睦鄰,都說明段是難得的儒將。第二個罪狀是怯懦於向朝廷求救兵,不是將帥之才,更可謂莫須有;邕管緊急而把段召回,時間不久卻又加以貶謫,都說明朝廷用人首鼠兩端,賞罰不到位,而使讒孽橫行,致使忠良被害。
《為段》以下所說「今者九州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鋒,已至城下」云云,發生在「咸通五年(864),三月,康承訓(新任邕管經略使)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通鑒》卷二百五十)所以,溫的《為段》啟當寫於咸通五年四月之後。當時康承訓連連落敗,不聽諸將之計,後來借「天平小校」夜燒蠻營之計,而僥幸得勝。
「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朝廷「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余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同上)。可見有「破蠻之功」的康承訓是個什麼角色。而直到此時,段文楚還處在「顧慙無用之軀,旋漏不私之貸。僑居乞食,蓬轉萍飄」的狀態。他慚愧自己不能報國,同時還是得不到皇帝毫無私心的寬恕。這時離他「左遷」已兩年多了,還因沒有回京路費,到處漂泊、客居討飯。
我們不知段文楚何時回京。細讀《段文楚墓志銘》(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咸通三年(862)段「左遷威衛將軍分司」之後,主要的仕履是「改左衛大將軍,轉天德防御使,改大同軍使(876~878)」而於任內被叛將沙陀人李克用所害。「乾符五年(878)二月七日,遇害於雲州」(被叛軍頭領殺害)。段的「僑居乞食,蓬轉萍飄」的歲月多虧溫庭筠記載下來。段文楚自864至876年十二年中,《墓志銘》只記「改左衛大將軍,轉天德防御使」,前者是虛銜,後者也查不到有關記載。通過溫的文筆,我們看到唐代忠臣世家段文楚,在邕管時就已懷冤抱屈。已有一段流離失所日子。我們欽佩他的高風亮節和忍辱負重,而嘆惜天不助忠而亡唐也。這時溫尚在隨縣尉之位,離去世只有一年多一點了。猶如此挺身而出,為忠良執言。可嘆也夫。
(三)憲長登庸,「徐寧」遷次
《投憲丞啟》(見《文苑英華》卷六六二啟十二投知五及《全唐文》卷七八六)啟主是誰?劉學鍇《溫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對本啟的說明認為「疑點頗多」,而疑此啟非溫作。本文認為,劉的疑點都可解釋,而啟主可定為徐商。今先簡釋如下: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或一言便許忘年。奇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運租船上,便獲甄才;避雨林中,俄聞託契。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親者也。某洛水諸生,甘陵下黨。曾遊太學,不識承宮;偶到離庭,始逢種暠。懸蘆照字,編葦為資。遂竊科名,纔沾祿賜。常恐澗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風末微姿,未卜棲身之所。
大意:我聞古來「窮士」求知遇、「孤臣」得薦舉,可能三年不能與對方交談,可能一句話就成了忘年之交。機運的有無,差別多麼大啊。至於袁宏運租,就被謝尚薦舉;茅容避雨,就成郭林宗深交。這又是無因由而自來相逢,不須紹介而互相親近了。當年我曾為洛陽太學生,年少敬仰永貞黨人;只是在學時,無緣得識承宮一樣的閣下;而偶至邊庭,才如種暠一樣有了被知遇的機會。從此加倍發憤、苦讀經書,終於中第授官。但我總自憂像澗中之石,畢竟得不到有利地勢;為望族之末裔而難求安身立命之位。
解釋:「三歲」句,《世說新語·文學》「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一言」句,未詳確典。可參《晉書·趙至傳》:趙至年十四,詣洛陽遇嵇康而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二人遂成(忘年之)交。以上二例,正是下文「奇偶之間,彼何相遠」的例證。「運租」「避雨」,用袁宏在江上自詠詩為謝尚所賞(見《晉書》卷九二)及「茅容避雨樹下」,為郭林宗所識事(《後漢書》卷六八)。洛水諸生,本東漢洛陽太學生;故「太學」應指唐代洛陽太學。甘陵下黨,據《後漢書·章帝八王傳》(卷五五),劉慶本人雖被廢,其子終繼位,而尊其陵寢為甘陵。這與唐順宗即位不久便被廢,而由其子李純(憲宗)即位甚似。劉禹錫《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全唐詩》卷三百六十)「甘陵舊黨凋零盡」句即以「甘陵舊黨」謂永貞革新的「二王」及「八司馬」(包括他本人)。溫年少無緣參加甘陵舊黨,而心嚮往之,受一些社會聯繫的影響,自稱「甘陵下黨」,本啟的憲丞恐亦同。承宮,《後漢書》(卷二七)有傳,少孤勤學,有「拾薪苦學」、終成大儒的故事;入仕後「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離庭,當指離京城相當距離的節度使駐所;種暠,《後漢書》(卷五六)有傳,少有濟世志,受到王諶知遇而被薦拔,後多歷要職。二句交錯為文,以「承宮」比喻對方,而以「種暠」自喻。「懸蘆」句,謂懸蘆火照明讀書,誇飾貧困勤學。編葦,細品之,不足為好學之典,疑或作「絕韋」;用《史記·孔子世家》(卷四七)「讀《易》,韋編三絕」事,自謂苦學。風末,比喻強大事物之末尾,喻祖業衰微的自己,故接「微姿」。
侍郎議合機彖,望逼臺衡。每敘群才,常推直道。昨日攝齊丘里,撰刺膺門。伏蒙清誨垂私,溫言假煦。內惟孤賤,急被輝華。覺短羽之陵飆,似窮鱗之得水。今者方祗下邑,又隔嚴扃。誰謂避秦,翻同去魯。佇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徐寧,因縣遼而遷次。下情無任。
大意:侍郎您議論相合於天機神卦,聲望迫近宰臣首輔。你每每品敘當今諸公之才,經常推崇正直之道。日前我心懷敬畏,登門求見,承蒙您用感人的教誨予我私愛和慰勉,用熱誠的語言給我溫暖和許諾。我內心越是想到自己孤賤潦倒,越是急於得到您的恩寵薦拔。在您面前,我感覺到短小的翅膀也能乘風飛翔,如涸轍之鮒得到了救命之水。我現在正守職窮縣,而君門閉塞;誰說是什麼桃源人逃避暴秦,簡直如孔夫子不忍離開魯國了。我久久期盼著您像漢朝的朱博,由御史大夫拜相,那我便能如晉朝的徐寧由縣令升遷入朝。區區此情,難以盡表。
侍郎,當為本文的憲丞入相之前不久以本官御史大夫兼任之職。機,事情變化的深微因果;彖,本謂周《易》概括卦辭之義的彖辭;機彖,猶言玄機神卦,譽見識高卓。臺衡,三臺星和玉衡星的合稱,都在紫微星(帝座)之前,舊用喻宰輔重臣。攝齊,據《論語·鄉黨》「攝齊升堂」朱熹注:「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齊(音茲),衣下縫。丘里、膺門,借孔丘居里、李膺門戶,尊指憲丞之宅。祗,祗候,恭敬侍候。下邑,下縣,即指隨縣,本為上縣;稱下者,示不滿與謙虛。嚴扃,崇嚴的門庭,此謂朝廷。避秦,陶潛《桃花源記》「自言先世為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去魯,《孟子盡心下》「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佇見」句,《漢書·朱博傳》(卷八三)「博以御史(大夫)為丞相」。徐寧,事見《晉書·桓彝傳》(卷四四)等,為輿縣令;桓彝遇賞之;薦之於庾亮,為吏部郎。
(四)侍郎援手,終上殿陛
全文既釋,我們就可以解釋劉學鍇在《溫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對於《投憲丞啟》的幾個疑點了。疑點之一,以為溫「終身未登第」,是一種誤會。如前文已証,溫終得第也。解釋清楚了疑點一,也就解決了疑點之三,就知道啟中語「方祇下邑」當然「可解為大中十三年貶隨州隨縣尉之事」之已為官身,而這種經歷,正是溫已「竊科名」中第的結果,中第之後自然釋褐而「沾祿賜」的表現。紀唐夫贈詩中「鳳凰詔下雖沾命」句,是指溫獲得中書舍人所撰一紙任命制文而已。
從文中「方祗下邑」及「願同晉室徐寧」二句知,投送本啟的時間在大中十三年貶尉隨縣之後。根據《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十四年(即咸通元年)詔微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而「(段成式)退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為從事,與成式甚相善」(《金華子》卷上)。這說明溫「謫尉隨縣」後一度留在(襄陽節度使)徐商幕下,可能掛著隨縣尉之職,隨州本是襄陽節度使的屬下。但這段交往只在大中十三年至咸通元年之間。而咸通元年之後,溫恐不得不赴任隨縣,但他也許有時帶縣尉銜「留長安中待除」(《唐才子傳》卷八)。《太平廣記》卷三五一所引《南楚新聞》的記載「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閒輦下」,可以為證。「佇見漢朝朱博」二句,表明溫掛銜隨縣期間,早就盼這位御史大夫登上相位,來使自己如晉朝的徐寧一樣,也遷升入朝。咸通七年溫去世前,除了徐商外,似乎沒有別人從御史大夫之位拜相,使溫「因縣僚而遷次」但我們斷定徐商就是本啟啟主憲丞,還有更重要的根據。
我們考慮溫投獻此啟時已在縣尉之職頗有時日、入為京官之前,進而尋找大中十三年為隨州隨縣尉至咸通六年入為京官期間,對溫頗為知遇而大加薦拔的人,就發現本啟啟主憲丞的有關的履歷,尤「既稱憲長,又稱侍郎」之似乎令人生疑的情況,與徐商若合符契。以下史料也是如此顯示的。《全唐文》卷七二四李騭《徐襄州碑》「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舊唐書》卷十九《懿宗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御史中丞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新唐書》卷九《懿宗紀》「(六年)六月,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咸通六年六月)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亦綜上記載為「徐商,(咸通六年)二月由大御遷兵侍同平章事。」徐商如何以御史大夫(從三品)而幾乎同時轉為兵部侍郎(從五品)、同平章事(同三品),確實有趣。其中轉兵侍為左遷、為平章事則為升調。但即使我們暫時找不出這樣任命的原因,卻至少可由此解決本文所謂「既稱憲長,又稱侍郎」的特殊問題。
以上引文中細節明顯無疑的共同點,是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而不記時間之先後。這一點值得充分注意。結合本啟的情況觀察,徐商應是在御史大夫任上,先兼職兵部侍郎,後來不久就入相的。所以「既稱憲長,又稱侍郎」應是可以解釋的,侍郎之稱無誤。而上啟時徐已以本官兼任兵部侍郎,故行文時完全可以就便簡稱之為侍郎。既領「憲長」之銜,又兼侍郎之職,而其後不久就入相(以致於史書莫能辨為兵侍與入相之先後),這種罕見仕履,既可用徐商的特別仕履證實,又可反過來證明本啟的啟主非徐商莫屬。而投送此啟的時間應在咸通五年秋冬。
其實徐商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而鎮襄陽時(自大中十年至大中十三年)直到咸通六年入相後,對溫庭筠是始終褒揚和支持的。《舊傳》「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為巡官」;又曰「徐商知政事,頗為言之」。《新傳》》有類似記載。
我們廓清了以上疑點,也就證明了本啟的啟主就是徐商。而從兩《唐書》溫本傳看,有更多旁證。徐商鎮襄陽時、尤其入相前後對溫褒揚舉薦,一直甚為用力;也就是說,溫授隨縣尉前後,徐商一直為其保護人。而從本啟看,在溫一生潦倒,幾乎絕望之際,徐對他「清誨垂私,溫言假煦」,表現了深摯友誼,使他在絕境中重燃起確定的希望而「覺短羽之陵飆,似窮鱗之得水」。另外,《全唐文》(卷七二四)李騭《徐襄州碑》敘商行實甚詳,其文德武治,尤「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戎狄侵叛,公時為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及受重藩,使絕塞,……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與啟文注引承宮之「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等皆合。
溫與徐商的交遊,見於溫集者,一是從《徐襄州碑》曰「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升朝為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入禁署」(即以殿中侍御史補禮部員外郎),可推開成五年冬寫《百韻》時,徐即詩題中所謂殿院徐侍御,而由《百韻》詩意推斷,溫開成二三年當與徐共有侍從莊恪太子之經歷,即皆曾任職左春坊司經局。
一是《碑》文曰「……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河中原名蒲州)移鎮於襄,十四年(大中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改元咸通)詔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茲六年矣」(此「六年」包含大中十四年本年以及咸通元年至五年)知徐商鎮襄自大中十年至大中十四年。兩《唐書》本傳皆言「署為巡官」在徐鎮襄時,當時溫庭筠、段成式、余知古、周繇等名彥雲集徐幕下,乃有(新唐書藝文志》所記之《漢上題襟集》也。鑒於徐商咸通元年內徵,溫為徐巡官而會諸彥,應始於大中十二年或更早。
二是清吳廷燮《唐方鎮年表》據《徐襄州碑》「授河中帥」,證徐鎮河中約在大中八年至十年春;溫《詩集》卷八《河中陪帥遊亭》,應係其時作,即本文所謂「偶到離庭」之時,約在大中八年。而從「遂竊科名,纔沾祿賜」之句接在「偶到離庭,始逢種暠」之後,適可證實,溫之「竊科名」當發生在大中十年以後。
三是《舊傳》「屬徐商知政事,頗為言之」及《新傳》溫本傳「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與啟中語「今者方在下邑,又隔嚴扃。誰謂避秦,翻同去魯。佇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同晉室徐寧,因縣僚而遷次」可謂因果相接。既然「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而咸通六年二月,徐商入相,可見本啟應投獻於咸通五年末。其後溫成為國子助教,真的「因縣僚而遷次」了。
四是啟云「某洛水諸生,甘陵下黨。曾遊太學,不識承宮;偶到離庭,適逢種暠」云云,說自己在太學就讀時,未曾結識「承宮」(對方),而到離庭一遊,正好讓對方與自己(所謂「種暠」)相逢,可証溫與徐商本東都洛陽太學之先後同學;而在邊關(即河中)相遇。尤其溫徐為洛陽太學同學之事,可以追到元和中。而徐商在河中雄鎮邊關、在襄陽惠澤一方,都不但切合「承宮」的典故,也確實說明他是晚唐時難得的有氣節和能力的好官,信乎其為溫平生至交。此亦溫庭筠平生不幸中之幸也。
徐商咸通六年二月入相之薦溫。溫努力一生,終得「對明庭」(「羡君雖不祿,猶得對明廷」,出《過孔北海墓二十韻》,《全集》卷六)而直接服務皇帝了。這是他家族的傳統,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咸通六年(865),溫已六十八歲,用他自己的話說「當年不自遣,晚得終何補」!(《寒食節日寄楚望二首》之一,《全集》卷九)。
(五)榜國子監,雄詞卓識
溫最終入為京官,擔任過什麼職務呢?國子助教(正五品),見《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万年縣下,引《京兆金石錄》有《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志》,「弟庭皓撰,咸通七年」。《唐摭言》(卷十)、《唐詩紀事》(卷六六)稱「溫飛卿任太學博士(正六品)主秋試」。以下的《榜國子監》,自稱「試官」,似是今存溫之最後文字。
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眾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榜出,以明無私。仍請申堂,並榜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榜。
此文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八,今存《永樂大典殘卷》亦載此文,其後接「胡賓王序:邵謁,韶州翁源縣人。……苦吟,繇是工古調。尋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榜(《唐才子傳》作「謁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已而釋褐,後赴官,不知所終。……今錄其詞,附之篇末。安定胡賓王序」。文中也提到邵謁「詞詠凄苦」。《唐詩紀事》(卷六七)「李濤長沙人也。……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牓於都堂。」但《唐才子傳》卷九:「庭筠仕終國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也可能是以「助教」主試,其後死。
由《唐摭言》(卷十)「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啟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辭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言溫之負冤,一是因為見妒於朝臣,二是因自己運氣不好。《唐才子傳》卷九有類似引文:「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去為山南節度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人李巨川草薦表……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相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孽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頷之。後遷至郎中,卒。有集文賦等傳於世。」
由以上這些資料看,溫咸通六年二月之後才調入為京官;咸通七年十月六日尚為國子監試官;咸通七年年底之前已經去世(《唐才子傳》云「流落而死」),而有其弟溫庭皓所撰《唐國子監助教溫庭筠墓志》傳世。可見溫的死是很突然的,不僅是流落而死,而且是流放(竄)而死。流放的原因,我們只能從《榜國子監》找了。溫榜示的詩篇。「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大致是說有膽識,有深度,語言尖銳,揭露深刻,不但繼承風雅,而且有所裨補於時政。其作者則都是「寒苦」士子,揭露時弊則恐甚於白居易當年的新樂府,而更疾惡如仇。溫「憫拔寒苦」,而且贊同他們對許多重大問題的揭露,並且出格地把有關詩篇公諸都堂,是他得罪之因。至於當時何人治他的罪,加了什麼罪名則無歷史記錄,不得而知,故不得詳論也。
(六)邵詩溫評,詞鋒警世
以下試略論幾首邵謁今存詩(見《全唐詩》卷六百五)。
先看《放歌行》「龜為秉靈亡,魚為弄珠死。心中自有賊,莫怨任公子。屈原若不賢,焉得沉湘水」。全詩似乎很冷峻,平行地羅列了不同類型的物 (當然皆關乎人)的不同死因,皆因心中之「賊」,即自身的敵人所致。屈原沉湘水而捐軀,則只為一個賢字,這個「賢」字,多少人立身的根本,也是自身之賊嗎?在那黑暗混亂、以不可阻擋的速度走向滅亡的末世,人們如龜之秉靈,會因其不同於眾的長處而死,如魚之弄珠(吐水泡),會為普通的謀生而死,也有因貪欲太大而死的,如任公子所釣大魚。最令人驚嘆痛惜的是,還有因賢而死的屈原。「賢」成為死因,看來「不賢」才是謀生的手段。作者無情地鞭撻了那個道德淪亡、民不聊生、完全沒有賢人生存空間的社會;出言之嚴厲,可謂驚心動魄。
再如《長安寒食》「春日照九衢,春風媚羅綺。萬騎出都門,擁在香塵里。莫辭弔枯骨,千載長如此。安知今日身,不是昔時鬼。但看平地遊,亦見摧輈死」。首四句寫春暖花開,連造物者都偏袒的遍身羅綺者,在千乘萬騎、香車寶馬簇擁中,出了都門,不知是為掃墓祭祖還是踏春尋樂。作者筆鋒一轉:不要推辭說什麼憑弔死人,自古都這樣(也要成為死人被活人憑弔)的。說不定你們就是以前的死鬼變的。我看你們今天在平地大道上奔馳,恐就會翻車死掉的。這樣的詩句,早就不溫柔敦厚了,毒意甚矣,充滿對高居社會上層者的詛咒,已非一般的仇富心理,而是殺富心理,可見當時社會矛盾之尖銳。所以後來高唱愛民論調的統治者及其幫閒文人,也不敢輕易引用。
此非專門論邵詩之文。故只再略舉成句:「流泉有枯時,窮賤無盡日」(《自嘆》);「天地莫施恩,施恩強者得」(《歲豐》);「他人如何歡,我意又何苦。所以問皇天,皇天竟無語」(《寒女行》);「在鳥終為鳳,為魚須化鯤。富貴豈長守,貧賤寧有根」(《送從弟長安下第南歸覲親》)。類似這樣的詩句,是發自社會底層的無望呼號,是豐年不霑天恩的深沉悲嘆,是仰問皇天而不得答的無奈沉痛,是對合理社會制度的茫然訴求。這樣的詩,不止晚唐統治者難容,後來諸朝宦達也不喜歡的。溫庭筠以榜示此等詩於都堂而得罪當塗,是十分自然的。
(七)在蒙飛卿,義山深意
今總結溫的一生主要經歷行實如下:
溫庭筠者,彥博六世孫。駙馬都尉溫西華之孫也。太原清源人。高祖肇基景命,太原溫氏卓建功勳而封侯拜爵。「高祖從容謂(彥博)曰『我起兵晉陽,為卿一門耳』。」自幼隨家卜居江南。尚見祖業餘廕也。元和中以廕入東都太學。少年歧嶷,師事八磚學士李程,而名高洛下。父某,失其名,時以忠直為宦者所害。溫羈孤牽軫,困頓輟學。既而羈齒侯門,懷鉛提槧,旁徵義故,遍訪山川。西窺塞垣,熟諳軍旅。南經蜀道,懷抱山河。卜居匡廬,開拓學問;遄遊京、淮,憂念民瘼。不唯以詩文精警名天下,亦以放任不羈傳宇中。與李商隱齊名,清詞麗句,皆一時之選,而各有千秋,親為弟兄也。每以嵇紹自喻,見其忠藎皇室之心、憎惡宦豎之情。是之為臥龍,非諸葛之臥龍,乃嵇康之臥龍也。大和末,甘露變起,所親鄉閭長輩宰相王涯被害。適溫有江淮之遊,青樓之中有所遇,將買名妓為妻,因携涯薦書,投刺舊交,謀職揚子鹽鐵院,望以自給,所求未果,而得有司饋贈。然揚州鹽鐵之利,多為宦者盤踞,乃加醜名而辱之。溫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公侯重臣頗有為溫執言者。時其師李程為吏部尚書,而莊恪太子方待賢輔。乃薦之於文宗,帝俞之,乃為宮臣,忠勤事幼主。位在司直,未暇實授。曉以綱常倫理、經史詩文。使與渤海王子詩箋往來,名傳域外。楊賢妃擅寵而譖死王德妃。文宗反其故常,乃信讒言而開延英議廢太子。宰輔重臣雪涕以諫,終使文宗回心。然宦者利楊妃之謀,乃於開成三年八月與共害死太子而囚禁文宗,欲報甘露之仇也。溫知其秘,而不能已於言,益為宦者所忌。嘗犯險,幾為所獲。中書舍人裴夷直仗義庇之。其時文宗為宦者囚拘,溫則暗處囚拘之列。急難之中,奔走京華,得益友、賢相之助,宰相裴度每憂儲君之事,命在彌留,猶鄭重囑託京兆有司,顧念忠臣之後。改名溫歧,字在蒙,以應京兆府試。名在等第,而慘遭罷舉,以改名事泄,宦者作梗故也。至開成五年初,宦者囚文宗而速其死,且矯其詔立武宗。時皇權易手,宮闈喋血。溫遐遁南國,自謂「觳觫齊牛,釁鐘未遠」,成南北司爭之犧牲也。及大中初,復試再登龍門,旋求為史官,皆不能果。溫心不平,志在直對明庭。宣宗好聽《菩薩蠻》,而丞相令狐綯假溫庭筠手為二十首而獻之,戒令勿泄,而劇言於人。不惟獻賦明志,蓋欲炫才市寵也。區區其心其志,雖不能得,亦可憫也。高才落寞,久而救人自樂。或言日救八人。又為宏詞拔萃者代筆,朝野為之喧噪。小宗伯莫之奈也。溫集中有捉刀詞,捕風捉影或可求旃。久居下僚,而忠心不變,屢敗屢戰。執政不得已,憫其以等第二十年濫竄,貶為隨縣尉,李程嘗為隨州太守故也。是之為中第也,不亦悲乎。昔日同窗友,早已出將入相,溫猶為九品小吏,白髮奔走,不能自已。時彥送溫之任,而紀唐夫詩尤壯其行。然其詩小有瑕疵,致使後人不能趨同,方城隨縣,千年誤說不已,徒然惑人。舊友徐商入相,其時南司之勢稍衰,乃薦為國子博士,轉國子助教;一為試官,便榜進士譏政刺時之篇於都堂,得罪執政,當即重貶急放而死。兩《唐書》本傳知其冤,而不能辨其所以冤也。
溫摯友李商隱有《有懷在蒙飛卿》(《全唐詩》卷五四一)詩曰:薄宦頻移疾,當年久索居。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城綠新陰遠,江清返照虛。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
詩題中之「在蒙」乃溫庭筠當年改名溫岐所用表字,如筆者昔文所證,李商隱將溫之原表字與改名後所用表字連在一起寫成「在蒙飛卿」,如「暗投的明珠、『不能奮飛』的鴻鵠,親密的戲謔中帶有多少摯友的同情」,也包含對溫正確評價的期望,使飛卿無復在蒙也。
詩中四聯言四事,而以「有懷在蒙飛卿」貫之。首聯言溫當年長期隱居,至今沉淪下僚,是在蒙也;頷聯言溫人瘦如尚書沈約,哀如開府庾信,則在蒙之飛卿也;頸聯言己與溫遠隔綠城新陰,而虛見清江返照;尾聯則盼得溫之筆墨,而待其書信之來,皆有懷飛卿也。全詩字面上緊扣有懷、在蒙、飛卿諸詞組的文字本義,兼關溫之才高命蹇與自己思慕之切;起承轉合之中,文心貫通,一氣流轉,誠為一人而發,而此人即『在蒙』之『飛卿』也」。其中「瘦極沈尚書」,典出《梁書·沈約傳》(卷十三》)(沈約)以書陳情於(徐)勉:「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李後主詞「沈腰潘鬢消磨」即用此事)。值得注意的是,首聯明說溫薄宦移疾,頷聯卻偏用其爵貴為開府的庾信之哀、其官高為尚書的沈約之瘦,來比飛卿之精神的哀傷和身體的摧殘,明顯是同情他大材小用,良玉委塵。而頷聯言溫當時所在,春城方綠,新陰甚遠;江上波清,返照成虛。這分明是遠方的江城,溫當時行跡所在。頗疑這就是溫大中所貶之地隨州隨縣。《東觀奏記》所言溫貶隨縣在大中十三年,似乎應早一二年,意者或在大中十二年李商隱卒前。再細抉其意,「新陰」之「陰」,諧「蔭」,皇廕也;新廕遠,即皇恩遙遠,貶地遙遠。
又「返照虛」易解,我們不願取最壞的理解,而只就皇恩而言,江上夕陽返照的最後光輝,是不是正可暗喻那徒有虛名的皇恩、即制貶隨縣尉呢?溫李往來篇什本不多,這樣理解只是一種猜測。若事實果如是,李商隱這首詩更可當作對溫庭筠到貶尉為止之人生的精準深刻之評價。
溫李交友,當始於當年曾同事令狐楚學藝。前文提及《上令狐相公啟》「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意為當對方如孔鯉一樣接受父訓、學詩學禮時,自己也在門下執弟子禮;把令狐相公之父令狐楚喻為孔子般廣收弟子的大儒。其時李商隱當然也在門下。《上宰相啟》二首之一又一次說「三千子之聲塵,曾參講席」,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溫李不但曾為同學,溫《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云「旅雁初來憶弟兄」,也表明他們兄弟般的情誼。這一對天才詩人,從他們在世之年就有如天上雙星,同光齊名。例如:《全唐文》(卷七九六)皮日休《松陵集序》「(咸通)十年,公出牧於吳,日休為郡從事。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為之最……」。這段話本是讚揚陸龜蒙的,其中提到溫李,大概是最早見於文字的「溫李齊名」論。又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下「庭筠……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較上引事,已過了數十年。《舊唐書·文苑傳下》「(李商隱)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新唐書·溫庭筠傳》中謂溫「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北夢瑣言》(卷四)「溫李齊名」:「溫庭雲,字飛卿,……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宰相彥博之裔。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唐才子傳》「側詞艷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
如今的溫庭筠,歷史的誤會尚未完全釐清,而對他的研究還遠非透徹。但時下一些研究者,似乎有重李輕溫的勢頭。他的好朋友李商隱「在蒙飛卿」之言,至今有效;溫之生平為人為文,尚需研究,尚求理解,尚待再發現,為使飛卿無復在蒙,解文史之糾結,發前人所未發,尚待通人抉發其全部文心隱秘也。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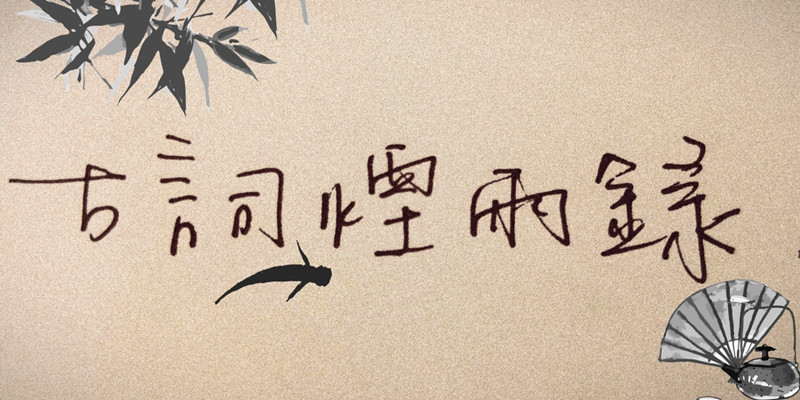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