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诸城那会儿,苏轼见境内百姓于田野道边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便知受了蝗灾,下车打问,当地官吏道:“蝗不为灾。”有的睁眼说瞎话:“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见过蝗虫漫天飞舞,起落时绿洲变赤地的景象,愤然道:“将谁欺乎!”上任不到二十天,即上书朝廷,请求豁免秋税,建议用青苗钱贴补民生。密州两年,除治盐拿贼,抗拒朝廷大小官员“造律”欺压地方,出奏百姓谋生之苦,还为本地弃婴做了一件看似微末之事,今日看来,却意义深远。蝗灾、旱灾、盐灾、盗灾、官灾……致使民间贫弱,苏轼下乡探访时,一路简行,时见荒野弃婴,心实难安。他筹措一笔经费,凡养不起婴儿的家庭,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生成,就不会再抛弃了。这看似书生意气的施政,温暖了一方土地,弃婴减少,人口回升,人伦之灾缓解。
寂寞孤独是苏轼的生命状态,又因此让他持有豁达朗观。前者源于出仕之多舛,后者源自内心之丰润。一实一虚成就了苏轼。若说苏轼算不得成功的政治家,却不能否认他是出色的文学家。怀才不遇的耀眼之光让他身后留下许许多多文化畅想的遗迹。历史最终给了每个人最贴切的结局。熙宁八年,出任密州第二年夏,苏轼偶然发现破败荒芜的官舍北一座废弃的旧城台,稍加修葺,就成高而明的休闲之地,登台四望,马耳山、常山若隐若现,穆陵幽然如城,潍河浩渺北去,视界很好,风景壮阔。他去信让为官济南的老弟苏辙取个名字。深谙苏轼者莫如苏辙。苏辙很快回信,建议叫“超然台”,并解释说:“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违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熙宁九年中秋佳节,苏轼与僚友会饮于超然台,欢愉之际,抬头望大而圆的月亮,竟只一枚,子由老弟可也在遥看这轮明月?团聚的人们如何晓得世上的时间不是倒计的呢?苏轼悲从中来,大醉,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孤高的词句,超脱了物的羁绊。
苏轼进士及第,一生出仕,屡遭贬谪,若无旷达胸襟,如何安身立命?迁徙流转任中,“东坡处处筑苏堤”,其中烟柳笼纱的“苏堤春晓”已是杭州西湖的十景之一,至今游人如织。被贬安徽阜阳时,苏轼率众疏浚颍州西湖,筑长堤成景。再贬广东惠州,苏轼已年近六旬,他捐助疏浚惠阳西湖,修长堤一条,后人亦名苏堤。苏堤横穿湖心,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水生灿烂,美景撩人。从超然台到苏堤,再到海南儋州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一系列文化现象和结果,全非为官之便,怕与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文化视野、文人睿智多有关系吧?
歌德说:“人生苦短,勿饮劣酒。”有时候我们会问:历史这个操蛋的物件,更老了还是年轻了,高尚了还是俗气了?反过来想,每一桩事情都不是它们本来的面目,而可能代表着另外的事情。
写于2019年
整理于2020年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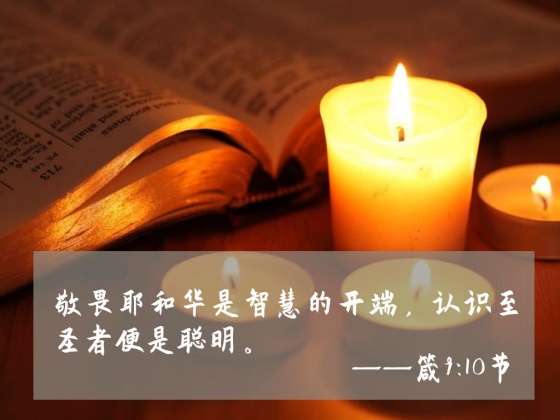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