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未超过五四那代先贤的水平。他对历史的研究也未超过民国史学家的水平。钱钟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虽然不无精辟之说,却都是只言片语,没有系统的学术思想。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谈中国诗》《谈艺录》,都没有超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顾随的《苏辛词说》、沈祖棻的《宋词赏析》、龙榆生的《辞词曲概论》、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余陛云的《诗境浅说》、缪钺的《诗词散论》等,这些谈古典诗词的经典著作的水平。所以夏志清用“除了钱钟书,无人能及”这种言过其实的话映衬吉川的成就,说明不了什么。
前几年有人提议建立“钱学”,不知道这个人要研究钱钟书的什么?钱钟书有西学功底,但是他谈历史、谈文学中,看不出受西学理论思想影响的痕迹。钱钟书与民国时期留学归国的学者一样,对西学都是浮光掠影,并未获得西学的思想精粹与真谛。在当代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中,钱钟书的研究远不及缪钺与叶嘉莹,这有缪钺与叶嘉莹合著的《灵溪词说》为证。叶嘉莹先生谈古典诗词中,常用西方文学理论思想明确古典诗词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别开生面,让读者耳目一新。叶嘉莹先生引用西学理论讲古典诗词的说法,佐证了“从世界看中国”的真理意义。“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晚年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提出了“从世界看中国”这个著名论断。这个论断的真理意义涵盖所有的领域。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如果不能“从世界看中国”,只能停留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民国专家的水平上。民国时期的专家创造了古典诗词研究的时代顶峰,后人要超越很难。这方面的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创新,只能“从世界看中国”。叶嘉莹先生仅是这种创新的起步。古典诗词研究的创新道路,有待后来者沿着“从世界看中国”的思路努力开辟。但是钱钟书并没有“从世界看中国”。
《钱钟书文集》在文化、历史、文学三方面没有什么学术思想的建树。很多人感兴趣钱钟书,都是源于钱的文章中那些俏皮话不乏聪明机智,这样的读书兴趣都是浅层次的感受。钱钟书说不上是个大学者,更谈不上是思想家。夏志清捧钱钟书,说明夏志清并不了解中国学术界。
读夏志清文章的突出感觉是,夏志清的话不可轻易相信,他有夸大其词的说话习惯。他说张爱玲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夸大其词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形象,不及《阿Q正传》里的阿Q、《雷雨》中的繁漪。阿Q、繁漪是现代文学中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属于不朽的文学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看过就忘了,不留印象。再说张爱玲的小说既不反映时代的风貌特征,也不体现故事情节涵有社会生活的时代意义,不过是十里洋场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们,围绕男女那点事使尽了所有本事。这样的小说走红孤岛是必然现象:不过是为无所事事的富太阔少在性饥渴中提供了文字上的精神快感罢了。
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反映了他的文学鉴赏水平很一般。所以他引用吉川的那些说法,也往往言过其实,经不住推敲。下面谈谈这个问题。
(二)
夏志清推荐吉川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没有莎士比亚。但西洋也没有司马迁、杜甫。”吉川这话接下来的意思是:西方没有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没有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内行人一看吉川这个类比就会觉得,在文化意义上说明不了什么。实际上,吉川的著作反映出,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对司马迁的《史记》、对杜甫的诗都缺乏深入研究,他对莎士比亚的了解流于粗浅,对司马迁、杜甫的了解流于平庸。
吉川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在于“莎士比亚很会写恶人”。这样的论断,连普通读者都能看出来与事实不符:存世的三十七部莎士比亚戏剧中,最著名的文学形象是《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是驰名世界的文学形象。但哈姆莱特不是恶人。
吉川没有从莎翁戏剧看出来:莎士比亚不但“很会写恶人”,而且会写人性意义上的人;会写天性丰富而又复杂的人;会写被社会异化了的人。吉川没有看到,血肉丰满的天性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展示。吉川更没有看出来:莎翁戏剧不是停留在展示天性人的层面上,也不仅仅展示被异化了的人。若那样,莎士比亚就不是莎士比亚了。吉川有所不知,莎士比亚戏剧最卓越的贡献是:通过剧中人物的生活行为、社会活动、心理矛盾,通过剧中人物一句话,暗示了社会的普遍问题,从而引起读者的思想觉醒与精神振拔。
例如,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涵有的“哈姆莱特命题”——To be,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这不仅是文学界永恒的主题,也是欧洲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哈姆莱特》在十七世纪第一天问世,犹如晴天霹雳一样炸响在欧洲上空。沉迷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欧洲人被震撼了:是啊!“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哈姆莱特命题”成为欧洲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于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消隐了的理性又回到了欧洲人的正常思维中。于是欧洲历史上空前的启蒙运动爆发了。所以有人说《哈姆莱特》问世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先声!欧洲近代史中的莎士比亚其实中国读者并不了解:莎士比亚终结了文艺复兴,挽救了欧洲人,开辟了欧洲持续二百年的启蒙运动。所以后人在纪念莎士比亚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莎士比亚不仅在欧洲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莎士比亚还是西方近现代史中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所以,丘吉尔说“我宁愿不要印度,却不能不要莎士比亚”。看来吉川并不了解这些基本常识:莎士比亚戏剧是体现人性的精神宝典,是西方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是欧洲思想史上的奇观,是西方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
吉川说莎士比亚仅仅“很会写恶人”——这样低级的欣赏水平,有失一个学者的身份。那么吉川推崇的司马迁与杜甫在东方文化、东方历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作用?这个问题不好解答,还是从司马迁的《史记》、杜甫诗谈起吧。
(三)
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但这个崇高的评价,不是史学意义上的,而是《史记》形象地、完美地体现了古典文化“文史不分”中那种既丰富多彩又生动形象的特色。《史记》是文史不分中空前绝后的光辉典范。而《项羽本纪》又是《史记》中永不衰谢的文学奇葩。
司马迁把项羽写活了,写成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英杰;写成了中国历史上顶天立地的英雄。楚汉之争的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中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景象,呈现出威武雄壮的气象。《项羽本纪》中那个让人过目不忘的项王,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那首诗、那几句话都是神来之笔!都有着不朽的精神震撼力量。所以我曾经告诉学生:《史记》可以略读,但《项羽本纪》最好能背诵下来,会终生受益。
司马迁有着卓越的文学天才,却没有基本的史学思想。《史记》就史学价值来说,称不上“史家的绝唱”。严格说《史记》并未摆脱中国史学流水账的旧习,司马迁不过是用纪传体,为流水账的史学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打破了历史是帝王将相家族史的惯例罢了。不必讳言的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很成问题,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究天人之变”就是研究“天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天与人是两个本质不同的存在,天就是天,人就是人,两者没有内在联系,怎样“合一”?中国文化连天是什么、人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谈什么“天人合一”?所以“天人合一”研究了两千多年,既没有哲学上的贡献,也没有科学上的发现。不过是浪费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时间、精力、生命罢了。
实际上,天是个科学问题。人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个宗教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这是科学解答不了的先验问题。只有哲学才能解答,只有宗教才能给出终极答案。这些问题司马迁都没有搞明白、也不可能搞明白。所以他的“究天人之际”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至于“通古今之变”,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发现历史规律。但是历史没有规律!凡是规律都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中国历史的进化过程与欧洲历史的进化过程大不一样,并不反映出历史有规律:中国从未有过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没有欧洲的奴隶社会。中国秦汉以降是两千多年的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这样的社会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欧洲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是教会与国王共同统治欧洲的“双驾马车”的分权社会。中国秦汉以降都是集权制社会。所以东西方走过的不同道路说明:历史没有规律。
规律都是可以在相同的时间里重现相同的现象。但是中国历史从未有过这种现象。历代王朝存世时间大不一样:短命的秦朝仅十五年,隋朝三十七年。汉朝竟长达四百多年。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东周列国时期混战了五百多年!中国历史这样多的“不一样”,哪来的规律?
既然历史没有规律,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岂不是一句空话?中国人研究“通古今之变”两千年了,哪个史学家“通古今之变”了?谁也不可能“通古今之变”!
所以《史记》既没有实现“究天人之际”,也没有实现“通古今之变”。应该实事求是承认: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不是建立在科学上,而是出于个人的良好愿望。
问题是,这种脱离实际的良好愿望怎么就成了历代史学家宗奉的圭臬?钱穆就对这句空话推崇备至。所以钱穆虽然著作等身,但他的史学并没有什么建树,不过是用历史佐证了他钟情的儒家文化罢了。吉川推崇《史记》作者司马迁无可厚非,却没有说到点子上。
(四)
杜甫的诗是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称赞杜甫诗是“诗史”,是因为杜甫用诗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社会状况、老百姓的疾苦、战乱中自己的艰难经历,杜甫诗表达了对朝廷不能再现开元年间安定淳朴社会的痛切失望。
如果说史书对大唐盛世的记载,淡化了大唐在连年累月的割据混战造成百业凋敝、经济萧条、民无安居中,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这个历史事实,那么杜甫的诗则真实地、生动地、悲怆地再现了大唐还有并不盛世的、多么惨痛的历史面貌。这是有些人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的根本原因。
但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说法是受十九世纪思想家的误导。实际上,所有的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中,没有人考虑自己是搞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创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创作思想中是不存在的。像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都是表达了作者不同的思想情感与不同的审美感受,用这两个“主义”比附两位诗人的作品能说明什么?其实这种比附既不有利于创作,也不有利于欣赏。这种上纲上线的说法是唯物机械论,还是政治庸俗化?抑或是“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翻版?实际上两个“主义”对文学艺术来说都是空洞的无用论。
应该看到,“现实主义诗人”这顶好看不中用的桂冠淹没了杜甫诗所含有的丰富的思想情感、崇高的家国情怀、高尚的审美境界、精湛的艺术造诣。那些动辄讲“现实主义诗人”的理论家并不知道:家国情怀是杜甫存世一千五百首诗的主旋律。众所周知,家国情怀又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经久不衰地响彻中国文学的大厦。家国情怀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遗憾的是,家国情怀在宋后的明清王朝变本加厉的集权统治中,畸变为愚昧的忠君思想,悠久的家国情怀永远消失在明清时期了。不过这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这里打住,回到杜甫的诗。
本文不想具体谈杜甫诗,不必重复杜甫在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形式上作出的突出贡献,千百年来谈杜甫诗的文章车载斗量,再说还是那些东西。这里只想指出:杜甫“诗史”的价值,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诗史”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
(1)开辟了古典诗词内容题材更广阔的创作道路。诗在杜甫前主要是文人用来唱和酬答及个人情感的抒发。“诗史”的重要示范作用是:诗可以叙事、可以在叙事中抒发既丰富又深邃的情感。所以有人说杜甫的“诗史”深远地影响了古典诗词的发展。
(2)“诗史”产生的这个重要影响使古典诗词含有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这个价值被民国时期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推崇的“以诗证史”涵盖了。“以诗证史”是中国古典诗词才有的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所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重视“以诗证史”的问题,都读中国古典诗词。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像夏志清、吉川那样不顾事实、夸大其词地过誉杜甫“诗史”的史学价值。杜甫“诗史”真实地、生动地、悲怆地描绘了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风貌含有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自不待言。但是,杜甫“诗史”虽然再现了中唐不堪的社会状况、老百姓疾苦;却并未就社会状况及老百姓疾苦提出问题来。也就是说,杜甫“诗史”仅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以及自己的家国情怀在这种描绘中表现出的无奈而又悲怆的感叹,仅此而已。“诗史”所有的叙述并无问题意识。“诗史”的描绘与抒怀中,如果能暗含发人深省的问题意识,“诗史”的思想含量、文化含量将会丰富沉重得多。在这一点上,杜甫远不及晚唐诗人杜牧。
杜牧的怀古咏史诗被誉为“中国古典诗词咏史诗的压卷之作”,主要是杜牧的怀古咏史诗涵有问题意识,唯其这种问题意识,才是杜牧怀古咏史诗经久不衰地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你看杜牧的怀古咏史诗《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其中的“东风不与周郎便”就暗含着重要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东风,是否会有赤壁大战?是否会有三国局面的出现?诚然,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历史假设的逻辑是存在的!这个逻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决定东汉末年历史走向、决定三国局面的根本力量,不是孙权、周瑜、刘备、诸葛亮、曹操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东风!东风是什么?东风是是天意,是偶然现象。沿着这个逻辑的思路放眼望去,历史的哪一次重大变化不是偶然因素发挥的作用?偶然因素没有规律,所以历史哪来的规律?杜牧为什么能在怀古咏史诗中提出这样重要的问题来?这与人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文化修养、精神境界、价值观不无关系。这里不可能展开谈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吧。
遗憾的是,杜甫的“诗史”没有问题意识。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杜甫:一个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治国思想的人,总是不切实际地幻想明君治国能再现政通人和、风俗淳厚的大唐“盛世”。这种泛道德主义的价值观,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的仁政上的人,怎么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社会问题来?何况仁政从来都是中国文化里的乌托邦。难道不是吗?有史以来何曾有过真正的仁政社会?
杜甫的“诗史”缺乏问题意识,与其渗入骨子里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仁政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杜甫的“诗史”虽然反映了中唐时期中国人苦难的生活、苦难的命运,但是杜甫没有苦难意识,他的诗仅是表现社会状况的“诗史”。他不可能像李煜那样在人生命运、人类命运的意义上咏叹自己经历的苦难。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诗史”上升到李煜词涵有的那种人生哲理层次而增添无尽哲思的浮想联翩。
如果说杜甫由于没有苦难意识,他的“诗史”只能真实地反映了中唐的社会面貌与老百姓的疾苦,从而使读者油生历史的感怀与悲悯的心情,这是杜甫“诗史”受到普遍欢迎的根本原因;那么,李煜因为有苦难意识,所以他在咏叹自己的苦难经历中,能认识到自己的经历与人生命运、人类命运都是一样的苦难。于是李煜词咏叹苦难经历的思想便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从而在所有读者中引起强烈的思想情感共鸣!这是李煜词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根本原因;也是解开诗界困惑千年之久的“‘亡国之君的哀音’为什么会经久不衰”这个奥秘的钥匙。
苦难意识是基督教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思想理念,是哲学、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苦难意识涵有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艰苦;还意味着精神生活的苦,人生道路的苦,日常生活的苦,学业事业上的苦,爱情的苦,婚姻的苦,家庭的苦,前行出路的苦,追求理想的苦……但是生活在泛道德主义、实用主义、乐感主义文化中的人,并不愿意有苦难意识。苦难意识虽然是宗教文化产生的概念,却体现了西方哲学的深度与广度。没有苦难意识,是中国文学艺术内涵稀薄的根本原因。
王国维对李煜词评价极高,但他没有搞明白“李煜词为什么是空前绝后的”这个问题。主要是王国维没有苦难意识这个概念。理论上讲的李煜有苦难意识,并非说李煜具有现代概念的苦难意识。而是李煜丰厚的文化修养,琴棋书画皆通的艺术造诣,缘佛近禅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命运、对人类命运有了非世俗的认识。这种认识提升了李煜的精神境界。所以王国维称李煜有“担荷人类罪恶”的襟怀。
应该看,到吉川读杜甫诗没有读出上述意义。他的“读后感”仍然停留在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平庸层面上。夏志清与吉川把钱钟书、莎士比亚、司马迁、杜甫扯到一起想说明什么?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却暴露了他们的文化学养、学术视野、价值观都存在问题。明治维新距吉川相去不远,但吉川不是明治维新精神的传人。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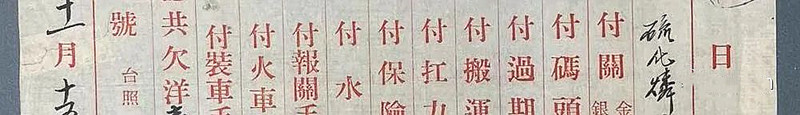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