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
1
宝贵的记忆经不起时间的流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三十年前一张稚气的脸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玻璃碎片割伤的是自己,是现在。
但有件事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带了相机。一部佳能50D单反。平常出门我没带相机的习惯,说起来缺乏摄影爱好者的素养。可那天我带了。不是为给卢维军拍照,只为找他聊天,相机扔在车座上。卢维军同学研究周易,到门店找他的人很多。我们说笑不多会儿,他来了客人。我回避走出店门,打算四处逛逛,赏赏春光。大多数树木没发芽,但柳树绿了。我在胡同口一棵硕大垂柳下待了片刻,摘了几片柳叶,朝北走。胡同北端,就是村庄的西北角立块黑色的志石,上写“娘娘庙”。我看那三个字足足几分钟,因不了解它的来历而好奇。随后,我迅速回到车子,取了相机,走进村庄的宽街陋巷……现在我想不起村庄的名字,大概和一直不清楚娘娘庙的前因后果有关。我向来欠缺对虚无之物的研究。
村庄是真实的,一间间肩靠肩、背靠背的房屋即为现实存在,进进出出的人演绎真实的故事,上演当下供将来回忆的悲喜。图片记录真实,让我得见,给我想象和回味。法国史学家丹纳曾言:“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他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规律,证明规律”。我该怎么做?
入夜,查看照片,忽然产生写点什么的冲动,不再写虚幻的缥缈的诗歌而写实实在在的东西,写家乡,写出生地,写亲历和所见,写现在。我写下“发现高密”,写下一篇不似文章的文章开头。随后,它成了一个持续的行为,一个事件,一种坚持,一段我生活的主旋律,一次出乎意料的付出和收获。
翻开公众号“龙河之春”,找到底,题为《娘娘庙》的文章还在。一篇文章的名字,一座村庄的名字,它帮我找回“发现高密”的起点。阅读那几段幼稚的文字,想笑却笑不出来,仿佛又回到数年前临屏书写的时刻。
2
由于重叠,比如多年后回到同一个逗留或生活过的地方,记忆会被唤醒。复活的记忆不虚浮,往往有味道,或甜蜜或涩苦,或甜蜜中掺杂涩苦,血管贲张,心房猛跳,眼神便多了自己表达不清的光芒。光芒中惆怅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时光不再,物是人非。这说明,你曾在那个地方用过心,动过情感,至少认真对待了经历的事情。
2018年12月19日,天阴沉,霾很重,准备第二次踏访晏王庙村,为了“夷地良人”的一篇文章。路上并不顺利,通晏王庙的干道拓宽,道路封堵,提示绕行。导航开启,过胶州市几个村庄后才拐回高密境内。冬天的原野寥落又空寂,白色塑料大棚和孤树是主要景物。土路在田间迂回,坑洼狭窄,车子摇摇晃晃,速度如步行。没多久,导航警示调头,它不认识面前去往目的地的小路,意欲返回竖立绕行牌子的干道。下车查看,直觉上距离晏王庙已不远,驱车冒险前行,居然找到通往晏王庙的水泥路,半个小时左右,车子停在和上次来晏王庙重叠的地方:村北一座宽大的红瓦房屋前的空地,几步远一个十字路口和一块志石。
2014年3月24日,起始写“发现高密”两日后,琢磨去晏王庙看看。当时对高密,除了历史上的三贤,我一无所知。晏王庙是晏婴故里,名人出生地,一定有值得发现走笔的东西。因为打了鸡血,一路顺畅,我信心满满地把车停在五年后停车的地方,用五年前的心情盯看十字路口黑色志石“晏王庙”三字,像看“娘娘庙”的神情相似,只是渴望更多一些,也许还萌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此时一位老乡过十字路口,赶紧上前打问“庙”的位置。老乡一脸懵懂,说没有庙。我旋即顿悟(人生的顿悟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晏王庙和娘娘庙一样指村庄,是村庄的名字。我对自己的无知深感惭愧。老乡也顿悟了:是找晏子墓吧?他转身,指了指路西遍布塑料温室大棚的农田。
百米外,越过大棚,望到一抔黄土的坟头,阳光下,崭新而荒凉,全无名人故里的繁华,望不到两千多年的沧桑。
志石已不在原位,移到了十字路口南十余米外路西,面东插在几个塑料大棚边上。五年时间它变化了位置。住村北大湾沿一间看护房的老奶奶还在吗?注视远处的志石第一个念头是去寻找那位五年前蹲在屋前收拾大白菜的老奶奶。过几间无人居住的旧屋,当今的话叫危房,亟需棚户区改造的危房,它们还和五年前一样,破旧不堪,却不再坍塌。远远见红砖垒的狭小的小屋还在。我一阵兴奋,一嘴甜蜜和紧张的味道。
这小屋像间场院屋或野外的看护房,房门捏了锁,垂挂细网带碎花的门帘,屋前堆着老人用过的物件,包括被褥,摞在一起,盖了防雨布,高如坟堆。我似乎嘟囔了句什么,想品咂此刻的味道,却是分辨不出。加上五岁,老人应已过九十。她怎么了?镜子还在,不见了照镜子的人。大湾西有位老大娘在捡烧火用的树枝和落叶,我绕过去,问老奶奶的情况。她直起腰,大冬天居然脸渗汗珠,站直了仍然有点驼。她一手垂背,一手指小屋,告诉我老人还在,被闺女接到了外地。享福去了。这是她告诉我的。我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拾柴火。她笑笑:反正闲着。我便又折去村西北角的晏子墓。甜之味还在。我安慰自己。我喜欢这味道。
风来雨去,晏子墓荒芜了,冢上生满荒草,枯干在冬冷中。2018年深冬的甬道比2014年初春多了两行蹲兽,但穹碑的红绸带被风吹走了。红绸带是2013年深秋重修晏子墓时有人给围上的,像根围脖,鲜艳明亮。又见甬道西边立了块石碑,上写重修晏子墓的时间和意义,是墓成至少一年后,和蹲兽一起补立的——也许为了减少此地的荒寒氛围。
如今回忆起两次晏王庙的探访便有个假设。假如晏婴有不死之躯,辞去官职,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迈着方步穿透时间的屏障,从临淄回到他的老家,重踏故里,像我一样围绕村庄转转,和相遇的乡亲聊聊天,在某棵老槐树下徘徊,走进大棚手摸土豆苗,于街巷中反复踱步,他嘴里会生就怎样的滋味?是甜蜜还是苦涩?抑或别的味道?
事实上,在这雾霾厚重的天气里,暮色沉沉之中,我在寻找一个拥有高尚精神的人,我相信他隐藏历史深处,没有真死去。当我和刚栽种完土豆苗的王玉静女士在村北水泥路相遇并闲聊时,这个人就在我们旁边,像棵沉默的树,心怀道德律,头顶星空。只是,我满脸惆怅,不敢肯定,我是否看见了他,但敢肯定,他正瞪眼瞧着我们,像个死不瞑目的人。
3
花一段时间,仔细走访并用文字把所见所想记录下来的村庄,是高密西南偏南部的小村落,叫相家庄,隶属柴沟镇。对这个村庄的描述因为文字粗陋没选入《发现高密》不代表我遗忘了它。这是一次真正的开始,从时间和思想上。它让我认识到村庄在这块土地的重要性。它让我看到一种根的东西生长在古老的树木之中,隐藏在坍塌和即将倾圮的房屋墙基之下,显露在生活于此的人们亦喜亦忧的脸上。从此之后,连续几年,不论春夏秋冬,我频繁进出大大小小的村落,为它们留下了影像和文字。或许,那些图片和字符,正是人们寻觅的抽象概念下的乡愁。
高密近千个村庄,为什么首选相家庄?有不足外人道的原因。有朋友告诉我说相家庄三面环水,村庄与外界连接的是小石桥,我心中升起一丝甜蜜的忧伤。它让我想起工作和生活过的江南水乡,古老的村落隐现在水雾弥漫中,房舍立在水边,小舢板、乌篷船和瓜皮舟送来船桨与流水的碰撞声,生满青苔的石桥把幽深的古巷缝合贯通,总有一两把油纸伞从石阶和桥洞中经过,竖起耳朵,便听到不解其意的吴侬软语……它让我靠近了行将远离的一段记忆,缓慢而清晰。
也许四十年,也许五十年,或更远以前,相家庄和我这位朋友的记忆吻合——三股流水以不同的形态缠绕村庄,裹带水草和游鱼,漫过人们赖以生存的四季,走进村庄又依依远去。但是今天,2014年6月10日这天,大股的流水已无处可寻,村庄陷入丘岭间,丘岭整理成平坦的农田,留下舒缓的坡度,只有村西断崖式的河堤下,林木森森,五龙河宽阔的河床挖出一条窄窄的深沟,残存一截弱水,深不足半米。由于无法流动,积垢太多,水变黑发臭,但是,六、七只水鸭和一只大白鹅却在这洼水中追逐嬉戏,玩得津津有味。有几只头朝下,毛绒绒的屁股朝天,嘴巴翻开泥浆,寻找食物。有几只可能累了,晃悠悠跑去树荫,不多会儿又返回,对村庄最后的这点水特别依恋的样子,嘎嘎地冲着天空,冲耀眼的太阳叫几声。我停在石桥上,石桥横躺河床,我们一起观望了它们良久。
2017年5月27日,全程探访五龙河途中,再次行走相家庄。那是个炎热的中午,街巷不见人影。已经行走近五个小时,午饭当口,又累又渴,日头下曝晒时间过长,人很疲乏。加快脚步赶去河底,那儿白杨林下的阴凉,能让我喘口气,去暑气。当我面朝南站上几年前待过的石桥,无风,最先感受的是凝重的寂静。寂静仿佛是这里特别的声音。这时候我希望有活物陪伴,一只飞鸟穿过林间,一群水鸭戏水,或树叶的唰唰声。我张望那群水鸭。沟内的水完全干涸,水鸭遁形。它们去了那里?我的回忆里吗?我怅然若失,感觉丢掉了什么,一种丢失后再也捡不回来的东西。
那座碾盘还在,斜躺桥头东南几棵树下,背贴黄土,面朝村庄,2014年的地方。我认为的老地方。一个沉默之物。默默无言是它的本色。它曾经向村庄发出声音,借助碾磙的转动和五谷的破碎。很早以前它就沉默了,被从村庄转移到一里外的河边之后。几年不见,它变了模样。第一次见它时它是完整的,第二次见到它已断裂为两块。是时间改变了它,也许还有外力。它一定遭遇了什么,但不会说出来,至少不会说给我听。可我相信它与万物一样,怀有心灵,我想了解它的心有没有一分为二,有没有淌出血液一般鲜艳的东西。在《五龙河》其中一章的开篇,我和它展开了心灵的对话。我们都忘了烈日炎炎。
时间消耗着我们。我和碾盘以及周围的一切。时间把我们消耗成我们不想成为的样子,又必然地把我们塑造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在时间中彼此顾念——一座村庄,一个碾盘,一条乌篷船。是的,仅此而已。
告别碾盘(我们不会第三次相遇,但我想告诉它不必对人类失望),沿河床走向五龙河纵深,一条不似小路的小路河道里起伏。路上和两侧,整个河床,生长野草。假如野草也会做梦,它们的噩梦应该是梦到了人类。我踩着它们的头颅去往远处。我希望它们没梦到我,而我眼里尽是绿色,足下一股清新。
4
我把村庄作为“老家三部曲”写作的重点,不同年份写下的村庄侧重点不同,每个村庄设定在一个主题下展开。它没有用记流水账的方式因照顾村庄的方方面面而降低文学性。同时,文学性也并非强加于村庄身上,而是自然形成。我拒绝贩卖白开水。我卖浓茶和烈酒。再加一点用于思考的盐。现实中我不喜欢重口味,倾向于品尝原味,比如白开水,当然也喝茶。必须承认,原味中也有重口味,比如红烧肉,但在此不讨论吃喝。村庄,无论大小,历史远近,都是重口味的组合,或芜杂的生命体。每一个村庄都给到我庞大的信息,有时庞大到我难以承受。信息流淌在当下这一刻——一堵破损的屋墙、一棵半枯半萌的老树、一根弃之不用的烟囱、一截忽明忽暗的窄巷、一位走来又走去的老人身上。那些村庄,短则一两百年,长则五六百年,以可见的不断翻新的容貌,承载深不见底的过去。一代一代的人从历史深处来到那一刻的阳光下,街巷中徘徊。
村庄不是一个个孤立生存的个体。它们以地缘、风俗、亲情相互联结,组成乡土的网。用一个个结系住乡愁。多数人在网中度过一生。少数人冲破了这张网,在非村庄概念的领域生活,但心中乡愁的结,聚而不散。每个人的身体都循环着村庄的血脉,头顶的明月照耀的永远是家乡故土。这是必然的人伦更迭。
除人伦,村庄的生态环境也处在变化之中。这个生态环境是村庄的生存环境,有看得见的变化,有看不见的变化。《程氏易传》言:“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事物能够止于当止之所就安定,不能止于当止之所就悖乱。时代在前进,“止”变成理想的状态,“所”变成持续变化的环境。变化一日千里让人兴奋,也让人忧虑。问题在于,比如面对不断拓宽的村庄街巷,铺上了水泥或柏油,干净了,出入方便了,人们难免又回忆起村落曾经的土街泥巷,湾沟流水,心里怅怅的,说不清哪一种现状更符合自己对村庄抱持的情感。不管怎样,总有一种失落如影随形,让目光黯淡。它既失落于泥泞胡同,也失落于通衢大道。现实比看见的、想象的更加复杂。
也许,这种痛心的失落正像诺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今天,已经很难再谈论爱了。”如果爱是事物当“止”之“所”,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住脚步,驻足在一幢被我们认为美丽的房屋前,仰面明晃晃的天空和俯视苍凉拥挤的大地,进行一番既不失感性也不失于理性的思考呢?
或者,我们愿意相信,无论村庄怎样变化(如今看来,它一定朝着越来越美丽的方向),乡土民情将随之变化,并且朝着越来越浓烈赤诚而非冷漠麻木的方向,朝向可止之所,朝向人心和仁。如此,当是村庄的现在和未来,当是所书之重。
5
城市吞并就近的村庄,规模壮大,本来离城远些的村庄猛地站在了城市边缘,懵懂又惊喜。倘若造城运动进一步深入,农田纳入开发用地,较远村庄也存在被吞噬的可能;真正“偏远”的村庄,粮食收入低廉,劳动力撇下耕地,进城务工,村内只剩老弱病残留守,逐步成为概念上的空村。于是,有人断言:村庄正在消失,传统意义的村庄一个个沦为“最后的村庄”。这是现象,也是事实。然而,断言村庄消失,或言之尚早。
一部分村庄的确消失了,伴随城市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挤压乡村,犹如刀刃碰刀背,刀刃还是刀背受伤很难说。也许都会受伤。村庄里游走,显见的事实是街巷两边的宅院,相当一部分大门关闭,铁锁把门,院内荒草丛生,寂无人迹。有的院落因为久不住人,墙倒屋塌,却依然坚守宅基地,看上去挣扎又无奈。也有些院落崭新,红砖的围墙,水泥抹面的房屋,红瓦绿树,空间宽大,平日里大门上锁,但随时可能有人回来居住,只是空闲的时间远远多于居住的时间。此类宅院,存在每一个村庄,有的多,有的少。
人去了哪里?一种情况是绝户。因无子女老人又去世,或只有女性子女又远嫁他乡,遗留下房子。这类房子无人打理,停在了村庄的过去,大多为土坯房,房顶院墙坍塌,是村庄残破的记忆。再一种情况是空巢。子女因为各种努力,比如考学,摆脱了乡村,生活在离家乡或远或近的城市,有的出了国门。老人在世时,每年回家一趟两趟,仿佛村庄的过客。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有的被接进城,有的在村庄离世。老家再无可亲近的直系亲属后,村庄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故土,只有乡愁作为纽带连接着对故去亲人的思念,而故居荒芜,萋萋荒草萌发在心里,仿佛一幅画画在生生不息的背景中——城市成为下一代人的家乡,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农村的衰败,生活的窘迫,迫使农村劳动力进城,有的成了产业工人,有的从事建筑业,有的寄居城市做点小买卖。他们分流在城市,以勤劳换取生存的资本,汗水滴在城市的角角落落,生活同样不易,但收入高于留守村庄种地。他们大多脚踏两只船。一条腿在城市,一条腿在农村。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城市买了商品房,过上了双面人生活。一面像城里人,每天早出晚归上班打工,参与社区活动;一面仍然是农村人,农忙时节返乡,收种庄稼。他们在城里有栖身之地,有工可务,在村庄有旧居,有耕地,有乡情,往来穿梭,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不妨称他们候鸟。
时代将朝哪一个方向迈步?依当今的趋势,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吸附其中,定居城市,繁衍子孙,村庄消失的可能性便会加大。假如村庄真的败落或消失了,将是一首哀歌。但是,社会是个庞大并复杂的生命体,容不得乡村的衰败和消失,承受不了来自泥土的原生资源诸如粮食的减少或断裂。乡村,或者村庄,是承载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遭受冲击和打压,都是暂时的。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规避粮食危机的一系列举措,城市生活综合成本的提高甚至不堪重负,促使农村劳动力回流乡村,振兴家乡经济,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乡土,历史前进的脚步离不开乡土,双脚走过大地才会踏实并稳健。人类尚未学会飞行,也不可能长出翅膀。蝉鸣七日,靠饮清风和朝露,这是神赐生命的倔强和荣耀,然而人做不到。硬币已抛向空中,它旋转着,呼啸着,终有一刻落地。盯住硬币的一面时,另一面同时存在,错误的选择随时发生。
6
城市的繁华令人流连,乡间的宁静让人向往。一种理想的生活是事业在城市有成,乡间有田园可归。少数人实现了这种生活方式,多数人还在打拼途中。一种可叹的局面是:城市不再是你想要的城市,乡间不再有你采菊的东篱。
浮躁生于人心。它像一面镜子,映现社会心态。让城市喧嚣的不是城市,赶走宁静的不是村庄。让人心神不宁的并非十三路公交车。让人心浮气躁的并非离村较远的场院屋。人吓人吓死人,人害人害死人。人是这个世界最不稳定的构件,最危险的刀锋。百花中,羔羊穿过旷野,多么甜美的图画。百花中,羔羊穿过旷野,多么危险的举动。百花中,有人昼伏夜出。利益追逐让众多人成为猎人,在社会的丛林,在城市和乡间,权柄和贪婪搜寻着猎物。丛林法则让豺狼笑,羔羊哭。而今,满足现状的还有几个呢?不争变为宝贵的资源和道德。多个不争的人居然能多一份安宁。
不争的事物依然存在。在村庄,在荒僻之处,有个湾。它拥有月亮的身体,岸边一棵供吴刚永远砍伐不倒的桂树,陪伴嫦娥长夜失眠的白兔总是安静,村庄童年的梦想种在水下,春雨秋风千里投奔它们的宿地。可不知什么时候起,坚持学习蜻蜓点水的垂柳枯死了,鲫鱼吹气泡的清水干涸了,荒草抓住湾沿,偷窥人间发生了什么。今天,它仍然在荒僻之处,隐去了月亮的身形,曾经不老的新娘,成了满脸沧桑的老菜皮。它在腐朽,在退却,却依旧沉默,依旧不争。它等待着,忽然有一天,垃圾填满了它,它心甘情愿地让有心人盖一座宽大的房子。看上去它不存在了,但它永远是一个象征。
有多少人家就有多少座门楼。门楼是村庄的不争之物。它像门槛一样供人跨越,供人踩踏,它没有不耐烦也从未喊过痛。它曾经十分简陋,甚至寒碜,如今换了一副身架,昂立着,为主人支撑面子——即使经常感觉累。但它恪守清心寡欲,不积攒风,也不浪费雨,至于铧犁、钉耙、二齿钩子寄存它那儿,它也欣然从命,它清楚,那些勤劳的家什,是影壁墙大红福字的组成部分。可它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厚重的铁锈让它的肠胃不舒服。它时常想说点什么,终于还是忍住了。它就要失去不争的本色了。
一座门楼前,我停下游走,点上烟。门楼壮观,也很普通,吸引我的不是门楼本身,而是门楼前几样东西。一只水泥大缸倒扣地面,割开一个方形的口子,是门,缸内是看门狗的窝。熟睡的小狗,趴在门口,但耳朵支愣开,注意着风吹草动。缸顶,一个树墩,静默地注视我和小狗,只要我有异常举动,它就会跳起来。门楼外并排两根水泥杆,直插天空,高得惊人。我看出那是一首诗。一首关于村庄的充满爱欲的诗,诗意中的自由和幸福抑或禁锢和不幸在静止的形式中流动,它实实在在地展示在我面前,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展示了它超越现实的意志:
门楼的红漆铁门无论怎么不情愿
每天必须至少一次打开和关闭
但它真实的欲望并非热衷于分分合合
并排耸立的两根水泥线杆
直到明白天空其实不需要它们支撑
才掌握刻度的秘密在于测量白昼和黑夜一样无益
飞鸟投下过时间的侧影
后来被隔壁飘落的桐叶覆盖
一阵风慷慨地从村外的灌木丛到达这里
它清点了万物包括熟睡中小狗的每根金色毛发
却无法把小狗梦中即将跌倒在水沟边
错乱的脚步摆正
水泥大缸不再派其它用场
无论睡去还是醒来,小狗会一生守护
白杨树墩除了习惯庸常的生活
还占据了水泥缸顶端的风景
它一边腐朽一边俯视铁链拴住的小狗
在某个极限内运动,吃饭,喝水
幸运的是,不争的人群依然存在,像众多不争的事物一样。不争者分两种:欠缺社会关系或无力构建社会关系的人;冷眼旁观不屑争斗的人。时代的进步会否将他们灭绝?唯愿他们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祭品。即使做了祭品,也去做门楼的基石,月光的亮影,初春的柳芽,懂得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向他们致敬。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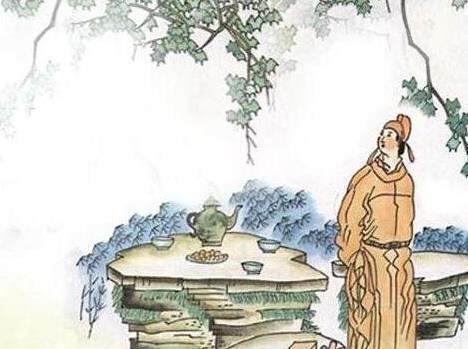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