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君是散文诗的名家,于荣健是现代诗的高手。一位曾是我的领导,一位曾是我的搭档。一位面黑心热,一位面善性强。一位量好擅饮,一位滴酒不沾。我是先认识何敬君(老何),后知道于荣健(阿健)的。认识老何是因为他对我的“不客气”,知道阿健是因为总在报刊上看他的作品。与老何算是不打不相识,由认识进而了解后来成了朋友。知道阿健时,他在大学教书,后来他来电视台帮忙后正式调入,与他因工作而认识再到从了解到理解渐成莫逆。
与老何认识缘于我们先后同住一间单身宿舍。我1985年毕业分到电视台,开始住在单位招待所,后来单县路39号倒出来一间单身宿舍,单位安排我住进去,我拿到钥匙打开房间,霉味扑鼻,房间不大,四张床上都堆着破烂,显然这些破烂都是有主人的,我看屋子中央还能派上用场,就用两张凳子搭上木板算是自己的床了。说实话,与其说这是一间宿舍,还不如说是一个破烂市,不过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就这样,我算是在单县路39号住下了。有一次,我外出采访,一两天没回,当我再进到宿舍时,看到我临时支起的木板床撤掉了,我的被窝被放置在靠窗的床上,叠得挺整齐,原来睡觉的位置,堆着一堆垃圾,其他床上的破烂也好像被整理过,房间显得亮堂了不少,再看垃圾堆上有一张纸条,字很遒劲,写着:“小伙子,房间我们给收拾了一下,你把垃圾倒出去。何”,我因为刚刚采访回来,累得慌,懒得动,那堆垃圾根本不影响我睡觉,也就懒得去管它了,第二天还是没处理,第三天回到宿舍,看到垃圾没了,房间清爽了,心里也随着清爽起来,至于那堆垃圾是谁倒腾出去的也懒得去关心,甚至早忘在脑后了。直到有一天在单位大院碰到一个乌发茂盛的黑脸汉子,上来没客气,开腔就问:你就是刚来的大学生?我说,是啊。接下来没容我多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无非指摘我懒得出奇,房间不知道打扫,别人打扫好了连垃圾都不知道处理。我意识到,这无疑就是那个留纸条的“何”,毕竟自己有些许理亏,再加上刚到单位,我没敢回怼,只好唯唯。心里却不免埋怨,你们离开了单身宿舍,却让破烂占着床位,我还没说什么呢。又想,你在广播我在电视,谁也挨不着谁,我也必要理会他。但是很快,不打交道的念想就打破了,一次我把钥匙锁在房间里,进不去门,只好到老何家要他的钥匙,我走进了他家,一个不到十平方的三角结构的房子,还不如单身宿舍宽敞,我怯怯说了钥匙的事,他让我进屋,在那间暗无天日的房间,我突然觉得他的脸并不黑,在家里,气氛不一样,我们都各自表现了足够的客气,就这样算是认识了老何。
和阿健相识就没有多少曲折离奇的故事了。1992年,电视台拍摄《大青岛畅想曲》,决定从社会招揽人才加盟,在海大当老师的阿健正好想跳出自己的圈子,就这样校园诗人走进了电视圈。他长发飘飘,颇有诗人气质。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名字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山大中文系78级系友作家杨争光来青岛,中文系几位系友在青岛日报张幼川那里聊天,我忝列其中,听他们说到青岛的青年一代作家诗人,当时他们说到了阿健,由此可见青岛文坛上,阿健早就有了一席之地。阿健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比我早毕业一年,差不多是同龄人,尽管他进电视门比我晚几年,但心理上丝毫不觉得自己处于劣势,而我也从没觉得自己在电视业务上占优势,反倒对他在诗歌、散文创作上的成绩颇为艳羡。他调入电视台时已经发表很多作品,进到电视门里,投名状很好看,自然是有身价的。现在想,亏得当时电视行业正在上升通道,这才引来像阿健这样名头很大的人才。时移势易,就像我们各自的青春不再了,电视媒体的优势也在消减,如今的电视媒体是否对人才还有这样的吸引力?还真说不好了。
老何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开始分在国家广播电视部一家直属单位,因为妻子在青岛,就申请调了回来。与老何越走越近,源于相同的农民家庭出身,他老家即墨,我老家平度。农民出身有一种天然的气质,这可能就是城里人眼里的“庄户孙”气质。曾经共同的贫寒经历,让我们很快忘却了乍见面时的种种不快,很快熟络起来。我依旧住着他曾经住过的单身宿舍,他自己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从三角房换到了我单身对面的筒子楼。有一次,他夫人带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娘家,我到他家吃饭,他用半斤羊肉做的羊肉汤,一碟花生,一点咸菜,我们喝了将近两瓶白酒,一瓶是“文君大曲”,一瓶是“沱牌”白酒,羊肉汤不停注水加盐和味精,花生米数着“个”吃,就这样一顿酒宴,让我铭记终生。后来和他、和别人喝了很多酒,吃过若干大餐,但细节和味道都记不得,唯有那碗清汤寡水的羊肉汤让我不能忘却。再后来他在九水路分了“大”房子,房子“装修”是我和他小舅子去干的,就是用白粉刷了一遍墙。他九水路的房子对我来说就像宫殿一样气派,老何的夫人热心肠,每到年节,都会让老何叫我们单身去他家过节,有一年中秋节,我、徐希臻和徐的女友一起在老何家过节,徐喝醉了,干脆宿在了他家。后来我好几位大学同学到青岛,我都带他们去老何家蹭饭、聊诗、谈天说地。这期间,他还用诗为我做了素描,后来他将写给我的那首诗收进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沉默的帆》。再后来,老何升官了,当了电台专题部副主任,再后来,他参与创办经济台,从副台长到台长,势头旺盛,意气风发,我们会偶尔吃个饭,但私下的交往淡下来了。
阿健调到电视台,正是电视的一个井喷式发展的起始阶段,幸运的是他一脚踏进电视台,就在一个创新意识超强的标志性部门名利双收,而我却在另一个部门不受待见,一度还下了岗。阿健当时所在的专题部,是一个五湖四海的部门,有老员工也有新生力量,创办的几档节目一经播出广受好评,钱也赚得盆满钵盈,从大学教书匠到媒体人,当时,阿健享受到一些学校里享受不到的好处。我下岗以后,有一次我实在闲得难受,就去他们部门办公的自来水公司找人聊天,听说了阿健打扑克的一件逸事。那时候,单位不太要求工作纪律啥的,什么迟到早退,休息时打打扑克都没人管,甚至领导带头做这些今天看来不太靠谱的事情,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没经历过的,绝想不出一个道貌岸然的领导会和普通员工在牌场上混战,输了同样脸上贴纸、颈上带环的景象。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有阿健在牌桌上的“壮举”,据说,有一次,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因为牌技不济总受到一位牌油子的揶揄,让他十分难堪,当即将一杯热水泼在那位牌油子身上,满场愕然,都被这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眼镜男的暴怒震撼了,那位揶揄他的牌油子也始料不及,连声道歉,这才了事。菩萨心肠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没有白白受欺负的道理,后来阿健受到一位同事的污烂行径伤害,但因对方是异性,好男岂能和恶女斗,只好气在心里,只能摇摇头徒唤奈何。
山不转水转,2002年7月,老何和我先后到了青岛广播电视报,他任总编,我给他当副手。命令下达后,他夫人很担心我们能不能合作好,怕因工作关系导致几十年的友谊翻船,我一再表示,自己经历过很多领导,绝对不会和老何怎样。老何当一把手惯了,在经济台一言九鼎,很多人私下都叫他“大黑脸”,没想到,他到了电视报,性情大变,让我负责编务,自己基本不插手,给我充分的空间。人就是这样,各自有了腾挪的空间,就不会轻易冲突。当时,我经常和他开玩笑,让他出出差,我好主持一下全面工作。这样的话,副手一般不敢和正主说,我说了也就说了,他知道我不会抢班夺权搞阴谋,我也相信他不会因为一句玩笑话而鸡肠小肚忌恨人。那时候,电视报已经走进下滑通道,我们用了不少心思,终难使其起死回生。后来,老何调整到局里工作,我接任电视报总编,我们搭档两年时间,没有任何冲突,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随笔和散文诗,后来出版了一本随笔集和一本散文诗集,这两部作品集是他创作成熟的标志,尤其是那本散文诗集《逝水年华》,可以称得上是他散文诗的代表作,后来我专门为这本诗集写了评论。
阿健到电视台后,报刊上很少见他发表诗作了,倒是常见他写的随笔。当时《青岛晚报》正火,他和其他几位文友开了专栏,后来几位作者分别将这些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他送了我一本。我主持电视报工作后,常常让编辑约阿健的稿子,编辑也乐意约他写稿,说是他的稿子基本不用费事,拿来就能用。那是肯定的,一个锻词造句的诗人,写流水一样的文章,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我是1998年底竞争上岗当的“芝麻绿豆样”小官,阿健也曾参加了竞争上岗,他没能如愿,为此发过这样的牢骚:阿狗阿猫都当上官了,我怎么不能?我说,就因为你不是阿狗阿猫!没成为“阿狗阿猫”的阿健在电视纪录片领域深耕细作,颇制作了一些好片子,像《青岛的路》《胶州湾》《青春青岛》等等,但是他不太会宣传自己,不仅在官场上难以跻身“阿狗阿猫”行列,在职称评比上也屡屡受挫,尽管我的职称评得也不早,但相对心安理得,因为很多年我没参与,我不想考职称英语,觉得那是对自己的苛刻,直到取消了英语考试,我才报名参评,可他一直在努力,所有的硬件早早够了,就是一再蹉跎,陪跑了无数届,直到2019年和我同榜评上了高级,这时,我们都离退休不远了,真是白首新高级,见人颇羞赧。
老何、阿健和我,三人交集是在电视台。2009年底,我工作岗位调整到电视台国际部担任主任,那时,老何是分管副台长,阿健是国际部的制片人。第二年又是一轮竞争上岗,阿健终于跻身“阿狗阿猫”行列,竞聘上国际部副主任成了我的搭档。当时国际部在新闻中心的盘子里是边缘化的部门,奖金福利都低于中心的其他单元,干的活也是拾遗补缺,总之,姥姥不亲舅舅不爱。我想,国际部有自己的实力和传统,应该抓大题材做大片子,于是和阿健策划为青岛建置120年制作一部12集历史文化纪录片,从2010年动议,报选题,找资金,到2011年12集《青岛时刻——120年12个瞬间》播出,我们两人和几位年轻的编导摄像殚精竭虑,终于没有辜负这个题材,也没有浪费宝贵的资金。片子播出后,获得好评,中央台纪录频道在黄金时间播出了其中六集,并于年底给了一个“最佳制作”的奖项,也算是对我们的肯定。这其中有一个插曲不能不说,2011年春分那天,老何突然出现在新闻中心例会上,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工作节奏慢了,怕到点播不了片子,影响大局,对我和阿健祭出批评的利器,言辞之激烈让会上三十几个人面面相觑,我一度从会场离开,再回到会场,老何的言辞更如烈火烹油一样,火辣得很,甚至说到要建议党委撤我们的职,我听后,火直往头上窜,会议结束,在电梯里,我没有克制自己的情绪,冲着他说道,你现在就撤我们吧!他黑着脸,一言未发。其实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我心知肚明,他也不会不知道,阿健也应该清楚。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为了工作我们曾经直面矛盾,很快就释怀了。对我而言,相比面子,友谊价更高,别说老何这样多年的朋友,就是一些毫无交情的领导或同事与我产生过节,我也会选择忘记怨恨,只记好处,阿健更是如此。
《青岛时刻》后,我和阿健又带领同事完成了另一部文献纪录片《青岛制造》,这部片子后期播出时,我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是阿健一力承担完成的善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片子都是老何分管电视台时的作品。遗憾的是我们特别想完成的青岛三部曲缺了一部,终于没能如愿,也好,留点遗憾,不求圆满不正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吗?当时还策划了纪录片《大沽河》,这部片子开拍的时候,我已经出国,只完成其中两集的初稿,最后给我挂了策划之名,算是对我的安慰。《青岛时刻》《青岛制造》《大沽河》都是申请市里专项基金完成的,都出版了同名书籍。算是我和阿健搭档的纪念。
值得庆贺的是,我和阿健搭档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虚位以待》,我的同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吴清波兄是这本诗集的责任编辑,我自告奋勇当了这本诗集的特约编辑,说白了就是当了第一读者,后来我为这本诗集写过一篇评论,尽管诗评有点隔靴搔痒,但毕竟有我一份情谊在里面。诗集出版对阿健是一个概念,了却了他一桩心事,诗集请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给他写序,我因此有幸与这位汉学家相识,并和他喝了几次酒。阿健在出版了诗集之后,又用一年多时间,整理自己耗费数年之功写成的关于卡夫卡的书《有意拖延的告别》,这本读卡夫卡,我认真拜读了,对其中一篇“打到父亲”感触尤深,为此我专门请阿健签了一本送给了我那个让我爱、让我忧、让我牵挂的儿子,叮嘱他一定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后来“良友书坊”举办了一次新书推介,阿健请了顾彬、高建刚和我在“塔楼”做嘉宾,尽管拙于言辞,我还是粉墨登场了一把。
退休后的老何经历过一次不期遇的波澜,等到自己心情平复了,一次,约即将退休的阿健和我到崂山一游,在山里找了一户农家,要了几个家常菜,面对青山,吹着山风,我和老何喝酒,阿健喝着茶,聊着与世俗不相干的虚无缥缈的文学,他俩都深得个中三昧,我是文学的业余爱好者,听他们谈诗说文,很惬意,很享受,真有一种超脱感。老何、阿健是我的良师益友,职业生涯得这样的诗人为同事是我的幸运。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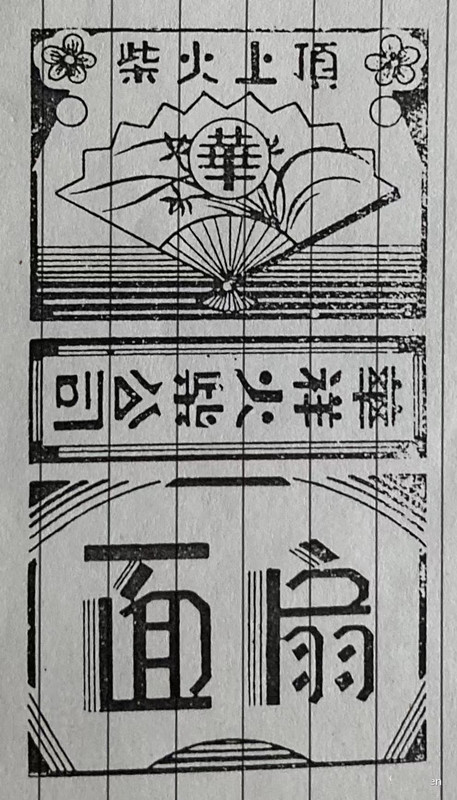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