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的反弹力
木心谈昆德拉,提到“布拉格精神”。所谓布拉格精神,主要是指那种对腐朽的传统观念或专制的意识形态的叛逆。木心认为:在卡夫卡、昆德拉这样出自布拉格的小说家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相对于世俗成见而言,布拉格精神是一种叛逆的、独立而自由的精神。它的成因,或许与布拉格这座国际化城市的特殊环境,也与它特殊的历史遭际有关联。但木心说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叫做“原生的反弹力”。
读了这个资料,我想到:这种“反弹力”是人人都有的。如果说人是“结构”出来的,那么“原生”就是其重要的结构元素之一。再加推测,“原生”虽然是深潜的东西,但它也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之物。猜想诸如本能、基因、气质、习得之物向潜意识的回流和渗透等等,便是“原生”的结构元素。
原生的反弹力随时随处可见,若把众多的反弹现象联系起来观察,真的会叫人“看得发怔”,如同昆德拉看东欧的极权主义社会;如同王硕看形形色色的“类型化人物”那样。
“原生”是隐蔽的,“反弹”却是可见的。例如,当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卡夫卡”,或“我不喜欢莫言”时,你知道他并没读过卡夫卡或莫言的作品,或只是从旁有一点了解而已,于是便会否认他“不喜欢”的理由。其实否认不得,他确实有不喜欢的充足理由——“原生”的直觉。一种特定的生命形态,当遇到“异质之物”时,立即就会作出排异的反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任何人身上,原生都是敏感的、直觉的、排异的,因为它是一种个体生存的反应能力。即使从经验上做对比,如:我是眼见为实的,你卡夫卡是梦幻的;我是有标准答案的,你卡夫卡什么都是不确定的;我是不会笑的(拉伯雷害怕那种不会笑的人),你卡夫卡是幽默的,等等。
原生的反弹力是非理性的,有的能照顾到良知,能爱一己之外的他物;有的只照顾自我意志,只附庸自我本性。虽有各种不同的反弹现象呈现在那里,但“原生”自身还是奥秘,就像《但以理书》中所说的,它依然是“封闭的异象”。
国情教会
要想走近救主耶稣,就得远离国情教会;远离自以为义的信仰圈子。
所谓“国情”,就是我们已习惯了的那些情况,它源于特有的文化积淀和生活环境,并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自己曾想从传统文化里找到基督信仰的元素,结果恰好相反,这种文化在根性上与圣洁的信仰追求相悖。实用主义不产生纯净的信仰需求;也不产生单纯的科学探索。因为它太浮躁,凡事都要“为我所用”,要“万物皆备于我”。它根本没有耐性真诚地走向客观对象,也不能谦卑地走向神。例如,把无限性的“知”挤压到有限而有用的“行”里面,谓之“知行合一”,这是何等的武断和自负。
厚厚的儒学传统,厚厚的小市民积习,这才是国情教会难以摆脱的“老我”。许多人信主是为了来找一种“被提”的良好感觉。举例如:说自己的读经微信群是“属神的”,而别的读经微信群则是“属人的”。讨论问题时,说“我们在天上”,而“他们在地上”。借用信仰来轻松实现自己做“人上人”的意愿,不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只要我信主,就是人上人”了。这种腐朽的官本位传统意识,不知不觉地就被移入了所谓的信仰里面,与基督信仰所持重的平等、互爱的理念相悖,并不是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意识。
此前,我用诗文两种形式写过对阿伦特揭露“平庸之恶”的体会。我认为,平庸并非平常,而是一种混合物,或者说是结构化的东西。圣经里所说的“酵”,可指“原罪”发酵为复合的“本罪”,其面目甚为可憎。如同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导致了极端之恶。国情教会正在发酵着“自以为义”的罪性,当警惕。
王起庆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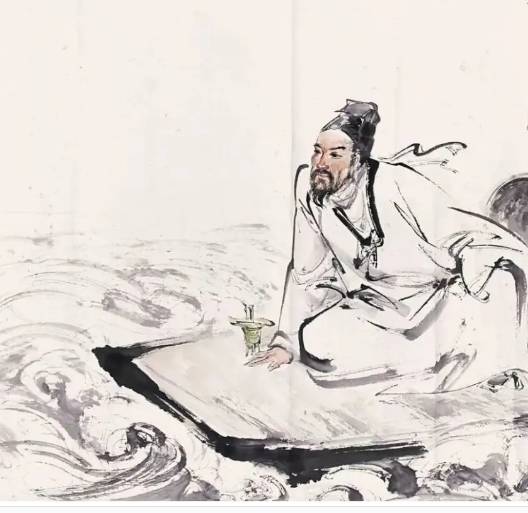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