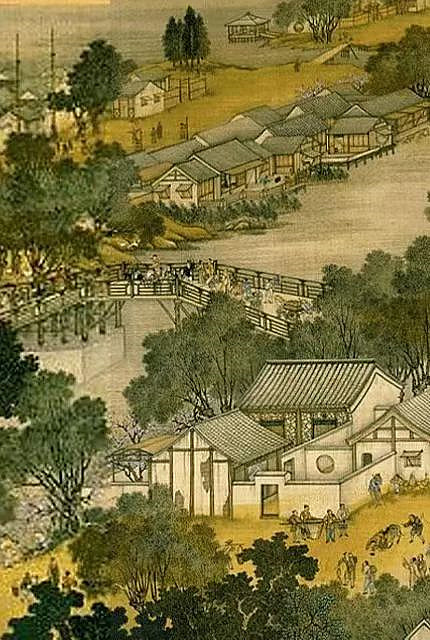1
从莫言南关旧居拍完照片,顺天坛路开车往南不远,到长丰街左拐,遇永安路右拐,往前是凤凰大街。凤凰大街和人民大街一样,是贯通高密的东西主干道,车流、人流汹涌,一幅忙碌拥挤的现代生活画。行进中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分秒必争、你挤我靠的车辆,而是莫言那四间新式瓦屋和陈列的有关他的过去的物品。
脑子就跳出“市井”这个词。资料显示,市井的含义大致有这么几条:古代城邑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指商贾;指集镇、街市;指城市中流俗之人;指行为无赖、狡猾;指粗俗鄙陋、飞短流长。市井与文化融合,或市井中经岁月沉淀的市井文化,可解释为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它反映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表现出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它自由闲散缺乏庄严,欠缺深刻性和心灵冲击力,更多的是自由闲散。
姑且不去评议市井和市井文化包含的褒贬意义,想说的是莫言在高密城内的旧居,就坐落在南关这片市井之中,如果不是门口“莫言旧居”的牌子,四间新式瓦房与周围众多的房屋几无区别,不仅平常,而且平淡。
但是莫言在这里生活过,与他的妻子和女儿。虽然我们无法复原莫言一天一天在这片市井中琐碎生活的场景,但我们可以展开想象,想象他如何手提新买的书籍走进天坛路,如何身穿汗衫站在前新一街和邻居磨牙聊天,如何匆匆忙忙奔赴火车站启程去往外地,又如何在深更半夜铺开纸张,沉入静谧的文字世界。无论我们如何想象,那时的莫言,我们可以把他定义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一个具体又简单的存在。
如今的四间瓦屋,因为有了这个具体存在,有了文学大师的背景,产生了与其他房子明显的不同。它不再是四间瓦屋,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为高密这个地方注入了更多文化内涵,远远超越了市井范畴。
礼拜天上午,我带着相机,径直冲进莫言旧居书房——这里,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我把自己设想为电视或电影摄像高手,集编、导、摄于一身,以书房为特写镜头,然后缓慢拉至中景、全景,全景后定格三秒摇出大全景,一片市井,又一片市井,组合排列为烟火天堂,它们可能囊括了生活的全部,三百六十度扫描了社会万象,但却无法展现生命的全部意义。
站在书房门口,咫尺之间,爬满由檐廊折射进窗内的光线。缕缕阳光像被木梳梳过,细密均匀地洒在墙壁、地面和天花板。进得书房,一眼便见南窗下硬木三人椅和三合板制面的茶几,书房内并无其他参观者,只一个书柜、一台写字桌、一张单人床分立房内各角落,简陋,局促,呈现一片荒凉。
荒凉是现实的构件,但这里的人生并不荒凉,更无荒芜。在旧居七年,莫言在简陋的书房内,完成了《丰乳肥臀》《酒国》《白狗秋千架》《天堂蒜薹之歌》等名著。
写字桌下并无座椅,想必莫言喜欢站着写作。站着写作累了,为不打扰家人休息,便和衣躺卧单人床上小睡片刻,然后起身喝杯浓茶,发一会儿呆,继续站立写字桌前,提笔创作。这当然是说笑,然而事实与说笑几无分别。
“这部书的腹稿我打了整整十年,但真正动手写作只用了八十三天。那是1995年的春天,我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在高密一个狗在院子里大喊大叫、火在炉子里熊熊燃烧的地方,我夜以继日,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全身心投入三个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连大门都没迈出过,几乎是一鼓作气写完了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
这部小说自然是《丰乳肥臀》,有狗大喊大叫的小院落自然是天坛路26号,如今也许只有那张破旧的写字桌还记得自己那三个月承受了什么。
我听到写字桌吱吱作响的叹息声,四条腿微微颤抖。虽然明白这是幻觉,却十分清晰,像刚刚发生过。
2
市井之中的日子,对于小市民,早出晚归,每日三餐,一天天过去,累积起来,就是一年又一年。回过头仔细看看,这一年和另一年,总不会有太过悬殊的区别。无非东家添了娃,西家走了老人。隔着不远的王家忽然发了笔小财,买了更大的房子,搬走了。而张家因为吃了莫名的官司,背了债务,出入再不如从前自在,见人便低了头,闪躲着匆匆走去,邻居们送上同情的目光,但也有心里却升腾起不可名状的痛快的。
行云流水,飘过家家天井,流经户户门前,到了天坛路26号,就打个旋,拐个弯,去往别处,因为书房门窗紧闭,飞短流长,市井传闻,都与埋头书桌的莫言没了关联,小说中鲜活的人物却在这几个平方里,轮流登场,演出一幕幕活剧。从33岁到40岁,莫言在这市井之中,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黄金的七年时光。
等到忽然一天,莫言举家迁往北京,市井内像刮了一阵风,起了微澜,饭桌上难免议论一番,议过后,风平浪静,日子重回老样子,什么人来过了,什么人离开了,都是擦肩的事,逐渐淡忘。
市井中总有一些人走的道路与大多数不同,人们淡忘的,是走的过程,记住的却是某个结果。因为走的路不同,难免被视为异类,引来议论,人们擅长用评议指点你的行走,但不会或终于不会陪伴你走上一段,这种心态,类似围观,或保持距离的围观。
也总有那么极少数,跋涉也好,隐忍也好,走到了底,走出了炫目的结果,于是围观变成喝彩,那异类也便成了楷模,成为市井中的风景与传说,并且代代传颂。
那块写着“莫言旧居”的牌匾终于挂在了天坛路26号门口,普通并平淡的小院落忽然平添了历史厚重感,它贯穿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成为不可撼动的碑石,在市井中突兀地站立。
莫言的过去我无法参与,自然也无缘介入他的将来,我只是在当下,以过客的身份,从陈列和悬挂中,用视觉和想象,拉近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
两间卧室,陈列旧家具和旧床铺。床、衣柜、高低柜,其材质来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是展示而不可能再被使用。女儿卧室床头之上的照片已经泛黄——母亲和女儿笑笑在旧居院内。她们站和坐的地方,现在已经被铝合金和玻璃隔为檐廊。照片中的月季花开得灿烂。那应该是个夏天。七个夏天在这里成为过去。
物是又人非,在市井中的小小院落,从一个作家短暂又似乎漫长的创作历程中,我能看到和感受的,自然比莫言本人少得可怜。
已经是旧居,也就是历史,是曾经和过往,所有的尽可追忆而非展望。
西厢一间展室,展示的大部分是作家的创作履历、一个个获奖的节点,作家的人生因为这些节点而变得具体而有高度。
墙壁挂满照片,从四面墙壁的照片中,我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王建章和张世家。
1988年,对于莫言来说,是一次迁徙。在南关村书记王建章协调下,莫言买下了天坛路26号这套旧房,将还在东北乡平安庄旧居居住的妻女接到县城,开启了市井生活。毫无疑问,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当时的作家,在创作上是质的改变。创作环境的改善,在莫言的写作道路上起到了多大作用,我们无权议论,只知道积极的变化是必然的。
莫言的另一次迁徙,与张世家有关。张世家比莫言年长一岁,自幼与莫言结为挚友,虽自创企业,走上了与莫言完全不同的道路,却一直鼎力支持莫言的文学梦。1995年,莫言举家迁往北京,张世家买下了莫言位于天坛路的旧居,完好保存并于2010年捐赠给社会,也让我有缘来到此地。
2010年4月张世家因病去世,7月由其子完成捐赠,了却了父亲的心愿。2012年12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张世家没能分享挚友的成就和喜悦,但是我相信,莫言在第一时间,早已与患难与共的朋友分享了这一殊荣。
时光在市井里流淌,有一种友情不为人知,它只在岁月里沉淀、升华。旧居的红瓦片、翠竹、石榴树,灼灼地、殷殷地记得曾经的一切。
3
莫言南关旧居面南背北,正屋四间,后建屋前檐廊,多为玻璃镶嵌,光透充足,现为陈列莫言著作之用。正屋一间书房,一间主卧,一间次卧为女儿笑笑的闺房,一间堂屋用于起居。
屋前小院方正,东西两侧建有厢房,各有所用。院门东开,入门透过过道可见影壁墙正中镶嵌斗大的福字,福字迎门而立,为市井人家“开门纳福”之普遍陈设,是向往居于福地的美好祈愿。
高出影壁墙的,是一丛翠竹,正拔节展叶,通体苍翠,兀自享受“明月时至,清风自来,形无所牵,止无所柅”的情趣。想必莫言也喜欢竹子,并于影壁墙后种植数株,逐年繁衍,生成大丛,喻之“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改其节”,夜凉风至,疏影摇落,清籁幽韵,宛自天开,可发怀古抚今之思。
碰壁北折入院,院内多为水泥铺地,隔开几个花圃,花圃雏菊开着,玉簪正绿。视线中一株石榴立于水井西侧,高两米有余,新生枝叶嫩绿,面向正屋一侧数朵石榴花开成粉红,闪躲在绿叶中。石榴之躯干、虬枝、花叶、果实皆可观赏,并因四时而不同,被北方文人喜爱,常植于院落。
石榴树旁,一株西府海棠,尚未成景,应该栽植不久,但观其主干,亦应超过五年树龄,初春花开之时,粉花连缀,簇簇迎风含笑,蔚为壮观。想那时莫言幽居书房,奋笔疾书,海棠花在西厢房外摇曳,恰似唐代诗人刘方平描写的庭院春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光流逝,市井中,唯此一景,不争吃喝,尚脱俗境。
立于西厢与正屋角落南视,银杏树高过墙头,超越院前红瓦房屋顶。树下一丛紫荆,花已经开过,只巴掌大的绿叶翘于枝杈。南墙下的海棠与屋前海棠呼应,为同一时期栽植。银杏与翠竹之间,四只石鼓凳围绕石桌,环抱着一段过去,讲述着一段往昔。
间或,王建章来了,张世家来了,莫言停下著述,落座迎客。树荫下,泡一壶茶,看竹影摇晃,聊些家常闲语,笑声扶地而起,轻飘飘,出了院落,散跌市井,失了影踪。
出旧居门,拾阶而下,便走到天坛路,北行几十米,与前新一街交汇,构成斜叉十字路口,东折北折继续为天坛路,北端汇入立新街,立新街两侧,店面林立,商业氛围浓重。
前新一街往西,穿过重重叠叠的平房楼房,商业店面,不多一会儿,可到达昌安大道,早些年前,这条大道被称为西关路,如今高密的西关,需再驱车往西十五分钟。
而沿前新一街东去,是一条现在叫作羊肠小道,过去却是大道的石子路,路边两排有些年头的白杨树,树荫完全遮住了路面,两边新房旧屋掺杂在一起,诉说着现在和过去。如此走下去,可到永安路,又一条店面林立的商业街。
站在天坛路、前新一街路口,迎面天坛理发店和西苑浴池,许是中午原因,已经关门歇业。右首望去,广州服装的招牌横在房屋西墙中央,批发零售杭州、广州的服装。紧邻的是冷冻肉放心店,红底黄字,备注为“安全、实惠、新鲜、美味”,分外显眼。
由旧居往南,一排一排与旧居模样相似的房屋。竖一列,横一排,组成井字形状。井字内,蛰伏着一户又一户人家,生生不息,人间烟火,代代相传。
房屋呈现惊人的一致性,显示了时代特征,被称为凝固的历史。家家四面合围,构筑成院落,院落相依相靠,却又相互独立,容不得侵犯,透露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建筑学理念,这种建筑理念,久而久之,演变为市井生活的信条。
这四面合围之地,便是家。人们走出家门,风雨里奔波打拼,大都为了安家。家安则人安,人安而心安。在市井之内,无家可归无疑是最悲惨的人生。
从莫言南关旧居这个点上升起来,俯视这片城,平房的市井,楼宇的市井,壮观为一片海洋。我如一条游泳的鱼,在市井里游弋,找寻另一种价值,另一种人生。当我正在为形形色色浑浑噩噩不同的人生发出感慨时,一位骑三轮车播放敲击卖豆腐梆子录音的老人,停在我面前,看了足足三秒后问:“小伙子,低血糖吗?”我说:“是。”他举刀切下一块豆腐:“先吃点,管用。”我说:“谢谢,多少钱?”他又切下一块,递到我手上:“吃了吧,不要钱。”
他骑上三轮车,梆子声清脆地往南去。他由莫言旧居门前,骑过这片市井,消失在长丰街上。
二十几年前,玩过一个电脑游戏,叫“帝国时代”。游戏开始,只分配给你几个探路者,一辆采矿车,一个兵工厂,一个电厂……世界是黑暗的,因为黑暗而混沌不堪,只有探路者经过的地方,才是可以看见的世界。探路者必须找到金矿,采矿车必须运回金子,电厂才能发电,兵工厂才会造出各种武器装备。越发展壮大,耗费越多,越需要金矿等资源,于是,必须组织军队,去占领邻居的资源,否则你的一切将因为匮乏而停止运转,并且必然被邻居消灭。
于是,无休无止的战争爆发了。探路者不断被派发出去,探明新的疆土和资源,所有探路者都倒在了通往黑暗的路上,无一返回。
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寻找。尽管他们探寻的结果是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但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并一刻不停地探寻未知世界,直到倒下。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为何痴迷这款游戏,望着老人骑着三轮车远去的背影,我想,当烟火散尽,尚有眼前的旧居穿过市井散发着温暖的光,吸引着我,以及更多的我前来。
原载《青岛文学》2023年第六期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