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刘敞的小诗《微雨登城》充满妙趣:“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他将美好现实景观比喻为一幅水墨画,毫无疑问,在这里,画作的艺术层级同样高于现实。
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中认为:艺术美本来就高于自然美,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而心灵和及其产品理应比自然和自然现象更高级。这一观点如今已经人尽皆知,它已经浓缩成了一句俗语: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然而,萧诗的末句却又说:“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将画里美人与现实中的美人区别开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实中人拥有活泼的精气神——她的眼珠会灵动顾盼,她的气息芬芳若兰,她会娇嗔含羞,会哭笑恼怒。而这些,再酷肖、再具艺术价值的画作也难描摹。
萧纲的诗中存在着浓郁的艳情成分,艳情深处即是色情,在这个领域,画作是无法替代活人的——正如以玉石雕琢成的大米即使再能乱真也不能填饱肚子。艺术无补于实用,哪怕是本自于实用的审美之情。
萧纲的艳情之趣也指明了一个事实——对现实事物再酷肖的摹拟也还是摹拟,摹拟便有其局限,必然要舍弃众多无法摹拟、无法再现的要素。艺术无不以“摹拟”和“技艺”为础石,但在这个基础的层次上,技艺永远比现实低一个层级,永远要亦步亦趋地追随于纷繁万象的现实事物之后。这一观念,与黑格尔的美学理论恰好相反。
以分别心看,人的情感中永远存在着自然无法替代的妙趣;自然世界里也永远包含着人无法再现甚至无法领略的信息和奥秘。以同理心看,人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不能或缺的属性。不知二者如何一判高下?
人的情操,自然的深意,本应彼此注入,相互锻冶,各自容纳——伟大的或敏感细腻的人类心灵,在自然万象中锻冶成了情怀,这情怀又将反过来容纳并锻冶自然万象。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国古典时代,满心诗情画意的士大夫向那层叠山峦、回环江河投去的眼眸,本就带有这般丰满的深意。只有秉持着这样的立场,文人水墨画和山水诗歌才有生发的可能。
原载作者原创著作《诗井汲花录》
《青岛财经日报》“红礁石”副刊
2023.9.20 A8版转载,见报时有改动
组稿编辑:周晓方
冯震翔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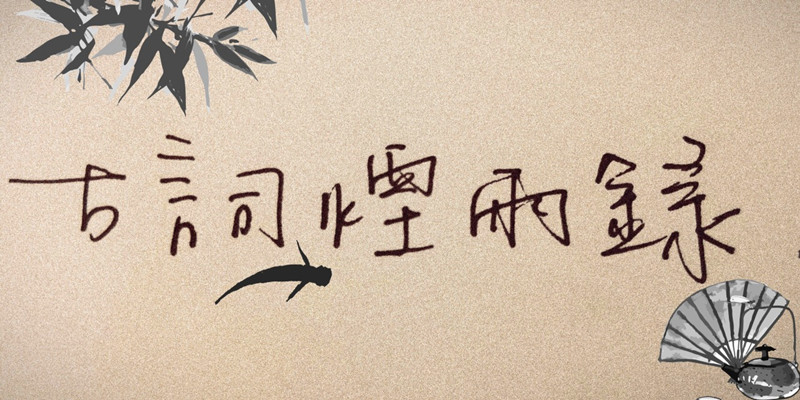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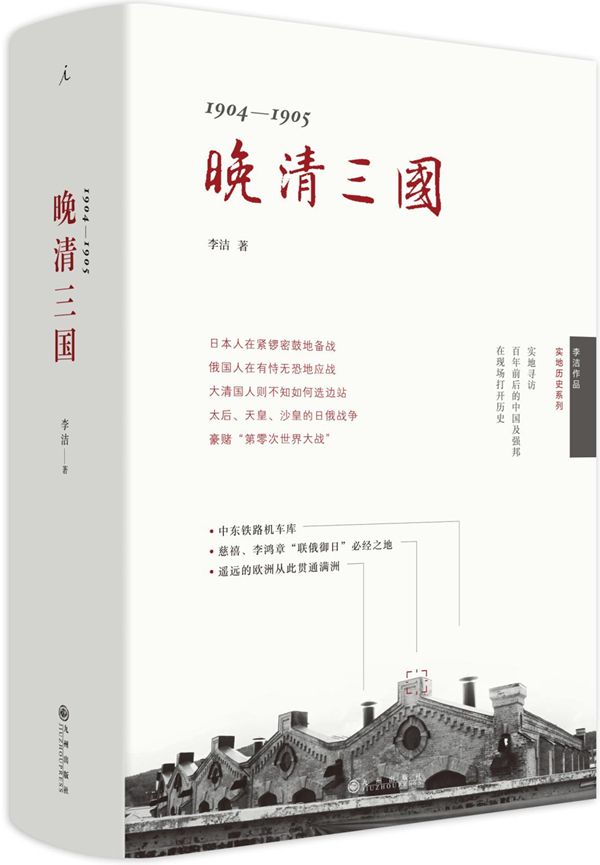



评论